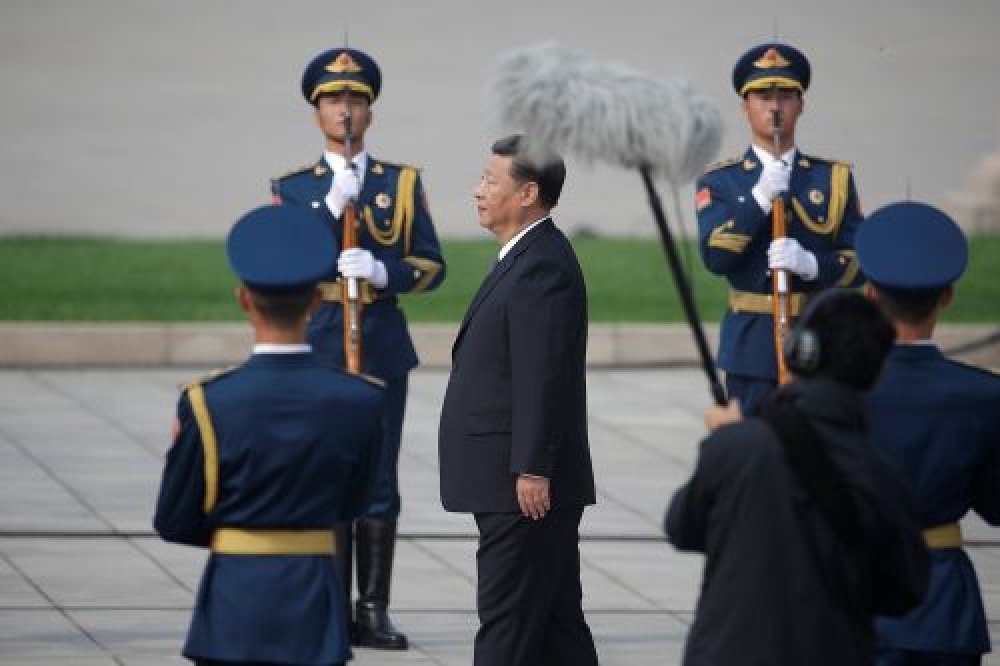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中華隊奪冠】AIT也發文祝賀 「這是歷史性的一刻」 2024-11-24 21:44
- 最新消息 【中華隊奪冠】感謝台灣英雄 賴清德:你們團結國家,讓世界讚嘆台灣 2024-11-24 21:37
- 最新消息 【中華隊奪冠】4:0完封日本!陳傑憲3分砲拿下MVP 賽後激動落淚:希望讓天上的爸媽驕傲 2024-11-24 21:02
- 最新消息 【12強冠軍賽】台灣奪冠!林家正陽春砲、陳傑憲3分砲 中華隊4:0完封日本 2024-11-24 20:59
- 最新消息 「小野爺爺」再次出動 邀請孩子共繪國家兒童未來館藍圖 2024-11-24 19:29
- 最新消息 主管遭爆性騷女職員閃辭 台鹽綠能:不因人異動停止調查 2024-11-24 19:06
- 最新消息 「給波波醫看牙,不如我自己拔」 王世堅上街聲援本土牙醫 2024-11-24 19:00
- 最新消息 波音再獲1.29億美元合約 持續升級日本F-15J「超級攔截機」計畫 2024-11-24 18:50
- 最新消息 【全代會觀察】打造主場秀拚黨魁連任 三度在野的國民黨用歡樂自娛? 2024-11-24 18:25
- 最新消息 【天氣變冷】明天全台各地短暫回暖 「這一天」低溫恐跌至9度 2024-11-24 18:25

接下來,我們不但應該直面他的憔悴肉身—一如直面他的強大精神,還要保存和傳播這些影像,直到他像格瓦拉的頭像一樣家喻戶曉。這些影像也應該成為他的詩的一部份,教曉我們何謂「無敵」。(湯森路透)
7月上旬這一次通過各種媒體觀看「直播」一個義人的死亡過程,我想不但會載入人類的心靈史,也將成為傳播學上的一次道德拷問。
中共官方主動發放劉曉波先生病重至彌留之際的影像,客觀上說是非常殘忍的,它有意無意之間把關心先生病情的人置於一個「旁觀他人的痛苦」的境地,在這種處境下你甚至無暇覺得荒謬,而只是加深自己的罪責感:
你眼睜睜看著一個不應該早死的人在迅速死去,你身處自由的世界看著一個尋求自由的人在不自由的禁錮中死去;你因為無力,而成為了權力的共謀。
但是影像自己彷彿有自我救贖的力量,也許這力量一直追隨著劉曉波先生的形象,使他並沒有淪為被同情者。當我看到劉曉波先生瘦骨嶙峋被一群醫生或者便衣包圍的一幕,我想起的是被約翰•伯格論述過的切格瓦拉殉難圖,他說後者令他想到的是歷代畫家繪畫的耶穌受難後被放下十字架的圖像。也許是攝影者潛意識被受害者的高尚精神所感召,選擇了一樣的角度,但更有可能的是,觀看者自行選擇了這種解讀,以作為無力之中最後的反抗。
雖然劉曉波、格瓦拉、耶穌三者大不同,但他們的急公好義、無私之心是一致的。縱然我們不希望一個民主抗爭的踐行者最後被聖徒化,但是他的受難必須被理解為「就義」。這完全可比聖徒之殉難,因為他沒有屈服於權力,僅僅是順應了「義」的悲劇精神而死去,此舉讓他和我們的「失敗」都得到昇華,讓我們稍稍知道抗爭下去的意義。
劉曉波先生留存在世的最後文字,也顯示了這種昇華。那篇目前僅見的寫於病床上的為劉霞的攝影集所作序言,絕不僅是序言、不僅是藝術共鳴、甚至不僅是寫給劉霞的情書(就像先生大部分的詩一樣),這也是他給我們的一個明確的訊息:
你們沒有罪,你們應該和我一樣坦蕩,徹底無視那個囚籠。整篇文字是光明的、強大的,它當中沒有一句抱怨和責難,甚至沒有所謂的「申命」。
他說:
「從此以後,讚美成了我一生的宿命」,
他以最後的文字做到了。
這最後的文字是詩,囚禁中的劉曉波還原為他最本質的身份:詩人。詩人讚美這世界的真、善、美,這是詩的本源。「詩三百,思無邪」,詩固然不能抵擋坦克、推翻獄牆,但它無時無刻不在種植坦克壓不死的野草、建設著比監獄美麗得多的花園。一如詩人W.H.奧登在《悼念葉慈》中所宣言:
「他在年月的囚籠中/教曉自由人如何讚頌」。
這樣的一個囚徒,他比任何人都要自由,尤其是比那些獄卒自由。
 之前我沒有觀看劉曉波先生的病中影像,一是因為不忍,一是因為對拍攝者的恨。但我想,接下來我們不但應該直面他的憔悴肉身—一如直面他的強大精神,還要保存和傳播這些影像,直到他像格瓦拉的頭像一樣家喻戶曉(我看見外國的塗鴉藝術家已經在這樣做)。這些影像也應該成為他的詩的一部份,教曉我們何謂「無敵」。
之前我沒有觀看劉曉波先生的病中影像,一是因為不忍,一是因為對拍攝者的恨。但我想,接下來我們不但應該直面他的憔悴肉身—一如直面他的強大精神,還要保存和傳播這些影像,直到他像格瓦拉的頭像一樣家喻戶曉(我看見外國的塗鴉藝術家已經在這樣做)。這些影像也應該成為他的詩的一部份,教曉我們何謂「無敵」。

【延伸閱讀】
●劉曉波已逝 我們還在等什麼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起底謝宜容!傳身家背景雄厚「善做公關」 先生和綠營高層有交情
- 陳妍希與陳曉鬧婚變疑復合 她素顏與閨蜜聚餐模樣超清純全網夢回《那些年》
- 《珠簾玉幕》大結局趙露思、劉宇寧擁吻訣別 她含淚哀求他「這句話」全網哭翻求番外篇
- 【內幕】T112步槍裝彈器採購案疑專利侵權 以色列向軍備局寄存證信函
- 楊冪人氣暴跌與《慶餘年》張若昀演新片淪鑲邊女主 造型曝光全網夢回《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 勞動部涉職場霸凌不只謝宜容? 何佩珊:與輕生者中間還有2個主管
- 《珠簾玉幕》趙露思虐戀劉宇寧流量破7億 卻因5大敗筆豆瓣僅拿6.3分慘輸《永夜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