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木村拓哉新戲《Believe-為你架起的橋樑-》攜手天海祐希演夫妻 8位豪華卡司公開全網期待 2024-04-20 18:00
- 最新消息 台灣第一人!他勇奪美國變裝實境秀后冠 蔡英文祝賀 2024-04-20 17:40
- 最新消息 桃園新屋今又停電 張善政:這不是台電總經理能解決的問題 2024-04-20 17:03
- 最新消息 【明天播出】楊冪新劇《哈爾濱一九四四》搭檔秦昊 預告曝光她僅露臉8秒慘淪鑲邊女主 2024-04-20 17:00
- 最新消息 身體老化最怕這個問題?8 成熟齡族未老先花 温昇豪:新式老花雷射手術 CP 值超高 2024-04-20 17:00
- 最新消息 預測員工去向、留住新進人才 日本企業求助人工智慧 2024-04-20 16:50
- 最新消息 七旬婦裝2針孔偷拍房客 理由竟是「怕在屋內吸毒要蒐證」 2024-04-20 16:22
- 最新消息 《長月燼明》白鹿新劇搭檔《蓮花樓》曾舜晞爆不和 他「妝造醜翻」疑遭打壓粉絲氣炸 2024-04-20 16:00
- 最新消息 【廢死論辯】為死囚請命!王牌人權律師父子檔登庭對戰法務部悍將 2024-04-20 16:00
- 最新消息 柯建銘轟黃國昌助「藍」為虐 被問徐巧芯名牌衣秒回:對她沒興趣 2024-04-20 15:37
國際法學家路易絲.阿爾布爾所堅持的法治精神,就是透過法定程序讓事實可以揭露,讓受害者可以作證,談出自己的遭遇。這正是台灣目前追求轉型正義的核心理念。(唐獎提供)
1996年,49歲,育有一兒二女的加拿大安大略省上訴法院法官,路易絲.阿爾布爾(Louise Arbour,我們就稱她「阿布」?)接獲來自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ICTY)的祕密接觸,探詢她是否可能接任法庭的首席檢察官?
平日就案牘勞形,又剛剛才以十個月的時間,主持針對金士頓市女子監獄醜聞所成立的調查委員會,完成加拿大獄政改革上重要的「阿布報告」的她心想,「我也不太清楚這個ICTY在做什麼,不如把這事暫時放一放,去做個頭髮」。
頭髮做到一半,電話來了,是法庭的主席,也是國際刑法學界的祖師,義大利籍的安東尼奧.卡謝謝(Antonio Cassese),朋友們都稱他尼諾(Nino)。他個性急是有名的,即使初次通話,寒暄的時間也只有兩秒。
尼諾:「親愛的,妳對國際刑法了解多少?」
阿布:「國際刑法?種族滅絕罪、戰爭罪、違反人道罪……。你知道,我們法院辦過涉及納粹戰犯的芬塔(R v. Finta)案?」
尼諾:「那妳對調查與起訴戰犯了解多少?」
阿布:「我是學刑法的,沒當過檢察官,但有刑事審判經驗。」
尼諾:「我們好不容易從曼德拉那裡借來的Richard Goldstone,兩年期滿,要回南非當憲法法院法官了,妳有沒有興趣來接他的位子?我們法庭有一堆起訴案,但還沒有太多戰犯可審。『我們的法庭』可不能失敗。」
阿布:「嗯,『我們的法庭』?這法庭是你開的嗎?」
這開始了阿布法律人職涯中,最具挑戰性的一段經歷。
阿布在演講中,曾自嘲說她是無意間闖進國際體系的觀光客(accidental tourist),只能邊做邊學。尼諾與阿布,一個大陸法系學者出身,另一個是普通法系下的法官;一個是搞國際法的,深諳國家間的往來之道,另一個曾是刑法教授,罪刑法定,講究證據,面對犯罪,同時深知必須以法律節制國家刑罰權。阿布曾說,若是尼諾與阿布可以經過衝撞,找到共同的觀點,那或許就預示了國際刑法的前景。
這位阿布是誰?
當時國際間,乃至加拿大外交圈,大概很少人曾聽過阿布的名字。但阿布在加拿大法界,已經是色彩鮮明的人權律師與法官。(唐獎提供)
具有猶太血統,卻在天主教的女子學院受教育;生於法語區的蒙特婁,卻立志打入英語圈,畢業後旋即進入加拿大最高法院擔任大法官助理,後來又成為法語圈中,第一位被任命為安大略省上訴法院的法官。朋友形容阿布似乎天生反骨,勇於突破既定印象的窠臼並挑戰權威。
在擔任奧斯古德廳法學院(Osgoode Hall Law School)刑法教授時,阿布同時是加拿大公民自由協會(Canadian Civil Liberties Association)的副會長,以提倡女權著稱。39歲被任命為安大略省的法官,對人權法有更完整的接觸,對涉及社會邊緣人的案件,包括身心障礙者、毒販、或一旦被引渡即可能面臨死刑判決的人,特別有感。但阿布從不讓自己人權律師的關懷,影響到她的判決:對她來說,犯罪嫌疑人也有人權,而刑法絕不只是為了追訴犯罪,同時也在透過保障人權節制國家權力,「讓民主社會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裡。」
1994年4月,加拿大金士頓市女子監獄,為了弭平暴動,派出男性所組成的特勤小隊進入女監,搜查牢房、脫衣搜身。畫面流出在電視上播放,引發社會譁然。加拿大政府組成調查委員會徹查此事,並委託阿布法官擔任主席。在短短的十個月內,阿布親自前往獄所訪談,調查證據,蒐集了大量事證資料,掀開這過去刻意被人忽視的社會死角,問題遠比表相嚴重許多。1996年「阿布報告」開宗明義即表明:「在調查委員會成立之前,加拿大獄政單位對這些問題,根本絕口不提」,並明白指出監所內眾多剝奪人權的實況,包括任意施加長期隔離監禁,與種種輕忽性別或族群差異的措施。報告中建議將獄政管理帶進憲法與法律管制之下,以符合加拿大人權暨自由憲章的標準,開啟了加拿大獄政改革的先聲,在滿20周年的此刻,仍然被提出回顧。
阿布指揮若定,有效率主持調查的能力,同時也得到遠在海牙的聯合國刑事法庭的注意。
國際刑事法庭
199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聯邦在裂解的過程,各族裔間爆發了激烈的內戰,原本受壓抑的宗教與民族仇恨,受到政治人物的挑動,蠢蠢欲動,族裔間屠殺、凌虐、強暴乃至令人髮指的種族滅絕或「種族清洗」,一路由初期的克羅埃西亞獨立戰爭,蔓延到波士尼亞,乃至後期的科索沃。雖然冤冤相報,各族裔都涉入戰爭的犯行,但無可否認的,絕大部分是在塞爾維亞當局有系統的策動或默許之下發生的。而其背景,與塞爾維亞人「受害者的歷史情節」脫不了關係,許多人相信遠在鄂圖曼帝國征服巴爾幹半島時期,部分族群改信回教以取得政治經濟上的優勢,欺壓信奉天主教與東正教的族群,其後在二戰時期,這些回教徒又裡應外合,導到眾多塞爾維亞人遭納粹屠殺。
在非洲的盧安達,1994爆發內戰,過程中占有多數的胡圖人有系統的滅絕居於少數的圖西人,背後也是受了「圖西族至上主義」的影響。
國際社會震驚之餘,由聯合國安理會動用憲章第柒章的強制性權力,成立了前南斯拉夫刑事法庭(ICTY)與盧安達刑事法庭(ICTR),誓言追究戰犯的個人責任,將發動與執行這些犯行的罪犯繩之以法,以實現正義,為未來的和平與族群和解建立基礎,同時也昭告世界,人類絕不容許這些慘絕人寰的罪行,再度發生。
這是自二次大戰後的紐倫堡與東京大審之後,時隔半個世紀,國際社會再度成立機制,發動國際刑事訴追。在這期間,國際人道法與國際刑法並沒有死去,只是在內國法院,零星的出現追訴戰犯的案件;在武裝衝突的現場,則是由紅十字與紅新月國際聯合會(IFRC)此類特殊組織,不斷倡議。
萬事起頭難。阿布就曾提到,在當時,法律界對國際刑法的立意與機制,少有所知。聯合國雖然動用強制性權力成立法庭,但是,人在哪裡?錢又在哪裡?還有,既然是法庭,一切就必須照法律程序來:眾人所指的戰犯,不一定能被定罪;新聞報導也不能成為呈堂證供。起訴、調查、鑑定專家又在哪裡?
這些重任,落在ICTY首任的首席檢察官,Richard Goldstone的身上。他以在南非主持種族隔離後政治紛擾調查的光環,大大提高了國際刑事法庭的能見度。他曾說,他在ICTY最主要的工作,是不停的開記者會、受訪,以及見必須見的人,張羅法庭所需要的預算與人員,而把實際的犯罪調查與起訴,交給他的副手。無可諱言,法庭所需的大量法律人員,仰賴歐美國家中的公務體系法務、調查與鑑定人員的支援,以及透過學界與人權團體等聯繫,所招募到的人。而在聯合國的公務預算以外,法庭也仰賴歐美國家的挹注。只是,他們要求法庭「作出成績」,以起訴來換取預算(money for indictment)。
在這樣的情形下,Goldstone 逼不得已,只好「衝數量」,先針對中低階層的嫌犯起訴,期能逐漸向上追訴。問題是,有了起訴案,下一步就是審判。而被起訴的,都是武裝人員,還在前南斯拉夫各地活動,且在民族主義下,被視為英雄而非罪犯,難以期待當地政府將這些人交給海牙;而法庭本身並沒有執法的軍警,而北約組織(NATO)的維和部隊,因著自身安危,也怕破壞在地均勢等種種考慮,不願意與法庭配合逮人。
因著這些因素,聯合國刑事法庭有了辦公廳舍,有法官,有上訴庭與檢察署(因經費考慮,初期ICTY與ICTR共用同一上訴庭與檢察署),但無人犯可審。Goldstone在任三年期間,真正進行審判的案子只有一件:Tadic案,雖然該案奠定了許多法則適用的基礎。阿布到任時,赫然發現,70餘件起訴案中,在押的嫌犯只有七人。
另外,Goldstone想了一個方法,迂迴的解決無人犯可審的問題:被告缺席的審判。由於缺席審判是國際人權公約所禁止的,這個方法有合法性的爭議。Goldstone運用程序規則第61條聲請法庭核發拘捕令(arrest warrant)的程序,在被告尚未到庭的情況下,實際上將起訴的事證呈堂,以換取媒體的注意與輿論的支持。因此被稱為「虛擬審判」(virtual trials)。
這些就是阿布到任前,法庭的實際狀況。那麼,為什麼找上阿布?
無害的魁北克女子
事實上,阿布是Goldstone 推薦給尼諾的。Goldstone深知,法庭的下一任首席檢察官,需要一位刑法專業的人,且有能力策略性的思考法律;必須精通英語與法語,以同時應付 ICTR的需要;最好是位女性,以更為妥適地處理以性暴力作為戰爭手段的犯行;同時,也必須能夠獲得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支持。在一次研討會遇過阿布之後,Goldstone就已瞄準他的繼任人選。
當時,外界對阿布的印象是:「嬌小、風趣、隨和、入世、就事論事但不會咄咄逼人的魁北克女子。」看起來無害,不致帶來什麼大變動的安全選擇。特別是,當時西方政府正致力透過外交途徑達成南斯拉夫各方的停火協議。刑事法庭?擺在那裡就好。若是有助於促使軍頭坐上談判桌,很好。但,絕不能容許法庭做出脫離北約將軍與外交官掌握的事。

逮捕人犯到庭的骨牌效應
將軍們所不知道的,是法律人也有策略性思考。阿布喜歡賽局:不論下棋、橋牌、大富翁;別人想下一步,她想下七步。
她要帶來的第一項改變,是逮捕嫌犯到庭。她深知,唯有逮到人,審判才能啟動,整個法庭的運作才能活絡,正義才得以實現。
至於她所運用的策略,第一,是改變姿態,由仰賴列強轉為以安理會的授權為基調,要求各國政府與軍事部門與法庭合作。前已提及,這兩個特設刑事法庭是聯合國安理會依憲章第柒章的權力設立的,依法各國皆有與法庭合作的義務。
第二,利用列強間的同儕競爭心態,單點突破。當時聯合國多國維和部隊進駐波士尼亞,實際上最重要的三個區域分別由美軍、英軍與法軍看管。阿布先透過說服波蘭特種部隊指揮官與她合作,逮捕在Vukovar 醫院屠殺案的要角Dokmanovic,藉此展示逮捕戰犯是可能的。Dokmanovic的就範,造成一連串的骨牌效應,包括其他嫌犯的投案,同時也給了三強部隊同儕壓力。阿布也善用法庭的道德光環,對列強部隊軟硬兼施,比如威脅若在逮捕嫌犯上配合不力,將訴諸媒體將其怠惰公諸於世。
第三,祕密起訴(sealed indictment)。不同於 Goldstone 時期的「虛擬審判」,阿布低調處理主要戰犯的起訴與逮捕計畫:起訴書一旦作成,經法官簽發拘捕令,直接交給配合的北約部隊,直到逮捕到人犯之後,才將事證公諸於世。此一祕密起訴的策略,使嫌犯無法得知自己是否已被法庭盯上,增加其心理壓力。同時,也為嫌犯的逮捕,增加突襲的因素,同時降低其武裝抵抗的風險,增進執法人員的安全保障。
如同阿布所預期的,拘提嫌犯到案的初步成功,會帶來一連串的骨牌效應,包括促使被起訴者自動投案、當地政府的交付人犯,北約列強部隊間的良性競爭等等。在阿布擔任首席檢察官期間(1996-1999),交付法庭人犯數量激增,這些策略活絡了國際刑事法庭的運作,告訴世人正義的實現是可能的。
對法治的堅持
在更宏觀的層次,阿布巧妙的運用國際刑事法庭檢察官職位,所賦予她的權力,以實現正義。但她所作的一切,都是以法治為基礎。
剛上任才三週,阿布親自到Vukovar 醫院屠殺案的現場,親眼目睹在地的情況與鑑識人員的蒐證。她的親自到訪,讓戰犯的調查,增添一絲人性的溫度。有一個波士尼亞回教徒的媽媽,拿著照片,請求阿布將她女兒與孫子女的遺體發還,讓他們能入土為安。因為鑑識的需要,阿布無法當場答應,但允諾一旦完成蒐證,會立即將遺體交還。波士尼亞媽媽說:「我要妳一句話,以一個母親的身份,對另一個母親提出保證(mother to mother)。」阿布事後回憶,這句話,這份受害者對正義的渴求,經常縈繞在她的腦海。
但空有正義感,不足以滿足法律程序。刑法,由於事涉刑罰權的行使,在眾多法律中,是程序正義要求最為嚴格的學門。當刑法遇到國際法,還可以繼續其正當程序的堅持?還是會隨著權力而轉彎?
這裡碰上「法」與「政治」交錯的永恆問題:法律是否應該為更大的正義服務?還是法有它自己的目的,不應受到政治的干預?在國際刑法的領域,當交戰的各方有可能坐上談判桌,達成停火協議,此時,戰犯責任的追訴,很可能被認為是達成「和平」的阻礙。反過來說,若是以正義之劍懸於其頂,甚至針對性,選擇性的辦案,豈不是將法完全工具化,臣服於政治的目標之下?當女神之眼不再蒙蔽,豈有正義可言?
這些艱難的問題,應該是阿布在擔任首席檢察官,時刻必須考慮的問題:起訴?不起訴?何時起訴?各利害相關者總有方法把訊息傳遞出來。但據阿布自己所說,她一概不理。在她任內,從未向聯合國任何機構報告,也從未由聯合國方面接獲任何執行職務的指示。在唯一一次由聯合國祕書長所轉來,對她起訴政策的關切時,她正式回函指出,依照ICTY規約第16條第2項,檢察官作為法庭機關之一,應獨立行使職權,不得由任何政府或其他任何來源尋求或接受指示。
至於「和平 v.s. 正義」更深的討論,阿布有精彩的想法,等待讀者挖掘。篇幅所限,這裡只能提及,阿布認為正義有它自己的軌道,不應臣服於政治之下,為「更大的目標」所犧牲。這樣的思考也影響了她對「轉型正義」的看法 ─ 對台灣,她的來訪正當其時。
由以下幾個層面,可以觀察到阿布對法治的堅持:
第一,證據辦案。據其同事之回憶,阿布不但是策略行動者,也是親力親為看卷寫起訴書的檢察官。她在上任後,將一些為了「衝數量」但缺乏足夠證據的起訴案撤回;她對證據的重視,也可由她幾次親赴犯罪現場實地勘驗的行動得知,包括在科索沃戰爭爆發時,親赴前線蒐集米洛賽維奇部隊戰爭犯行的證據。在國際刑法圈內,阿布以其起訴案件證據堅實,而贏得稱譽。
第二,打老虎不打蒼蠅的策略。阿布放棄衝數量的想法,而往「打老虎」的方向,直接追溯到戰爭犯罪的源頭。也因此,阿布將追訴的重心,移轉至 Prijedor 集中營屠殺、Srebrenica大屠殺、與Vukovar醫院慘案,因為這些事件也是事證較為齊全的。
第三,對米洛賽維奇的起訴。科索沃戰爭一爆發,阿布親赴馬其頓與科索沃邊境,要求前往調查,被塞爾維亞阻擋在外。畫面透過媒體,傳到全世界,迫使米洛賽維奇低頭,讓檢察官進入。當時阿布語帶霸氣:「米洛賽維奇認為他可以不讓我進入科索沃,我們來看看他可不可以不進海牙。」(“Mr. Milosevic thought that he can keep me out of Kosovo. I believe that he can’t keep himself out of The Hague. We will just see.”)
但是她對米洛賽維奇的起訴,仍然是證據到哪裡,辦到哪裡。因此,在最初階段,僅以違反人道罪,而不是種族屠殺罪起訴米洛賽維奇,因為當時的證據尚不及此。當然,此一大膽的舉動引起西方世界震動,甚至多人在最權威的報紙撰文,指責法庭檢察官完全沒有政治概念,不受節制,將引發巴爾幹半島局勢動盪等。沒有人料到的是,一年多以後,米洛賽維奇選舉失利下台,又不久,被移交給國際刑事法庭審判。
阿布堅持法治,至少向世人證明,沒有人在法治之上。
不論由策略性的思考,或是對法治的堅持,阿布曾走在國際政治的鋼索上,看盡戰爭與屠殺,所帶來人性最黑暗的一面。她沒有退縮,拒絕無為,反而選擇了勇於任事,不怕爭議。支持她往前的,相信是對人權的尊重與熱愛。不論對監獄的調查,或戰犯的審判,她曾說,最重要的,是透過法定程序讓事實可以揭露,讓受害者可以作證,談出自己的遭遇。這不正是台灣目前所在追求的,轉型正義的核心理念?
不論就法律、就國際人權、就人性尊嚴,阿布都有很多可以教我們的事。她將於九月下旬前來台灣,從第一屆得獎人阿比手中領取唐獎法治獎。20年前,國際社會或許錯看了身形嬌小的阿布。我相信,台灣不會錯看了她。
延伸閱讀:
Oleg Gjerstad 所拍,描寫阿布擔任戰犯法庭檢察官的紀錄片
2016唐獎得獎人系列活動
http://topic.cw.com.tw/event/2016tangpriz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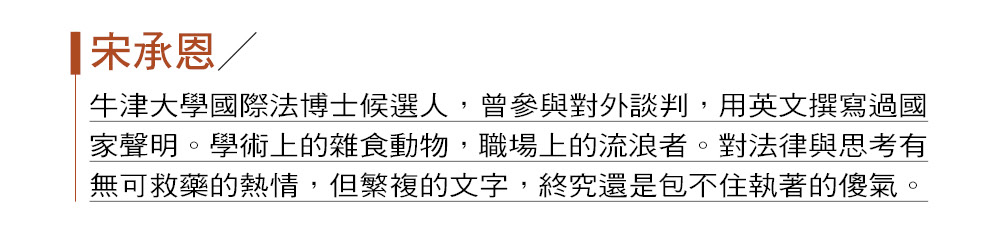
【上報徵稿】
上報歡迎各界投書,來稿請寄至editor@upmedia.mg,並請附上真實姓名、聯絡方式與職業身份簡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