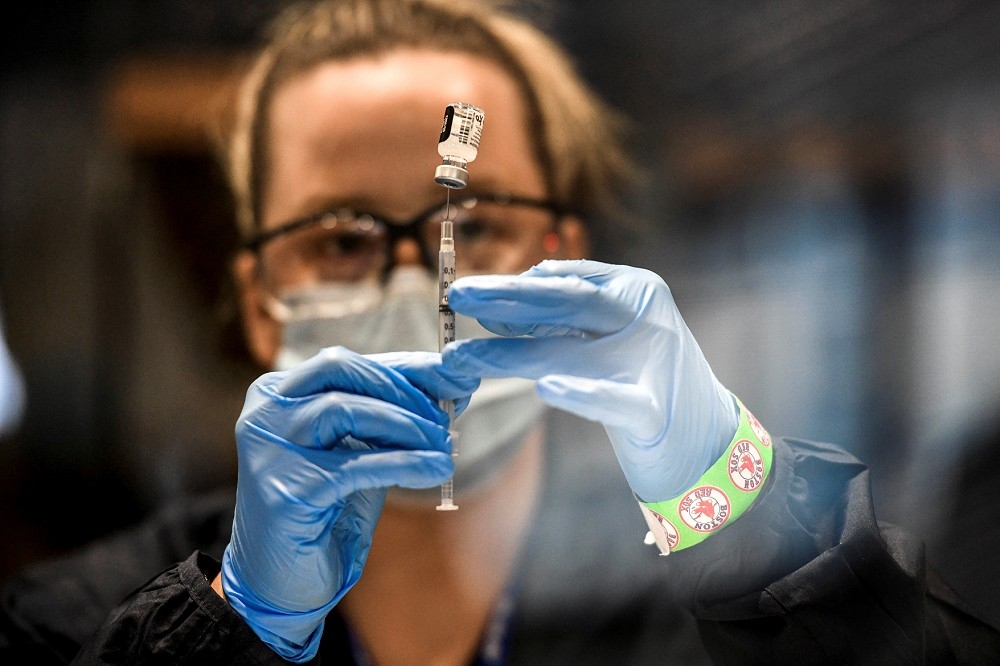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500元鈔票上「南王國小少棒」曾稱霸美國 資源不足曾解散、近年才得以重組 2024-11-28 17:32
- 最新消息 《流水迢迢》任嘉倫深陷婚內出軌醜聞人氣暴跌 自創潮牌衣服賣9千元挨轟削錢 2024-11-28 17:30
- 最新消息 雙城論壇擬12月中登場 上海團百人將訪大巨蛋、北流 2024-11-28 17:14
- 最新消息 陸生團2靚女!奧運金牌楊倩最愛台灣鳳梨酥 「超仙」彭弋航夢過日月潭 2024-11-28 16:50
- 最新消息 《繁花》唐嫣新劇自降咖位演《慶餘年》張若昀的媽媽 預告曝光她扮神秘歌女造型美翻 2024-11-28 16:50
- 最新消息 鄭運鵬找到新工作 「畢業30年重新回到本行」 2024-11-28 16:47
- 最新消息 大谷翔平遭翻譯水原一平詐欺 要求歸還價值1000萬元的棒球卡 2024-11-28 16:45
- 最新消息 莊瑞雄否認玩球版「有就切腹」 民眾黨PO影片:他不只賭球還賭總統大選 2024-11-28 16:40
- 最新消息 賴清德總統30日出訪南太平洋3友邦 過境夏威夷關島 2024-11-28 16:31
- 最新消息 首波冷氣團報到!雪霸山區覆冰霜 銀白美景畫面曝光 2024-11-28 16:20

早期《新新聞》的標題慧黠犀利,專題企劃令人驚豔,是台灣解嚴初期政治新聞的標竿。(圖片摘自網路,本報合成)
《新新聞》要停刊了。雖說停的是紙本,不過,你知道的——秋天來了,冬天還會遠嗎。
我非常想念它,雖然我只是它的讀者,而且很慚愧,還是個從不付錢的讀者。它創刊時我在讀高二,總在下課後去金碧輝煌的「金橋圖書公司」吹冷氣,站著看完整本《新新聞》。那是一九八七年,台灣像一個戴著手銬腳鐐的乩童,經歷著自己也未必明白的劇烈震動,卻掙不脫言論管制的束縛。大多數人活在大眾媒體的泡泡裡繼續安逸著,計較著街頭運動的「社會成本」;一個大型的「楚門的世界」。《新新聞》是一個珍貴的破口。那時聯考導向的課堂上,有一位老師見識不凡,偶爾會說些他對時事的看法。我一聽就知道,他也看《新新聞》。那個年代的《新新聞》,是辨認我族的密碼。
後來《新新聞》漸漸淡出了我的視野,直到某一年,《壹週刊》傳出易手的可能,臉書上流傳一位高中生的文章。他說《壹週刊》是他的啟蒙,他因此嚮往記者不畏權勢揭弊的使命……文章寫得很好,英雄出少年,但是《壹週刊》是他的新聞標竿?我驚嚇不已,感覺好像老家被人拆掉了。《新新聞》就這樣完全被遺忘了嗎?

這幾年我在研究一起死刑案件,發生於一九九〇年。我想溫習一下那個年代的氛圍,於是跑去國家圖書館看《中華民國年鑑》。翻開那厚重的精裝書,有我們那年代所熟悉的政治圖騰:秋海棠地圖、國旗、十二道國徽的畫法、國父遺照、蔣公遺照、經國先生遺照、總統玉照……。第一章〈歷史與文化〉,不是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說起,而是從伏羲氏、神農氏說起!這是「歷史與神話」才對吧!我翻到「青年」的章節,記載著大專辯論比賽、籃球比賽的優勝隊伍,沒有一個字寫到野百合學運。
於是我重讀《新新聞》,從一九八七年創刊,讀到大約一九九二年。《新新聞》的標題慧黠犀利,當初膾炙人口的兩則,其一是「『政工』不能再『康泰』了!」這是因為孫立人案,談到國民黨用以控制軍隊的「政工系統」(第五十六期,頁二六)。其二是「『人二』怎能做『老大』呢?」當時每個公家機關與國營事業裡,都有一個叫做「人二室」的神秘組織,是情治系統監控之用(第六十期,頁四五)。

神來一筆的標題在早期的《新新聞》絕非罕見,他們總是直球對決,但謔而不虐。例如郝柏村與李煥的鬥爭中,李煥落敗,《新新聞》的標題是:「驀然回首,李煥已在燈火闌珊處(第一六六期,頁四二)」。蔣良任的〈士林殘夢了無痕〉更是經典,寫蔣宋美齡在蔣經國死後私函干政,企圖阻止李登輝接班:「這一齣荒謬的宮廷鬧劇,是由一群身在歷史之中、卻不甘心走進歷史的人所推出的。老夫人在走進歷史的前刻,留下一段幾乎變成民主罪人的紀錄(第四十七期,頁二七)」。
那段時間的重大議題,《新新聞》都提供了既好看又鮮活的分析報導。例如那個不改選的國會(標題:「一千人對抗一千九百萬人的戰爭」,攝影記者陳愷巨拍出了朱高正的抗爭爆發力,也拍出老法統頑固抵抗的決心);蔣經國過世(標題:「再見了,蔣總統!」對蔣經國的評價是:「晚間十一點半才開始工作,等到午夜鐘聲一響,他留下太多的工作,就被迫遠離了。」);史上首次軍人出任行政院長(政論漫畫名家CoCo畫郝柏村提著一袋屠刀進入醫院開刀房,病人很緊張的哀求醫生,「喔,不!不要!我認識他,他是殺豬的……」);許信良想盡辦法終於偷渡回台(標題:「美麗島喜形於色,新潮流鎮靜如常」)。一本政論雜誌,讀下來妙趣橫生。


我只是讀者,對於當時的《新新聞》編採過程全無參與。他們怎麼做出來的我不知道。我只是從成品裡看到,這個時期的《新新聞》才氣縱橫,有許多專題企劃令人驚豔。例如,「報禁解除」這件事怎麼報導?《新新聞》報導了兩大報編輯台,在報禁解除前的最後一夜;隔天是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解禁後的兩大報,仍然「全文恭錄」蔣總統元旦文告。《新新聞》問道,「這是一份等待了四十年之久的報紙嗎?(第四十三期,頁十)」又如萬年國會的許多民代,當初是落選者,只因當選者死亡或沒有到台灣來而遞補,不具正當性,但政府拒絕公布當初得票情形;這怎麼報導?《新新聞》挖出民國三十六年的《大公報》,重現萬年國會誕生的那一場慌亂的選舉實況。《新新聞》採取了一個「理解歷史」的角度而非「歷史審判」的角度,對於國共內戰期間的這場選舉,持平指出客觀條件的限制與各種缺失(第三十八期,頁一七)。
也有幾則小新聞,引起我的注意。那時候中國不斷對台灣喊話要「三通」:通郵、通商、通航,但台灣政府都不願意,當時的大陸政策是「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與大陸通信或做生意,都可能被認定為匪諜。這時,台灣省政府社會處發了一份公文,說如果父母在大陸過世,台灣的子女也可以請喪假,但必須依據「來自台灣域外地區的電信證明」。《新新聞》敏銳地嗅到了政府立場鬆動的氣息:這不就是默許民眾與中國通郵嗎?不通郵怎麼會知道父母在大陸過世呢(第三期,頁六二)?在我看來,這種敏銳細膩,就是記者的典範角色。
《新新聞》面對政治壓力的策略是公諸於世,以專業反擊。第一〇九期,權傾一時的政治家族朱安雄來函,對於《新新聞》報導他與妻子吳德美的非法貸款表示不滿,要求更正。《新新聞》來函照登,然後附上詳盡的「本刊說明」,意思是朱吳二人是政商勾結的惡例,已有公論,其他報刊包括《天下雜誌》亦已詳盡報導;《新新聞》出刊前訪問了朱安雄,已做到平衡報導。「現在朱委員夫妻開始顧惜名譽和形象,值得同情和肯定」,「官商結合乃當前政治之嚴重弊端,也是議會政治的毒瘤,本刊以往尚未針對政商特權情事深入加以報導,今後將把這類調查採訪列為重點,以不負讀者對本刊的期待」(頁八十)。怎不令人擊節大樂!
習慣了自由開放,今日重讀《新新聞》,也許會忘記解嚴前後種種桎梏的滋味,覺得《新新聞》這樣不是理所當然,很正常嗎?不是,那時候媒體受到國民黨文工會的控制才是正常,報紙想漲價必須向蔣總統呈報獲准才是正常(第二十六期,頁二五),電視台明知蔣經國死了也不敢播報才是正常(第四十九期,頁九二),像《中華民國年鑑》這樣八股、荒謬、粉飾太平才是正常。《新新聞》盡責監督政府之外,對於媒體同業受政治指使也不假辭色,屢次痛批《聯合報》當政治打手(第三十六期、三十七期、四十八期),結果《聯合報》旗下的海外通路「世界書局」,將《新新聞》惡意下架(第四十八期廣告頁,〈向海外讀者說對不起〉)。儘管《新新聞》的創辦人多半出身《中國時報》,但當中時余家競選國民黨中常委時,《新新聞》也絕不沉默(七十一期,頁八四)。當兩大報聯合漲價(第二十六期,《新新聞》評:「就像吸血鬼在天亮之前,集體享受最後一次鮮血。」),當《中時》與《自晚》有勞資糾紛(第八十期、第八十一期、第八十二期,第二十六期),《新新聞》大聲批評,並不「媒媒相護」。但是,《自立晚報》赴大陸採訪被移送法辦(第二十七期及後續),《首都早報》想要創刊被新聞局說名稱敏感(第八十七期),這些涉及媒體自由的議題,《新新聞》則熱情聲援,毫不保留。

我們那個沉重壓抑又荒謬至帶有喜感的年代,不僅過去了,而且被忘記了,如今只有在《新新聞》裡才得一見。當一隻螞蟻被包裹在琥珀裡,牠就從一隻普通的螞蟻,一躍而成為一隻承載了歷史意義的螞蟻。正是《新新聞》,使得解嚴前後那幾年,洋溢著蜜一般的琥珀色澤。如果《新新聞》當年的團隊還在,他們會生出什麼樣的精彩企劃來報導《新新聞》的紙本停刊?可惜這是無效的問題,因為這是涉己事務,他們大概不會花心思做這個。就像一個擅長為人辦生日驚喜派對的人,只能年復一年地過著自己不會有驚喜的生日。
《新新聞》的創刊酒會上,陶百川寫了一幅字,稱他們為「自由報業第一聲」。所有人都知道,《新新聞》週刊是暖身起跑,目標是辦報。但是天時地利人和終究沒有湊在一起為《新新聞》鋪設紅地毯,美好的願景沒有成真。那時候並不知道,戒嚴的訓令拔起之後,媒體的榮景竟是短暫的,更無法想像有一天《壹週刊》會成為新聞標竿,而《新新聞》不再被提起。
《新新聞》應該不是我個人的小小鄉愁,也不應該是我個人的小小鄉愁。但是好像沒有人知道網路上可以讀到《新新聞》。方法如下:第一,申請新北市立圖書館閱覽證。第二,在網頁上找到「讀者查詢服務」→「電子資源」→「期刊、報紙」→「風傳媒政治知識庫」。在「新新聞PDF」,可以一期一期的讀,也可以用關鍵字搜尋。如果你經歷過那個年代,讀《新新聞》如重溫舊夢,必有新的體悟。如果你沒有,《新新聞》是那個時代的人類學博物館,從題材到風格都是。我們至少把《新新聞》珍藏在記憶裡,如同將螞蟻封進琥珀那樣的慎重。
再見了,《新新聞》!這是我的懺情錄,為了我當年沒付錢。
※作者參與社會運動多年,關心性別、司法、人權等議題,著有《姊妹戲牆》、《愛的自由式》、《無彩青春》、《走進泥巴國》、《殺戮的艱難》、《十三姨KTV殺人事件》等書。德國漢堡大學犯罪學博士。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珠簾玉幕》大結局趙露思、劉宇寧擁吻訣別 她含淚哀求他「這句話」全網哭翻求番外篇
- 傳賴清德想把500元鈔票改印「中華隊奪冠照」 央行確定發行12強紀念幣
- 《深潛》成毅新劇搭檔《大夢歸離》古力娜扎 台灣女星演武林高手劇照曝光全網認不出
- 《春花焰》吳謹言與老公洪堯牽手逛街孕肚藏不住 他因「這理由」挨轟沒擔當
- 大風吹時間!《英雄聯盟》LCK 賽區各大戰隊轉會期 11/23 人事異動整理
- 【中華隊奪冠】麥當勞大薯買一送一!拿坡里、漢堡王、必勝客等 7 家速食優惠懶人包
- 《珠簾玉幕》大結局趙露思、劉宇寧生死訣別掀淚海 她與「崔十九」從宿敵變知己全網感動
- 中華隊最強捕手「林家正」介紹、IG!185 公分長腿、大胸肌迷翻家正婦 12 強冠軍戰炸裂東京巨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