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大巨蛋類地震】比照小巨蛋「禁跳令」? 北市議員:建管處可做周邊建物安全評估 2024-12-22 20:48
- 最新消息 【TPBL職藍】新北中信特攻邀海巡署長張忠龍開球 號召青年一起守護海洋 2024-12-22 18:56
- 最新消息 俄烏戰爭下是否該抵制〈胡桃鉗〉 立陶宛文化部長發言重掀激辯 2024-12-22 18:55
- 最新消息 柯建銘稱財劃法有折衷批韓朱卻硬幹 朱立倫:邊打邊談算哪種協商? 2024-12-22 18:52
- 最新消息 準颱風「帕布」水氣周一來會更濕冷 周五夜冷氣團再襲低溫下探13度 2024-12-22 18:25
- 最新消息 高捷列車車門「錯位」手動停靠引議 官方:安全無虞、深表歉意 2024-12-22 18:18
- 最新消息 【迎接2026】台北101跨年煙火搶先曝光 聚焦12強奪冠、融入台灣流行樂 2024-12-22 17:58
- 最新消息 《九重紫》大結局倒數最新預告曝光 李昀鋭中毒吐血孟子義用「這方法」餵藥又甜又虐 2024-12-22 17:45
- 最新消息 【大巨蛋類地震】「三天三夜」嗨唱掀共振效應專家解答 北市府暫不禁止跳動 2024-12-22 17:30
- 最新消息 《九重紫》李昀銳與孟子義戲份慘遭配角強壓收視暴跌 「他」演惡男頻頻搶戲全網唾棄 2024-12-22 17:15

德國戰後轉型之路遙遙。(取自Pixabay,邱惠鈺製圖)
美國猶太裔記者米爾頓.邁耶(Milton Mayer)在威瑪共和國的末期深入德國訪問,與當地的德國家庭共同生活了長達十年之久,結識了十個支持納粹的德國朋友,他嘗試從這些人身上找到「正派人」如何且為何成為納粹的答案。他發現,納粹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體制或意識形態,更是一種十分適合一戰後德國人氣質和心態的世界觀。
納粹征服德國人的心靈,也壓垮了他們
他進而指出德國的去納粹化和轉型正義的艱巨性:「在任何情況下,對德國人進行治療,都不會是沒有代價的,也不會有任何處方能夠確保治癒。」在德國問題再次成為歐洲和歐盟的核心的當下,這樣的觀察和結論並未過時。
美英法占領當局本來要對西德全面去納粹化,但冷戰的爆發使這一過程被迫中斷。西德的民主化和美國化遠不如日本:日本是由美軍單獨占領,儼然是「日本總督」的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戰功卓著,而且是堅定的保守主義者,遵循其清教徒觀念秩序對日本做出大刀闊斧的改變;西德由美、英、法分別占領,各國占領區的政策並不統一,且缺乏麥克阿瑟式的靈魂人物,加之蘇聯的威脅近在咫尺,安全問題迫在眉睫,使得除垢工作虎頭蛇尾。
1946年,美國占領當局釋放了被關押在巴本豪森—達姆施塔特戰俘營的德國戰俘,美國陸軍部在大門上貼出一份公告,這份文稿是典型的美國式的樂觀主義和理想主義:
無論是黨衛軍成員舒爾茨還是下士米勒,在你們跨出這道大門之時,你們的步伐會把你們引向自由。遺留在你們身後的是數月和數年的奴隸般的屈從、數年的殺戮和數年間人的個性遭受難以置信的羞辱。……你們不要自責。你們受到了蒙騙,盲目追隨了錯誤教義的呼召。自現在開始,你們在家庭圈子中的生活,能夠展現出自由的和泰然自若的情態。
然而,現實並非如此。在1946年,美國管制區57%的民眾對轉型正義工作表示滿意;到了1949年,滿意度只剩下17%。原本接受美國委託執行海德堡大學去納粹化工作的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因為看到轉型正義理想無法實現,失望地離去,轉往瑞士巴塞爾大學任教。雅斯培的離去,成為終戰之後,原來在納粹時期耿直堅忍地以「德國良心」留在德國家鄉,此時反而黯然離開的著名例子。而海德格、施密特(Carl Schmitt)等納粹御用學者,很快復出並在學術界享有崇高地位。
自以為轉型正義優於日本
第一位社民黨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在華沙在納粹屠殺受難者紀念碑前下跪,德國政府拿出巨款來賠償以猶太人為主的受難者群體。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的著作大大強化了這一觀點,他發現德國知識分子特別討厭日本,他們認為:「我們德國人是歐洲基督教文明的一員,講究實事求是,因此老老實實地承認我們對外侵略的歷史。可是日本人則不同,他們以所謂的『東洋文明』為由,不想承認錯誤,這難道不是軍國主義思想的體現嗎?」但這件皇帝的新衣經不起推敲。
日本記者三好範英反駁說,德國為了要平衡納粹犯下的不可饒恕的「唯一的惡」,對歷史採取斷然二分的態度,以全然的否定來顯示對自己過去的「克服」。由此,所謂「以罪為傲」讓德國在戰後重新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央。而且通過和日本的比較,產生某種道德優越感,日本成了德國重新做人的道德對照組——德國台面上人物屢屢公開批評日本戰後對待歷史的態度,但這恰恰是一種「扭曲的民族主義式的自豪表現」。
悄悄地成為歐盟領頭羊
柏林牆倒塌、兩德統一之後,聯邦德國成為歐洲第一大國、歐盟領頭羊。德國通過加入歐元、歐洲單一市場、追求「歐洲一體化」、輸出福利國家概念等政治經濟手段,逐漸實現其野心。在可預見的一段時期內,德國難以擁有昔日的軍事力量,但它對東歐一帶將持續保有地緣政治的野心——歐盟東擴最大的受益者是德國,德國得以掌控大部分東歐與巴爾幹半島地區。
在德國長期執政的梅克爾(Angela Merkel),其觀念秩序在東德共產黨時代就已定型。梅克爾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聯盟被視為中間偏右,但梅克爾本人比社民黨更左——那些特別標明為基督教政黨的,往往是沒有基督信仰甚至敵基督的政治力量。梅克爾並不珍惜德國和歐洲的基督教傳統,敞開大門接納百萬穆斯林難民,大大稀釋德國的基督教傳統。
命運與歐盟糾纏在一起
歐盟體制是帶有德國烙印的官僚政治產物,是個超越現有國家實體的跨國管理機構,它並不民主,其官僚機構不需要對歐盟選民負責。歐盟不可能通過體制改革走向民主,嚴重官僚化且腐敗,如同一個擴大版的普魯士模式。歐盟的困境也是德國的困境。
在美中進入新冷戰的國際格局之下,梅克爾政府堅持與中國結盟,儼然要「脫歐入中」。 美國與中國的衝突烈度,將超過冷戰時代的美蘇對峙。全球所有國家都必須選邊站。如果德國選擇站在中國一邊,那將是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第三次選錯邊。
近年來,在一個眾所周知的「民族品牌」指數排行榜上,德國位列第二位,僅次於美國。然而,「何為德國」的答案仍眾說紛紜,遠不如「何為美國」清清楚楚。德國哲學家哈伯馬斯提出「憲法愛國主義」的身分認同,但若完全拋棄歷史、民族和宗教信仰,憲法何以成為效忠對象?戰後,德國新教和天主教都日漸衰微,甚至比在嚴酷壓迫下的納粹統治時代的影響力還要小。在德國乃至整個歐洲那些飽經滄桑仍金碧輝煌的大教堂中,除了少許白髮蒼蒼的老人,就是蜂擁而至的亞洲遊客。
何謂「歐洲文明」?
德國和歐洲的知識分子是最反對宗教(基督教)的一群人,他們認為,德國和歐洲的身分不能建立在基督教基礎上,因為德國和歐洲國家正變得越來越世俗化,大部分還成了擁有多元化宗教信仰的社會。
英國學者斯蒂芬.葛霖認為,如果說存在一個與現代歐洲的宗教意識平行的東西,這種東西既不是基督教世界的統一,也不是神聖羅馬帝國宗教改革後奉行的「在誰的地盤,信誰的宗教」,它更類似於歷史學家吉朋對羅馬帝國晚期宗教生活的描述——「對於人民而言,所有宗教都一樣真實;對於哲學家而言,所有宗教都一樣虛假;對於政府而言,所有宗教都一樣有用。」
然而,這些自由派(左翼)知識分子無法解決的悖論是:如果抽去作為「屋角石」的基督教及其觀念秩序,「普世價值」還能剩下什麼?法國式的啟蒙主義能夠定義德國何以成為德國嗎?「普世價值」既然是「普世」的,又如何成為德國及歐洲的身分認同和核心價值?無法準確定義何謂「歐洲文明」的歐盟憲法的難產,絲毫不足為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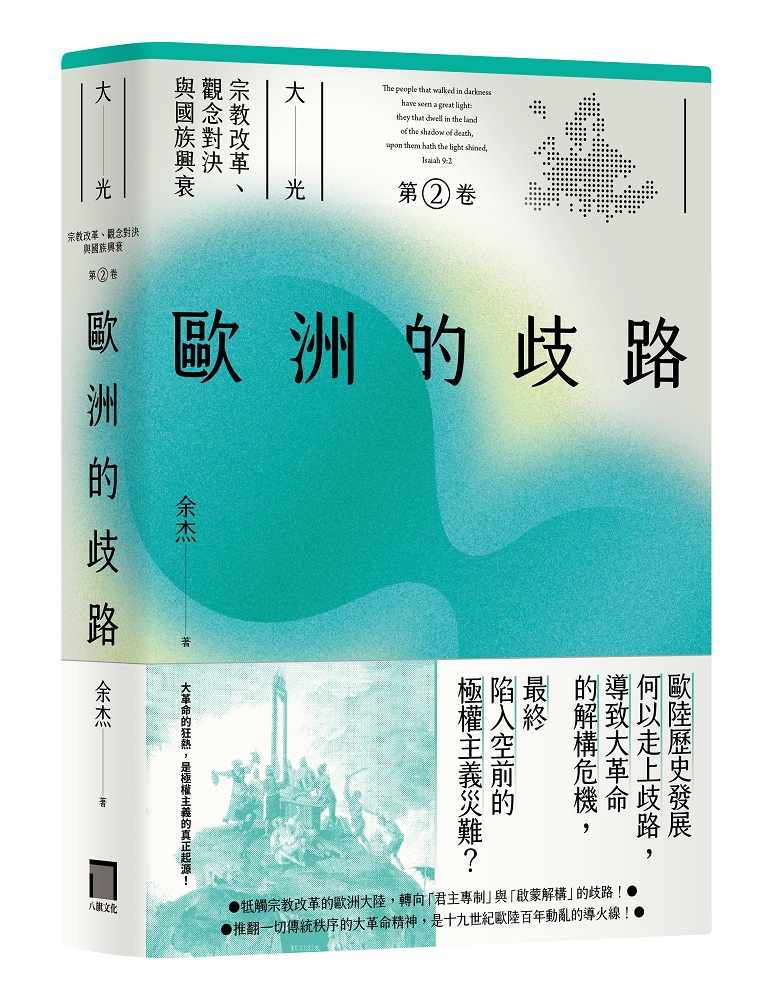
作者簡介
余杰
1973年生於成都,1992年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1998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暢銷百萬,其文字和思想影響了中國一代年輕人。2012年赴美,拋棄如同「動物農莊」般野蠻殘酷的中國,誓言「今生不做中國人」,並致力於在思想觀念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意識形態、解構大一統的中華帝國傳統,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徒精神與保守主義價值,也就是其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
余杰集政治評論家、散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倡導者於一身,著作六十餘種,涵蓋當代政治、古典文學、近代思想史、民國歷史、台灣民主運動史、基督教公共神學、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等多個領域。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公民勇氣奬」等獎項。
著作包含《徬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在那明亮的地方:台灣民主地圖》、《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人是被光照的微塵:基督與生命系列訪談錄》、《1927:民國之死》、《1927:共和崩潰》、《用常識治國》等書。
※本文摘自《大光:宗教改革、觀念對決與國族興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