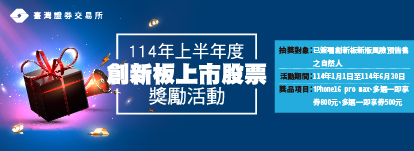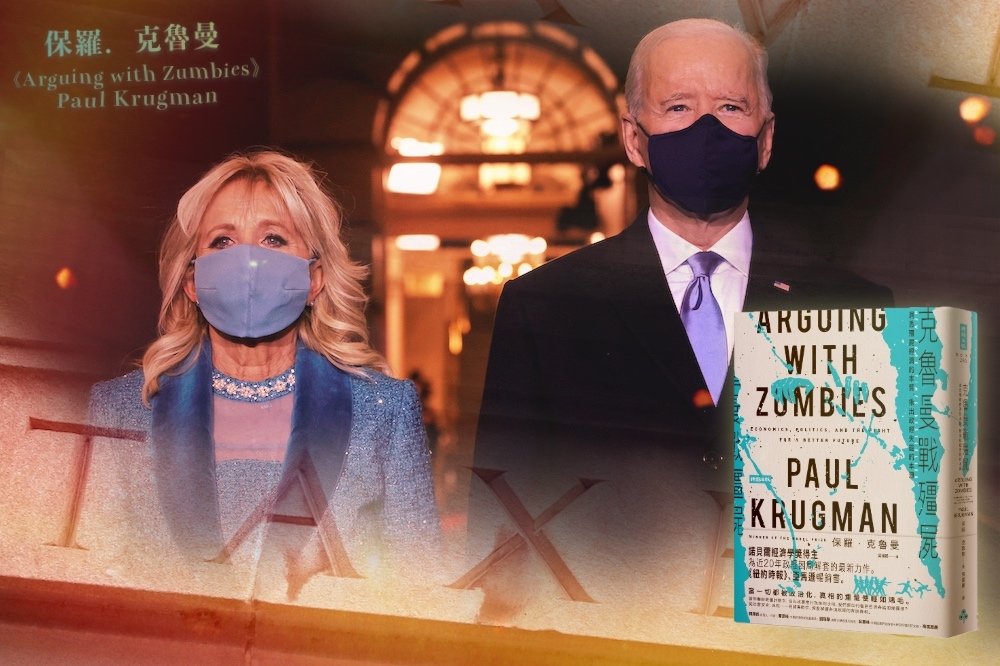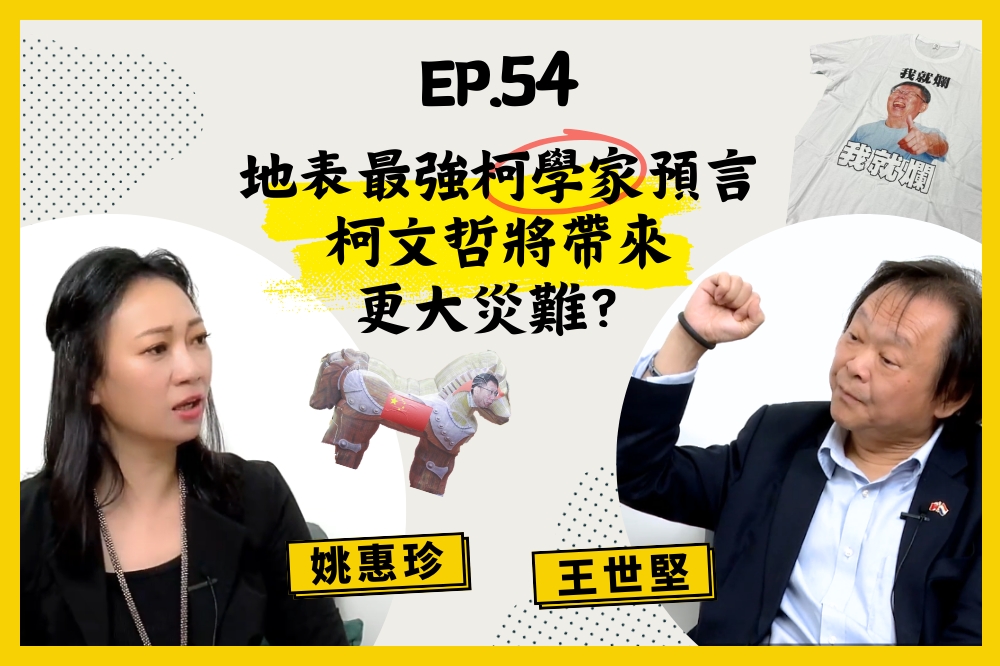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陳嘉宏專欄:什麼是「用更大的民主解決民主的紛爭」? 2024-12-23 07:02
- 最新消息 「時時香」華麗升級!瓦城集團新品牌「SHANN SHANN 小香」信義新光 A9 正式開幕 搭配紅白酒打造「新潮台灣菜」 2024-12-23 07:00
- 最新消息 民主與自由:台灣的價格與挑戰 2024-12-23 07:00
- 最新消息 【大巨蛋類地震】比照小巨蛋「禁跳令」? 北市議員:建管處可做周邊建物安全評估 2024-12-22 20:48
- 最新消息 【TPBL職藍】新北中信特攻邀海巡署長張忠龍開球 號召青年一起守護海洋 2024-12-22 18:56
- 最新消息 俄烏戰爭下是否該抵制〈胡桃鉗〉 立陶宛文化部長發言重掀激辯 2024-12-22 18:55
- 最新消息 柯建銘稱財劃法有折衷批韓朱卻硬幹 朱立倫:邊打邊談算哪種協商? 2024-12-22 18:52
- 最新消息 準颱風「帕布」水氣周一來會更濕冷 周五夜冷氣團再襲低溫下探13度 2024-12-22 18:25
- 最新消息 高捷列車車門「錯位」手動停靠引議 官方:安全無虞、深表歉意 2024-12-22 18:18
- 最新消息 【迎接2026】台北101跨年煙火搶先曝光 聚焦12強奪冠、融入台灣流行樂 2024-12-22 17:58

荷包縮水只能怪在機器人身上嗎?(湯森路透)
我在中產階級社會長大。從各種意義看,它不平等:大公司執行長的平均薪資是一般勞工的約二十倍。但有一種普遍的感覺是,除了那些極少數人外,其他人都生活在相同的物質世界。
那種情況已不復可見。現在的執行長薪資是一般勞工的三百倍。其他高所得族群的薪資也大幅增加,但過去四十年來,一般勞工的薪資在調整通貨膨脹後只見小幅增長,或者紋風不動。
所得都轉移到一小群菁英身上
美國的傾斜到了一九八○年代末已明顯可見。對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來說,這似乎是壞事。這不僅意謂一般家庭未能分享經濟的進步,而且意謂我們生活在一個共享社會的感覺逐漸淪喪。所以有人可能期待社會嚴肅地討論這種不平等加劇的背後力量,以及可以怎麼做以扭轉這個趨勢。
今日確實已經有許多嚴肅的學術研究探討不平等的原因和結果,可想而知,這也引起殭屍們的群起圍攻。畢竟,承認不平等大幅上升可能導致我們想辦法解決它。因此,幾乎從一開始就有某種否認不平等的產業──有點類似否認氣候變遷的產業──宣稱不平等並沒有真的上升,或者它無關緊要。
有一個較微妙的問題多年來充斥著不平等的討論,它牽涉三個廣為散播的誤解:
第一,是不平等上升主要是受較高教育的勞工生活比受較少教育者好,而不是受較高教育者中的一小群人把所有其他人遠遠甩在後面。
第二,是一種有時候不是出於善意的頑固說法,即藍領勞工的所得減少反映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如家庭價值沒落。我們看到美國勞工階級社會地位下跌的表徵是機會減少的結果,而非原因。
第三,是一切都是科技惹的禍,知識產業的成長需要高教育勞工,或機器人取代所有的勞工。原則上這可能是真的,但正如我在〈別把低薪資怪在機器人頭上〉裡談論的,證據顯示科技與不平等上升的關係遠比許多人想像的小,權力關係的影響大得多。
〈別把低薪資怪在機器人頭上〉
Don’t Blame Robots for Low Wages/ March 14, 2019
有一天我發現自己在一場會議中討論薪資落後和不平等激升(正如我常做的那樣)。會中有許多有趣的討論,但引起我興趣的一件事,是有多少與會者直接假設機器人是問題的一大主因──機器人搶走了許多好工作,甚至所有種類的工作。有許多時候,這一點甚至不是以一個假設被提到,而是當作每個人都知道。
而這個假設對政策討論卻有實質的影響。例如,許多有關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熱烈討論,是基於相信隨著機器人末日降臨,工作將變得愈來愈稀少。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指出:每個人都知道的那件事並不是事實,似乎是個好主意。預測很難,尤其是有關未來的預測,而且也許機器人總有一天真的會取代我們所有的工作。但自動化並不是過去四十年影響美國勞工因素中的重要部分。
我們確實有一個大問題──但它與科技只有很小的關係,與政治和權力則有很大的關係。
讓我們後退一會兒,並且問:機器人到底是什麼?顯然機器人不一定看起來像C-3PO(電影《星際大戰》中的機器人角色),或者到處滾動著說「消滅!消滅!」。從經濟的觀點看,機器人是泛指使用科技來取代以前人類做的工作。
而從這個定義來看,機器人已改造我們的經濟好幾個世紀。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李嘉圖(David Ricardo)一八二一年就曾寫過機器的破壞效應!
今日,當人們談論機器人末日時,他們通常不會想到露天採礦和炸開山頭採礦,但這些技術絕對改變了煤礦開採:煤產量從一九五○年到二○○○年幾乎增加一倍(直到幾年前才開始減少),但煤礦工人的數量從四十七萬人減少至不到八萬人。
再想想船運貨櫃化。碼頭工人過去是主要港口城市風景的一大部分,但雖然全球貿易從一九七○年代起直上雲霄,美國從事「海運貨物處理」的勞工比率卻減少了三分之二。
所以,科技破壞不是新現象。儘管如此,它正在加速嗎?根據資料顯示並沒有。如果機器人真的正在大量取代勞工,我們會預期看到剩下的勞工平均製造的產品數量──勞動生產力──大幅增加。事實上,生產力從一九九○年代中期到二○○○年代中期成長的速度比後來還快很多。
所以科技變遷是一則老故事。新奇的是,勞工未能分享到科技變遷的果實。
我不是說應付變遷是容易的事。煤業僱用的勞工減少對許多家庭造成破壞的效應,而過去煤鄉的許多光景也一去不復返。港口城市的人力工作流失當然是七○和八○年代都市社會危機的原因之一。
雖然科技進步向來會有一些受害者,但直到一九七○年代生產力成長才轉化成絕大多數勞工的薪資增加。然後這個關聯性被打破了,而且打破它的不是機器人。
打破它的是誰?愈來愈多、但並非全部的經濟學家皆有一個共識,即薪資停滯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勞工的談判權式微──而其根源則完全是政治。
最顯著的是,在過去半世紀,聯邦最低工資在調整通膨因素後下跌了三分之一,即使勞工的生產力增加了一五○%。這種背離是純粹、完全政治性的。
在一九七三年私人部門的勞工加入工會的比率占四分之一,現在只占六%。工會的沒落表面上可能不是政治性的,但其他國家沒有看到類似的沒落。加拿大現在的工會化程度和一九七三年的美國一樣;在北歐國家,工會會員占勞動力比例高達三分之二。讓美國成為例外的是,一個對勞工組織充滿敵意和對打壓工會的僱主友善的政治環境。
而工會的沒落造成極大的差別。想想卡車司機的例子,過去這是一個好工作,但現在的薪資比一九七○年代少了三分之一,而且工作條件極為糟糕。為什麼有這種差別?去工會化是很大的原因。
而這些可以輕易量化的因素,只是我們的政治中長期的、全面的反勞工偏見的幾個指標。
這帶我回到為什麼我們談論這麼多有關機器人的問題。我認為答案是,這是轉移注意力的伎倆──一種避免面對我們的體系被操縱成不利於勞工的方法之一,類似於談論「技術缺口」是把注意力從造成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壞政策轉移開的方法。
而特別是進步主義者不應該落入這種膚淺的宿命論陷阱。美國的勞工有能力且應該獲得遠比現在好的待遇。而探究他們未能獲得好待遇的原因,過錯不在我們的機器人,而在於我們的政治領導人。

作者簡介
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
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教授,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是《紐約時報》最受歡迎的專欄主筆、《時代雜誌》評鑑最佳的財經部落格作家。
克魯曼的文筆優美,美國經濟協會稱讚足以媲美日本的俳句、狄金遜的詩和馬蒂斯的油畫,《財星》雜誌讚揚他是自凱因斯以降,文章寫得最好的經濟學家,《華盛頓月刊》讚譽他為美國最重要的專欄作家。
1983年: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獲頒美國經濟協會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1994年:正確預言亞洲金融風暴而奠定經濟大師地位。1998年:榮獲德國柏林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倫敦政經學院百年教授尊榮。2004年:獲頒有歐洲普立茲獎之稱的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社會科學獎(The Prince of Asturias Award for Social Sciences)。2008年:因提出新的貿易理論、解釋全球產業內貿易現象,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克魯曼亦是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成員,曾經擔任紐約聯邦準備銀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以及葡萄牙、菲律賓等多個國家的經濟顧問。
譯者簡介
吳國卿
資深新聞從業人員,從事翻譯工作十數年。譯有《解密陌生人》、《Deep Work深度工作力》、《父酬者:姓氏、階級與社會不流動》、《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等書。
※本文摘自《克魯曼戰殭屍:洞悉殭屍經濟的本質,揪出政經失能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