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陳金德不公布審議委員名單挨批「官箴敗壞」 工程會發聲明回應4大爭議 2024-11-28 22:50
- 最新消息 北市教育局爆性騷 前副局長被控伸鹹豬手還留言「我想吃妳」 2024-11-28 22:25
- 最新消息 不用加班了!洪申翰要求同仁「六日開會」挨批 晚間宣布:延後至周一 2024-11-28 22:03
- 最新消息 【有片】俄羅斯大規模襲擊民生設施 烏克蘭百萬人頂0度低溫卻無電可用 2024-11-28 21:56
- 最新消息 公部門職場霸凌頻傳 衛福部擬增列公務人員身心調適假 2024-11-28 21:53
- 最新消息 道路施工鐵柱打穿地下道 騎士撞柱慘摔、新北市府重罰業者 2024-11-28 21:37
- 最新消息 健保罕藥專款恐歸零?王正旭、康照洲等人成立罕病委員會 陳莉茵盼共創「罕病照護政策升級方案」 2024-11-28 21:30
- 最新消息 大谷翔平紀念球吸人潮 賈永婕再爭取中華隊冠軍球於101展出 2024-11-28 21:03
- 最新消息 500元鈔票上「南王國小少棒」曾稱霸美國 資源不足曾解散、近年才得以重組 2024-11-28 20:35
- 最新消息 直播/健康台灣推動委員會第2次會議 20:30會後記者會 2024-11-28 20:30

《父親》的剪接跳躍、虛實跳躍,也漸漸平息下來,置換成一種詩意。(電影《父親》宣傳)
近年拍攝父親主題的電影,最佳首選佛羅萊恩·澤勒導演的《父親》。大陸譯《困在時間裏的父親》,港譯:《爸爸可否不要老》——其實英文原名就是The Father,很樸素,但也反襯出中文譯名不僅劇透而且縮窄了電影的寓意:實際上只要是父親,都困在時間裏,不只是片中這一位患上老人失智症的英國父親安東尼。父親節那天,看了這部意味深長的電影,讓我更理解我們的老父親。
電影是佛羅萊恩·澤勒根據自己的舞台劇《父親》改編,作為電影處女作,獲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在第93屆奧斯卡金像獎中獲六項提名,包括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配角,獲其中的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改編劇本;獲第78屆金球獎四項提名,包括最佳戲劇類影片;獲第74屆英國電影學院獎六項提名,包括最佳影片。
如此多的肯定,一方面是給83歲高齡的安東尼.霍普金斯精湛如入化境的演技(當然演他女兒安妮的奧利維亞.科爾曼也是影后級的,但兩者的區別在於安東尼像是本色出演,最後讓觀眾渾然不分演員和角色);一方面是電影本身不按常理出牌,複雜的時空人物調度,先讓觀眾如墮五里霧中,最後赫然面對現實時,已經被深深拉進角色的心內,悲其所悲,再慨自己之慨也。
因為複雜的調度,這部電影前4/5的部分,甚至被有的影評人稱之為「驚悚片」——的確,安東尼.霍普金斯當年在《沉默的羔羊》裏飾演的吃人狂漢尼拔實在太深入人心,自帶驚悚濾鏡。其實他在本片飾演的只是一個普通的阿茲海默症患者,在病情日益嚴重時拒絕家人僱用看護照顧,女兒把他接到自己家照顧他五年後,只好送了他去養老院。
電影一開始沒有明說這一切順序,而是像拍攝平行時空一樣把他晚年這幾個階段所處的時空,微妙地混剪在一起——你要很細心才能看出兩間公寓和養老院之間的異同,但這差異又滲進你的潛意識裏,讓你隱隱覺得哪裏不對勁。同時,一角由多人分飾的安排令這個魔方更加複雜,這一切,都讓人想起驚悚片經典《閃靈》(The Shining)。
慢慢的,隨着女兒安妮的淚水、她的無奈,我們也漸漸明白,這一切顛倒混亂是因為電影大部分在模擬的,就是失智症老人安東尼的視角——包括他的現實、心理、回憶和夢境。電影處理得如此圓融自洽,上一次我這樣深入一個老人的內心已經是多年前看福克納小說《當我彌留之際》了,現代小說慣用的意識流手法在電影裏直觀呈現,我們於是得到一個沉浸式體驗:體驗我們身邊老人乃至我們自己的未來可能遭遇的困頓和驚悚。
是什麼讓我們即使想明白了電影的時間線也仍然不能釋懷?那就是我們在兩個小時觀影中步步為營地闖過的驚悚感,對於老人安東尼,其實是他餘生的日常。除了無法辨認真偽的回憶空間,還有親人與陌生人的混淆,都令他難以接受又不得不強忍。
比如說那個化身為他主觀「記憶」裏的女婿的男醫護,也許就是我們常常聽說的老人院裏不堪壓力虐待老人的行兇者;電影裏他隱含的暴力威脅,與老人心中擔驚受怕的內疚感完美契合,於是才演繹出不知是真實記憶還是幻覺裏那一幕老人被掌摑的殘忍鏡頭。這樣的殘忍,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鏡頭,實際上不知道已經在老人腦海中上演過多少回。
而我們受的折磨,來自我們首先代入了:他孝順的女兒安妮的角色。她對安東尼照顧備至,也有無比的温柔和耐心,但安東尼對她是雙重傷害:一方面因為失智症的加重而漸漸忘記這個唯一的親人,並且懷疑她並不孝順,只是圖他的遺產;另一方面安東尼對早逝的另一個女兒露西卻念念不忘,固執地認為她沒有死——我們常說:死者是完美的,現實在照顧他的女兒反而顯得不如缺席的女兒。
這種誤解和委屈,大多數照顧家中老人的中年人都體會過,尤其在中國的普通階層。所謂久病床前無孝子,當電影閃現一個最可怕的鏡頭:安妮突然想勒死睡夢中的父親時(導演刻意模糊了這到底是安妮的幻覺還是安東尼的噩夢),我想不少觀眾都會理解並且有種悖德的釋懷感!
然而焉知這折磨其實也同時在安東尼身上。他力圖在女兒女婿、醫護等人前面保持尊嚴,但病情使他做多錯多,而且照顧者也因為失去耐心而忽略這種尊嚴的需要:就從老人堅持要換正裝才見醫護,女兒不當回事說穿睡衣就好一樣。失智症老人,就這樣慢慢從一個能撐起一個家的父親,退化成一個不獲信任的男孩,最後退化為嚶嚶哭泣尋找母親的幼兒……這固然是病情發展所致,也是照顧者無奈的放棄而生。
也許這是父親的宿命,從兒女來臨世界,父親就進入一部驚悚片中——他必須擔當勇鬥惡龍的騎士來保護他的家人。而現實的惡龍無所不在,既是咄咄逼人的生存環境,又是虎視眈眈你的幸福的各種危機,你不過是一個普通至極的父親——你的盔甲穿好了,最後變成壓垮你的重量。
「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不就是這個意思嗎?雖然漸漸喪失掉身外身內的一切,安東尼最惦念的還是老女兒安妮的幸福和已逝女兒露西的安息。最終他不堪重負,才能回到兒時,變回那個坦然接受撫養和愛的人。不過,按照阿茲海默症的發展,這時他離辭世也不遠了。
《父親》的剪接跳躍、虛實跳躍,也漸漸平息下來,置換成一種詩意。安東尼在嬰兒一般啜泣之前,他說了一句詩一般的句子:「我,我感到我全部的葉子都在落下離我而去……」——愛爾蘭大詩人葉芝,也在晚年寫過類似的詩:
「我在陽光下抖掉我的枝葉和花朵;
現在我可以枯萎而進入真理。」(《隨時間而來的真理》,翻譯:沈睿)
凡人不是詩人,安東尼所能依靠的不是詩和真理,只有耐心的看護凱瑟琳的肩膀。不過,導演還是慈悲的,他讓鏡頭緩緩搖出養老院的窗外,盤旋在無數閃爍新生的樹葉子上面,這也許寄寓了安東尼未來靈魂的輪迴,也寄寓了我們對父親的歉意——且讓我們接下來這些葉子,成為廕庇下一代的父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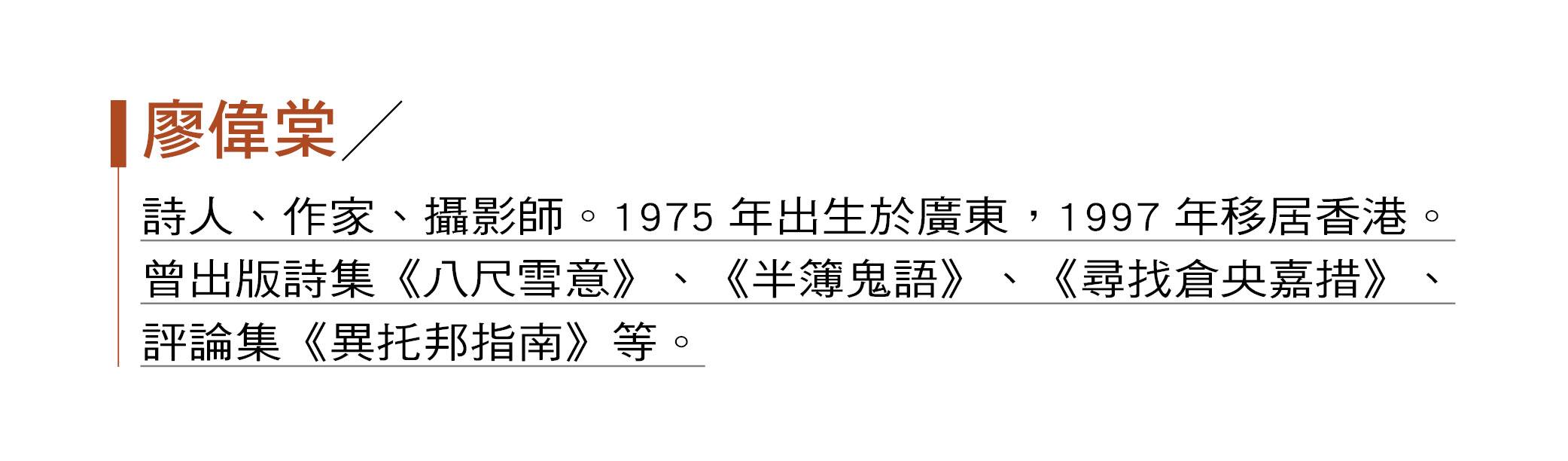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吳崑玉:以為來台灣會看到一個以色列 沒想到卻看到越南
- 傳賴清德想把500元鈔票改印「中華隊奪冠照」 央行確定發行12強紀念幣
- 【中華隊奪冠】麥當勞大薯買一送一!拿坡里、漢堡王、必勝客等 7 家速食優惠懶人包
- 《春花焰》吳謹言與老公洪堯牽手逛街孕肚藏不住 他因「這理由」挨轟沒擔當
- 中華隊最強捕手「林家正」介紹、IG!185 公分長腿、大胸肌迷翻家正婦 12 強冠軍戰炸裂東京巨蛋
- 《珠簾玉幕》大結局趙露思、劉宇寧生死訣別掀淚海 她與「崔十九」從宿敵變知己全網感動
- 【世棒爭冠戰】台日先發投手年薪差31.5倍 中華隊若奪冠每人獎金可望破千萬
- 台灣奪冠「沒用的香檳」最後去哪? 網友笑翻:原來帶去配和牛燒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