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連續數任防長遭罷黜 中國為何對解放軍高層進行大清洗 2024-11-27 20:51
- 最新消息 【總統催婚成功】郭俊麟單膝下跪向陳冠宇求婚 球迷嗨喊:一定要幸福 2024-11-27 20:40
- 最新消息 設宴款待馬龍、楊倩 馬英九邀陸生:明年一起泳渡日月潭 2024-11-27 20:10
- 最新消息 遭控花356萬「就業安定基金」開演唱會 許銘春、謝宜容列貪汙被告 2024-11-27 20:03
- 最新消息 蔣欣璋妻指控「邀老公去她家看貓後空翻」 戴湘儀反駁:有誤解、盼對方節制 2024-11-27 19:57
- 最新消息 LINE表情貼首翻新!舊版遭刪除免擔心 一招教你快速救回 2024-11-27 19:40
- 最新消息 【有片】英國首艘自主無人軍用潛艇完成測試 有助提升水下情蒐能力 2024-11-27 19:35
- 最新消息 【新北耶誕城卡司】孝琳、告五人壓軸 男團Energy、Ozone接力嗨翻舞台 2024-11-27 19:30
- 最新消息 王義川爭議多!失言挨轟「靠背川、王膝知」 批劉德華演唱會讓粉絲炸鍋 2024-11-27 18:45
- 最新消息 52年來最大暴風雪 首爾單日積雪20公分逾220架航班停飛 2024-11-27 18:25

我們即使僅僅看到《時代革命》的三分鐘預告片,就足以把我們關於2019年反送中運動裡許多刻骨銘心的記憶喚醒。 (圖片擷取自Variety推特)
坎城影展(Festival de Cannes)突襲宣布播映香港反送中紀錄片《時代革命》,自由世界皆稱讚其勇氣難得,但我並不意外。因為表達自由、直面歷史,是法國現代精神的基石,如果因為懾於中國壓力而從這兩點退卻,那才是荒謬。
坎城影展勇氣可嘉,周冠威導演的勇氣更是氣沖牛斗。在這明夷亂世,緹騎遍地的香港,他坦然以真名擔當這部電影的展演,無異乎以身為燭。我們現在尚未得觀看《時代革命》,但就以16日下午放出並被瘋傳的預告片看來,影像凌厲果斷,被訪者遍佈運動光譜,是一部誠意和戰意俱備的佳片。
恰好,我剛剛看了2019年金馬影展的強悍紀錄片,智利大導演帕特里克·古茲曼(Patricio Guzman)的《浮山若夢》(La Cordillera de los sueños,又譯《崇山夢魘》、《夢之山脈》)。和他的上一部《深海光年》相匹配,海水貌似無情,卻默默留下了皮諾切特政府虐殺反政府示威者的罪證;安第斯山脈屹然超越塵世,但也俯瞰塵世,讓那些背叛、傷害、剝削赤裸無顏。
《崇山夢魘》這個譯名,未免帶有太多感情判斷、出自香港譯者之手則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我們依然處於夢魘之中。但古茲曼是痛定思痛,譯作《夢之山脈》是一種處之泰然的中立說法。至於《浮山若夢》,最符合電影裡綿延不絕的安第斯山積雪與藍天相搖盪的迷幻感,但和李白「浮生若夢,為歡幾何」的聯想太密切,給人虛無詩意——而偏偏,古茲曼和紀錄片都反對面對智利歷史採取虛無態度。
是《浮山若夢》裡面的「戲中戲」讓我想到《時代革命》。古茲曼在採訪了許多創作涉及安第斯山意象的藝術家、尤其是異議、流亡藝術家之後,突然回到智利的街頭,找到一位民間紀錄片工作者巴勃羅·索拉斯Pablo Salas。古茲曼跟隨巴勃羅的腳步去到至今依然存在抗爭運動的街頭前線,採訪巴勃羅作為一個在皮諾切特時期依然堅持紀錄抗爭的點點滴滴的勇者的心路,並且選用了大量巴勃羅拍攝的素材——因為那個期間古茲曼流亡法國,無法第一身拍攝到自己的祖國。
巴勃羅,這個智利人常用的名字讓我想到智利最偉大的詩人巴勃羅.聶魯達,後者在皮諾切特政變後幾天去世,無從注視山河變色的漫長歲月,是不幸也是幸福,但要是他活著,只有像古茲曼那樣流亡一途。紀錄片工作者巴勃羅和詩人巴勃羅的相像之處,是他們都有巨大的韌性和幽默感,還有在關鍵時刻永遠把現實鬥爭需要放在創作的第一考量。
紀錄片對於我們來說,第一是記住,第二是喚醒,第三才是藝術。就像我們即使僅僅看到《時代革命》的三分鐘預告片,已經把我們關於2019年反送中運動裡許多刻骨銘心的記憶喚醒。巴勃羅的紀錄近乎瘋狂執著,我卻完全理解,因為這是在悶黑鐵屋裡除了吶喊你唯一可以做的事情:看見微弱的火光在哪裡、異議的聲音在哪裡、喘息聲在哪裡,你就轉頭去注視去記住。
但的確需要藝術才能深化前兩者,古茲曼的意義就在此。一如「故鄉記憶三部曲」前兩作(《星空塵土》《深海光年》),古茲曼本人的苦澀自白,隨時攜帶著他的成名作《智利之戰》作為電影的潛文本發聲。片中與「天地終無情」的崇山峻嶺並列的,除了留下來的艱險抗爭,還有流亡者的心路崎嶇,包括古茲曼,最後鏡頭那個徒手攀登陡立峭壁的無名攀山者,未嘗不是古茲曼本人的隱喻:他要用紀錄片越過不可能的時間巨壁,甚至使之逆流,回到他念茲在茲的「智利寶貴的童年」。
「我離開我的國家已經46年了,在這期間,我拍攝了20部關於智利的電影。我生活在國外的時間比在自己國家還要長。我習慣了在遠方拍電影,但日常獨自工作時我沒有一天不感到孤獨。在我的心底,我那被毀的家中揚起的灰塵從未散去。如果可能,我想重建我的家,重新開始……我的母親告訴我,每當夜晚空中有隕石落下時,你就可以許願 ,你要你不把它說出口,願望就會成真。但我想把它大聲說出來——我希望智利能夠重拾童真和快樂。」
古茲曼最後的話如此,海外離散的港人,讀之應是百般滋味。周冠威導演說他會留下不離開香港,但此刻他的電影已經走出香港在全世界流傳,這是香港人共有的心史——心在史在,反過來說也有深意:史在紀錄,則人心不死。
Webpage for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時代革命) on #Cannes2021🎬 official website includes a few snapshot images from the film.
Please visit: https://t.co/uB9ylltWt0 pic.twitter.com/V09qpy8mrB
—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重光團隊 (@Stand_with_HK) July 16, 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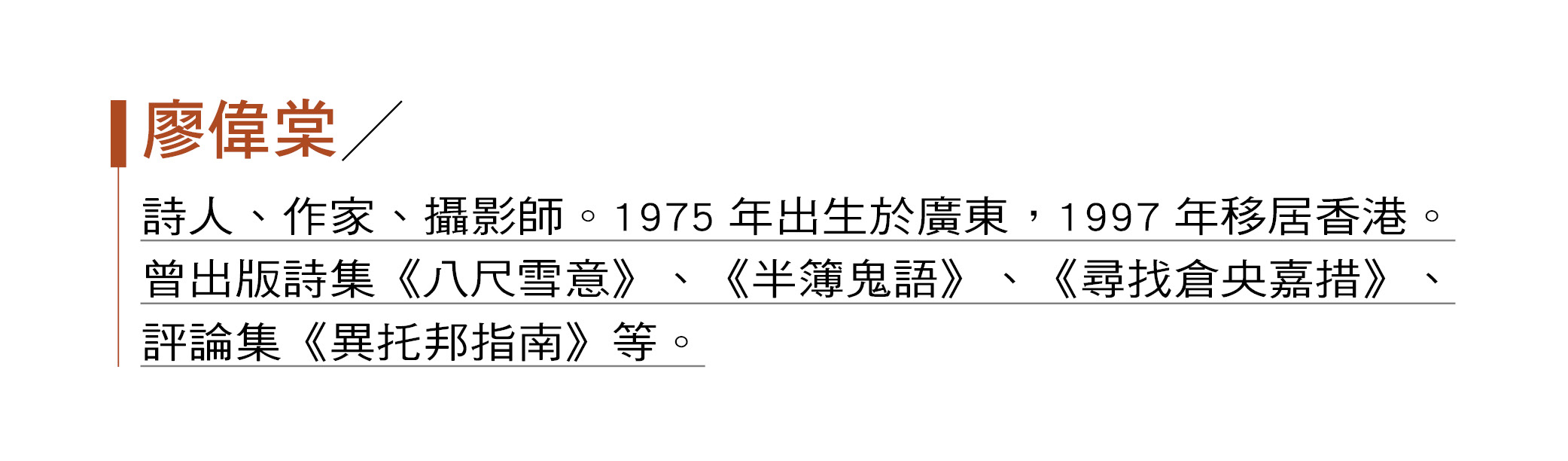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珠簾玉幕》大結局趙露思、劉宇寧擁吻訣別 她含淚哀求他「這句話」全網哭翻求番外篇
- 傳賴清德想把500元鈔票改印「中華隊奪冠照」 央行確定發行12強紀念幣
- 《深潛》成毅新劇搭檔《大夢歸離》古力娜扎 台灣女星演武林高手劇照曝光全網認不出
- 大風吹時間!《英雄聯盟》LCK 賽區各大戰隊轉會期 11/23 人事異動整理
- 《珠簾玉幕》大結局趙露思、劉宇寧生死訣別掀淚海 她與「崔十九」從宿敵變知己全網感動
- 【中華隊奪冠】麥當勞大薯買一送一!拿坡里、漢堡王、必勝客等 7 家速食優惠懶人包
- 【世棒爭冠戰】台日先發投手年薪差31.5倍 中華隊若奪冠每人獎金可望破千萬
- 《大夢歸離》侯明昊錄真人秀在非洲草原拉屎 全程被外國遊客拍下秒登熱搜糗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