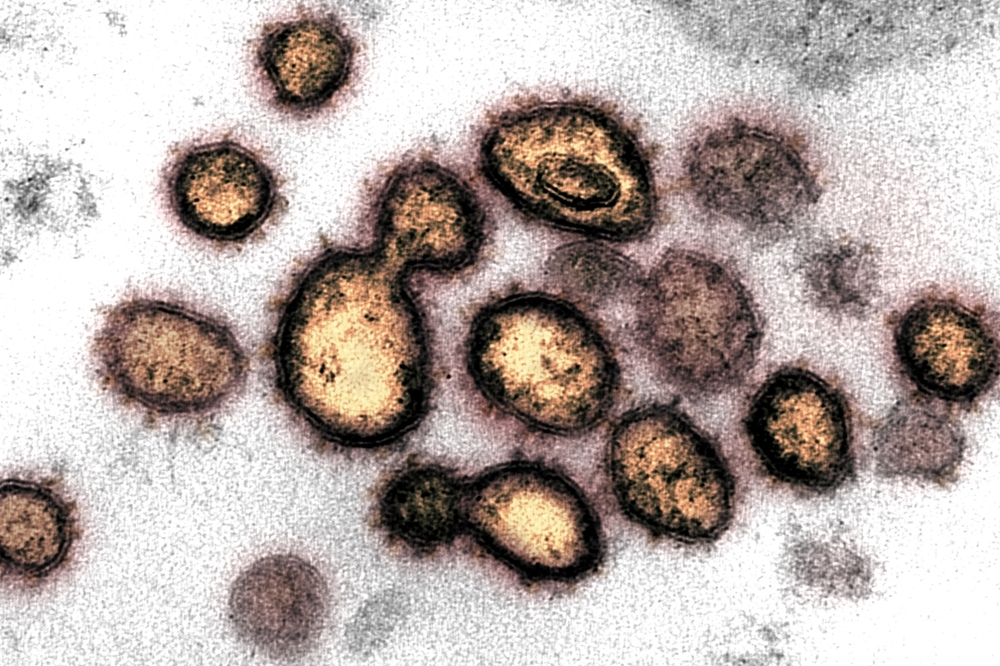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有片】露面了!謝宜容鞠躬道歉 落淚稱對不起家屬:孩子成冷冰冰遺體 2024-11-22 12:20
- 最新消息 不斷更新/【世棒四強賽】「中華隊 vs 美國」林家正、張政禹、陳晨威連續長打 中華隊4局上2:0領先 2024-11-22 12:18
- 最新消息 美特使還在以色列進行調停 以軍持續對黎巴嫩空襲釀47死 2024-11-22 12:03
- 最新消息 徐千晴重提高虹安「北一女案」 批大官對「良善」解讀與大眾脫節 2024-11-22 11:59
- 最新消息 《永夜星河》丁禹兮霸氣砸48萬買虞書欣封面雜誌 他這舉動暗藏「超甜細節」全網嗑翻 2024-11-22 11:44
- 最新消息 【擴大健保財源】健保署改革補充保費 擬增售屋、賣股票項目 2024-11-22 11:40
- 最新消息 對俄天然氣工業銀行祭出制裁 美財長葉倫:使俄軍更難取得資金 2024-11-22 11:23
- 最新消息 全聯隔日達改名「全電商」!每周六日一最高回饋 12.5% 黑五同步登場、爆殺品下殺 26 折 2024-11-22 11:00
- 最新消息 西方國家官員表示 北韓高階將領首度在俄國庫斯克地區遭攻擊受傷 2024-11-22 11:00
- 最新消息 快訊/賴清德再為「勞動部霸凌案」道歉 承諾嚴查嚴辦、檢討法令 2024-11-22 10:59

中國作為民族國家,尤其凸顯了民族主義的殖民主義特性。(湯森路透)
這兩日,中國藝人小S發了篇請「國手」到家裡吃飯的貼文,商案接連取消,一夜消失三千萬,他的姊姊可沒有幫忙說項:「習,屠殺我們」,畢竟我們知道這是現實上不可能,自我言論審查的基礎在於肉體消滅的真實可能性,在中國,沒有什麼離奇事。隨著,徐佳瑩只用了Emoji發表貼文,小粉紅也同樣出征,就連前中國球王林丹提到戴資穎實力比陳雨菲還好,你就不再是自己人,同樣給你出征。大中華民族感情不可侵犯乃是此等現象的命題,那什麼是辱華就是必須探索的問題。
所謂辱華,語意上是有他的意思,所謂侮辱就是對於他人人格之貶損,所謂華當然就是指中華,顧名思義,辱華即為侮辱中華。而什麼是中華?這恰好與美利堅相對等,美利堅是不同種族共同形成一個國家,但中華卻又是同一個種族(以漢人來說是大宗的中華而言)形成不同的國家。所以在國際間才有所謂「華人社群」這回事。
 小S(左圖)挺參加東奧的台灣國手,被中國網友出征,她代言品牌火速切割,連女兒Elly都受牽連。右圖為「壽全齋」終止小S代言聲明。(左圖取自臉書,右圖取自微博)
小S(左圖)挺參加東奧的台灣國手,被中國網友出征,她代言品牌火速切割,連女兒Elly都受牽連。右圖為「壽全齋」終止小S代言聲明。(左圖取自臉書,右圖取自微博)
但說實在的,很多概念進行還原之後會有更明晰的理解,例如說中國有沒有哲學?張喚民前陣子在八旗文化的書籍開宗明義告訴你沒有,甚至在書的開頭就提出了哲學來自於日本學者西周將 Philosophy 翻譯成為 「哲学(てつがく)」,再追溯而上當然就是回到希臘的 Philo Sophia,即愛智。前蘇時期到蘇格拉底對人自身認識的追索是當代哲學的起源,然而要說老莊孟是哲學,基本上就是中式新儒家的自慰隊,欺晃著「民貴君輕」乃中國幾千年前就有的「民主思想」,然而所謂儒家其實只不過是種治術,反而佛教還更符合「哲學」的意旨。
有道是:中國的宗教才是哲學,中國的哲學是宗教。不過是我說的。
所以我們把中華給還原,就像把中華台北給還原,其實中華就是「Chinese」, Chinese 更是在「中國」的原初概念,清末民初梁啟超乃為革新而隨民族國家潮流創建的「中國」,乃是將過往朝代(dynasty)概念給廢棄的創始人,所以你要說端盤服務生aka蘿莉控是國父還是梁啟超呢?自由心證吧。
所謂的民族(Nation)與種族是不同的概念,種族(Ethnic)是血緣、生理性上的,民族則是具有共同的情感認同群體聚合,根據 Bennedict Anderson 《想像的共同體》提到民族的建構像來自於於「語言」,原先說著各式各樣的「法語」、「英語」、「西語」而無法溝通的人們,在印刷媒介中產生互相理解,在這語言的「共時性」中認知到此語言場域中存在著數百、萬人的同胞,於是:語言創造了民族,民族也誕生於語言。
「掌控語言既是殖民統治,也是民族主義的共同特徵。」
民族的歷史並非編年式的,而是逆溯的,所以都是以今鑑古,後存的中國概念與領土卻成為千年不變的固定範域,忽視了歷史上只存在著朝代以及大大小小變動不居的統治領域,考古學所到之所,就是民族之源,甚至未竟之地也可透過神話充填,中華民族五千年來自於黃帝與蚩尤大戰,而大家也就這麼信了。其實這種想像不只發生在亞洲,就連1225年逼著英王約翰簽署大憲章的爵士們根本都不說英語,但卻是今日英國史的教材,民族主義的客觀現代性與民族主義者主觀的古老性、民族歸屬的形式普遍性與具體的特殊性、民族主義的政治力量與哲學的貧困,是民族主義的弔詭現象。
「非歷史的歷史主義是所有民族主義的特色。」
中國作為民族國家,尤其凸顯了民族主義的殖民主義特性,在我群與他者的民族式區分中,加上中國極權體制的潛規則特性,也就是依照張娟芬在《亡國感的逆襲》(同書名內文)所提到的無可預測性質,讓中國可以為所欲為而對國際擺態,再加上美國前先的歷史的帝國主義特性以及走在前的已開發國家地位,讓中國以開發中國家的受害者姿態更加猖狂。
這種恣意性(arbitrariness)正好是形容中國最貼切的形容詞,所以別人可以的我也可以,我可以的別人不一定行。所以,你不能說中國的運動員不夠好,即便你是中國的運動員,但是中國運動員可以在大清晨時期説:「我糙!」。而具體而微彰顯在凝聚成這個民族國家的個體間也是相同的,對於規則詮釋的任意性使得辱華不辱華是「我們」說了算,而我們是誰?「我們」就是中國,即便你國籍寫著China,即便你認同China,但只要一被「我們」給判定失格,你就被給取消。那又根據什麼判定呢?前說辱華有其語意上的內容,但在實際上卻因著中國(民族與極權國家)的恣意性質,使得辱華是說你是就是。

今日的親中派也才發現—或說早已知道但沒料到已經輪到自己,原來我這麼愛中國我也不是中國的一份子,其實倒也不盡然如此,而是「中國」的概念與標準正在緊縮,而民族的概念越需要凝聚之時都乃在於有外敵存在(例如奧運),18世紀各民族國家的形成也即在對法蘭西的反抗中成形。
而最不會去辱華的人,卻正正是知道如何才是辱華的人,然而這樣的「思想上辱華」在何時會成為「辱華」的實際,也指日可待,而當辱華的行為是包括現實上有或無辱華,那麼辱華不辱華也不再是宏旨,因為只要在這個政權的統治範圍之內,一切都是依照意志—而非規則決定何人是否適格。然而相較於歐美國家的取消文化,在極權國家的取消文化可不是社會性死亡,卻是物理性死亡。
但有趣的是,中國饒舌歌手(如果中國真的有饒舌)吳亦凡的性醜聞遭官方指令取消,卻引起凡粉聚集在天安門,看似低能但卻也未必,畢竟政治的偶像崇拜從毛澤東到蔣介石還是川普都遍存於今,而這樣的卡里斯瑪(Charisma)—超「凡」魅力反倒是韋伯提出的一種支配類型。我們覺得好笑是因為這群凡粉還沒達到可以顛覆中共政權的地步,如果人數多到跟法輪功七千萬人一樣多,公安還不把這些凡粉抓去活摘才怪。不過這也說不準,搞社運的寇延丁也不過搞搞社運,也被以顛覆國家政權抓捕去寫了《敵人是怎麼煉成的》一書,簡單來說,在這恐懼的共同體中惴惴惶惶將是一個沒有規則的世界,明日發生什麼事都無法預期,政治社群的解體將是回到魯迅說的吃人社會中。
尤其,中國歷史吃人也不只是種比喻,是真的吃了。
※作者為執業律師。寫作者。唯一的信仰只有知識。閱讀範圍主要是政治哲學、倫理學與女性主義。作品主要為書評、影評與政治社會評論。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起底謝宜容!傳身家背景雄厚「善做公關」 先生和綠營高層有交情
- 一元特典!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釋出「零星票券」,11/24 採實名制一般販售
- 【世界棒球12強賽】滿足「2條件」台灣確定晉級4強 今晚是關鍵
- 先搶先贏!Ado 五月林口體育館演唱會採實名制入場,11/19 輸入「指定代碼」可優先預購
- 【內幕】T112步槍裝彈器採購案疑專利侵權 以色列向軍備局寄存證信函
- 王一博金雞獎典禮被抓包視線離不開趙麗穎 網揭兩人4年戀情無法曝光背後真相
- 楊冪人氣暴跌與《慶餘年》張若昀演新片淪鑲邊女主 造型曝光全網夢回《三生三世十里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