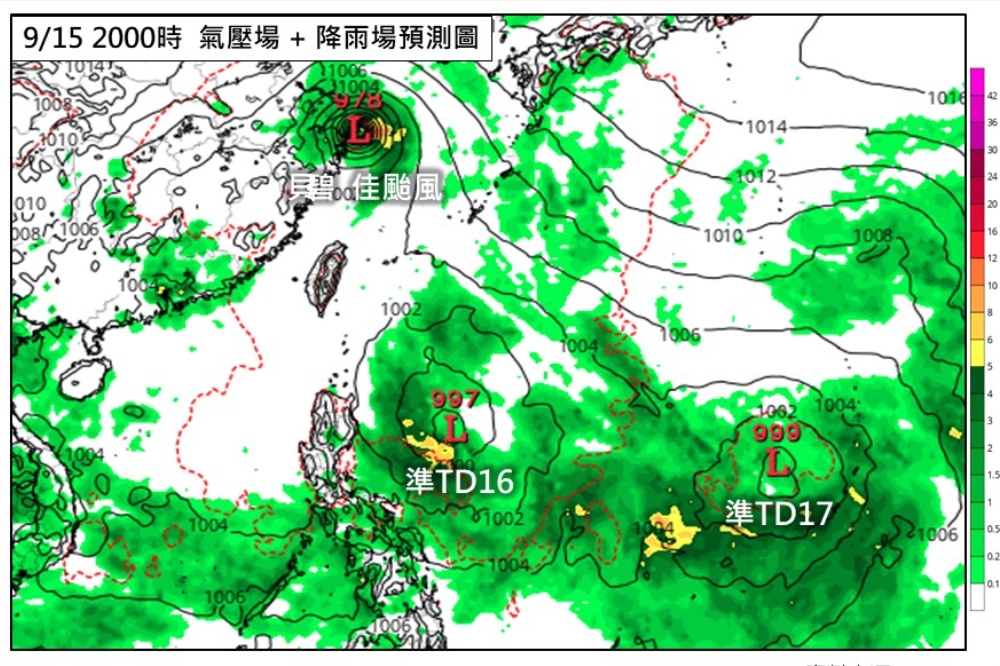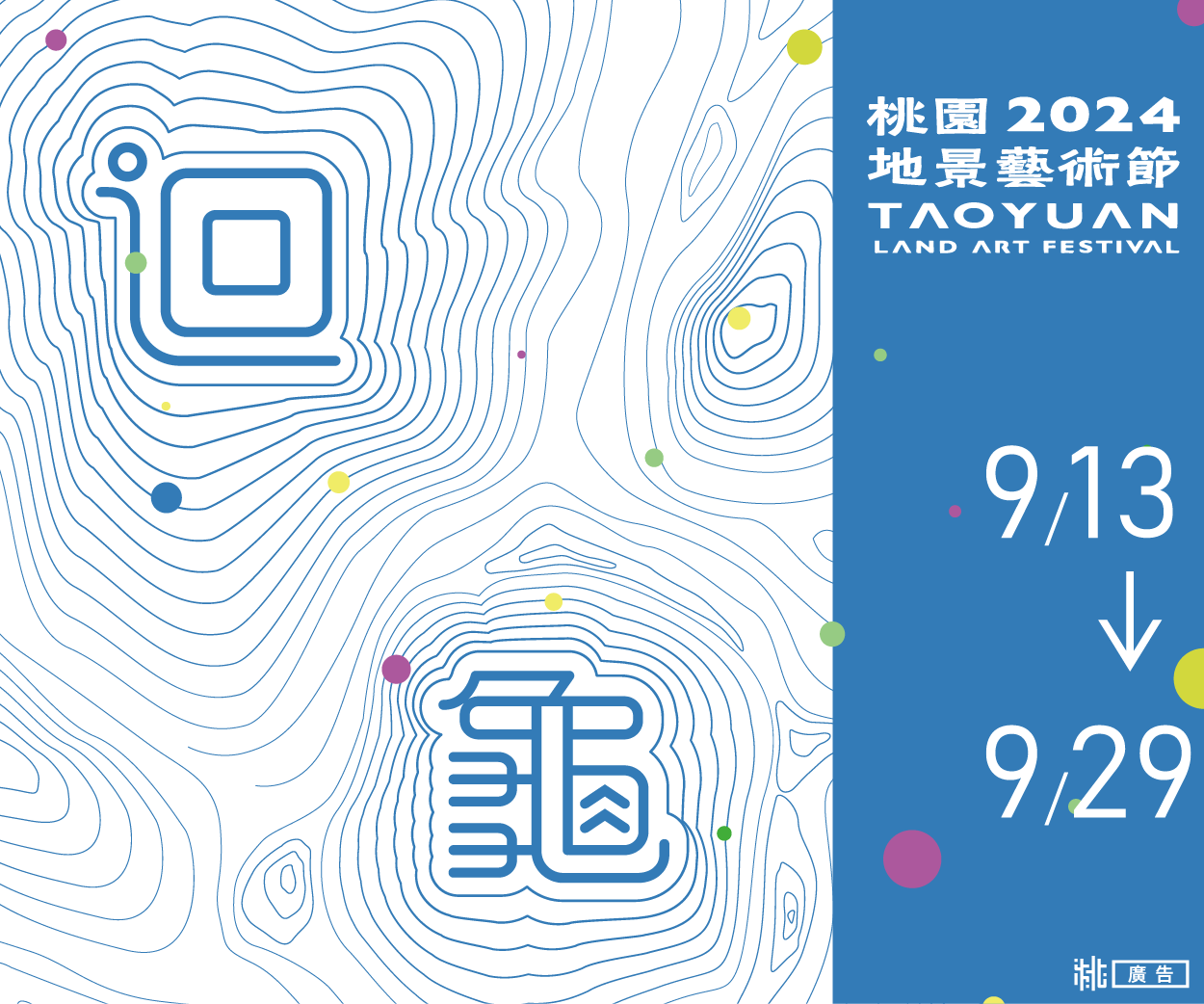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挺台!美副國務卿:中國以聯大2758號決議為工具損台灣地位 2024-09-19 09:20
- 最新消息 匈牙利否認台灣「貼牌」呼叫器在該國製造 BAC公司美女負責人也喊冤 2024-09-19 09:05
- 最新消息 最強法務出動!任天堂攜手寶可夢對《幻獸帕魯》開發商 Pocket Pair 提告 2024-09-19 09:03
- 最新消息 【潛艦國造】海鯤號海測改明年3月 顧立雄:重型魚雷分批交貨導致延4年結案 2024-09-19 09:00
- 最新消息 【潛艦國造】7艘後續艦逾2840億列公開預算 國防部須向公眾清楚交代 2024-09-19 09:00
- 最新消息 【敬老優惠】台北 5 間飯店自助餐推長青樂齡優惠 最高壯世代吃到飽享 6 折 2024-09-19 09:00
- 最新消息 【有片】黎巴嫩再傳日本製無線電也被引爆 造成至少20死450傷 2024-09-19 08:30
- 最新消息 【有片】聯準會一口氣大幅降息2碼 防止勞動力市場進一步惡化 2024-09-19 07:45
- 最新消息 李濠仲專欄:想像倫敦市長那樣訪美 蔣萬安就該反「扭曲2758」 2024-09-19 07:00
- 最新消息 【內幕】賴清德換人「連招呼都不打」 蘇貞昌點滴在心頭 2024-09-19 00:45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孟子.滕文公上》。(Pixabay)
十世紀晚期,冶鐵工業開始在中國北方的部分地區發展。有人估計到了一○一八年,工廠的煉鐵量一年已超過三萬五千噸以上,在當時來說,這是一項不可思議的成就;再過六十年後,產量甚至已超過十萬噸。不過,這並非政府經營的結果,而是在當時對鐵的需求量大、礦石和煤炭開採便利加上供應又充足下,民間私人企業抓住了這個機會。由於鍛造鐵的熔爐與鑄造場就坐落在可航行的運河水系旁,因此生產出來的鐵要運往遙遠的市場去就十分容易。中國的鐵礦老闆很快就從中獲得巨額利潤,於是繼續投資在擴張熔爐與鑄造場上,鐵的生產量也因此繼續大幅成長。鐵的大量生產,在農業上帶動了鐵製農具的使用,連帶影響了糧食產量的提升。一時間看來,中國已經開始發展資本主義,下一步就要進行工業革命了。但是突然間一切都被停掉,彷彿來得有多快、去得也多快一般。到了十一世紀末,鐵的產量不但變得少的可憐, 甚至在不久之後,原本冶鐵用的熔爐與鑄造所都淪為廢墟。這到底是怎麼了?
原來是朝廷大人們警覺到這些小老百姓正在透過製造業致富,還敢用高工資雇用農民工。他們認為這些行為對儒家價值觀和社會的穩定構成威脅。小老百姓應該要知道自己是誰,只有上層菁英可以是有錢人。因此他們就以國家之名壟斷了煉鐵工業,掌控一切之後,事情就這樣結束了。英國歷史學家溫伍德.里德(Winwood Reade,1838~1875)總結說,中國在數百年中發生了經濟上和社會上的停滯狀況,原因很簡單:「因為財產權沒有保障。其實整部亞洲歷史也可以用這句話來總結。」
一五七一年,在歐洲重創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勒班陀海戰(battle of Lepanto)中,歐洲海軍劫掠鄂圖曼戰艦時,也有一個同樣令人震驚的例子。獲勝的基督教海軍洗劫了還漂浮在海上或已擱淺的土耳其船隻時,在由艦隊司令阿里帕夏(Ali Pasha,1740~1822)所指揮的旗艦蘇丹娜號(Sultana)上,居然繳獲了大量寶藏和金幣。另幾位穆斯林海軍將領的戰艦上也找到了數目同樣可觀的財富。軍事史家維克多.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1953~)對此解釋說:「因為伊斯蘭世界沒有銀行體系,阿里帕夏將軍擔心一旦觸怒蘇丹,就會被抄家。同時也為了避稅, 所以一直小心翼翼地私藏自己的個人財產,在這次戰役中全都帶到了勒班陀。」不過,阿里帕夏將軍並不是那種在豐收後就想盡快將餘糧偷藏起來的農民暴發戶。他是伊斯蘭上層社會的一員,還娶了蘇丹的姐妹為妻。如果連他這樣一個有地位的人,都不敢把錢留在家中,也找不到適當又安全的投資管道,那麼其他小老百姓還能期待什麼?
這也難怪在專制政權統治下,社會都呈現進步緩慢又貧富不均的狀況。不只像阿里帕夏那樣,為了不被國家徵收,隨身帶著財產到處走,甚至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好比土地、作物、牲畜、建築物,還有你的子女,都有可能被任意強搶。正如中國那些大煉鐵家所遇到的狀況一樣, 這都是見怪不怪的生活日常。更慘的是,專制政權很少把剝削得來的財富再投資在增進生產上,只會用在各種炫富消費上,像是埃及的金字塔、法國的杜樂麗宮(Tuileries Palace)、印度的泰姬瑪哈陵(Taj Mahal),都是專制統治下建造的。這種紀念建築雖然美麗,但絲毫沒有任何生產價值,而且背後還付出了悲慘與貧窮的代價。這也是為什麼專制政權的經濟制度被稱作「統制經濟」(command economy),不論是市場還是勞動力,這兩者都處於受支配和強制的狀態, 根本不被允許自由運作。也因此,該如何剝削人民,再把財富消費殆盡,成為專制政權的主要目標。
最早的統制經濟,與國家一起誕生在這個世界,至今也還存在於現代世界的許多角落。事實上,統制經濟還有許多熱情的支持者。但是統制經濟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經濟生活事實: 所有的財富都來自於生產。財富的出現一定來自於生產活動,如種植、挖掘、切割、捕獵、放牧、製作或是其他創作。一個社會所擁有的財富數量,不是靠這個社會有多少人口總數,而是取決於人們在參與生產時的勞動意願,以及他們生產技術的效率高低。如果社會的財富全都會被徵收,或是隨時都處在被沒收的威脅中,對人們來說,該如何保住自己的財產就比提高生產效率重要多了。這個原則不但適用於有錢人,更適用於沒有錢的窮人,所以統制經濟總是會導致生產效率低落。面對只會肥到少數人的各種苛捐雜稅,即使是那些沒被奴役的自由農民,也只會想著該如何把收成的作物偷藏起來,而不是思考如何擴大產量。更何況那群被迫勞動的人,不管是奴隸,還是每年約定要義務勞動的自由農民,為了多得一點好處,唯一想到的方法就是盡量偷懶、少做一點。有錢有勢的人則輕視、冷眼旁觀、瞧不起那些身處在風險和障礙當中,勉強維持經濟、載浮載沉的人們。
八二九年,拜占庭皇帝狄奧斐盧斯(Theophilos,812~842)看到一艘雄偉華麗的商船駛進君士坦丁堡的港口,在問出擁有那艘商船的主人居然是自己的妻子時,立刻火冒三丈地向她怒吼: 「神讓我當皇帝,你卻讓我變成船長!」 立刻下令叫人把那艘船給燒了。在好幾個世紀當中, 拜占庭的歷史學家都歌頌他的這個事蹟,有可能那些古典哲學家對此也表認同。
亞里斯多德譴責商業貿易是一種不自然、不必要,並且與「人類德行」相衝突的行為。因此他認為,古希臘的公共廣場只能是聚會的場所,不可被當成是市場,此處不但「一定要乾淨到沒有任何商品,商家、工匠、農夫等等類似的社會階層也一樣,非得希臘行政長官的允許, 不得進入此地」。亞里斯多德還說,物品之間的交換只能在已有過社會關係的人之間進行, 最後結果還必須是互惠的價值。根據物品的重量和色澤,價值應該固定不變。
亞里斯多德的意見並不是曠野裡的聲音,而是希臘人的傳統觀念。勞動是奴隸的事,商業也不是希臘公民該做的事。根據經濟學者摩西.以色列.芬利爵士(M. I. Finley,1912~1986)的說法,希臘公民即使投資土地,背後真正的動力「是提高身分地位,而不是追求獲利的最大化」。
芬利爵士指出,在希臘原始文獻中完全沒有提到任何投資(包括放貸)、土地改良或製造業相關的內容,反而有「為了奢侈消費和政治協議的大額借款之相關證據」。
儘管羅馬的上層經常參與商業活動,也會對外放貸收利,但他們的態度根本上類似於亞里斯多德。君士坦提烏斯(Constantius,317~361,君士坦丁大帝之子)頒布的法令中說:「只要你是以下那些身分—最低賤的商人、換匯商、低級職員,或是卑微的服務業代理人,都別肖想享有社會地位或階級,因為這些人從事的都是沒用的工作,賺得都是無恥的利潤。」 在羅馬時代的希臘作家普魯塔克(Plutarch,46~125)看來,不只商業是不道德的,而且所有為了實際需求與現實事務相關的活動,都是「無知和庸俗的」。西塞羅(Cicero,BC106~BC7)也藐視地寫著: 「作坊內沒有任何高貴可言。」
也因此,羅馬帝國的衰亡不是一場悲劇性的挫折,要是偉大的帝國還繼續主宰世界,現在哪會有所謂的「西方文明」呢?如果羅馬還繼續統治世界,歐洲將陷入在統制經濟的野蠻泥沼中,也不太會有發明和創造。連帶影響下,世界的其他地區恐怕也會停留在十五、十六世紀的狀態,也就是歐洲人初見時的模樣。羅馬帝國根本是進步的敵人!
海耶克(F. A. Haye,1899~1992)對此解釋說:「沒有比這更大的誤導︙︙傳統的歷史學家把一個強大國家的成就,等同於文化發展的頂峰;其實那常常是文化發展的終結。」海耶克特別指出:「資本主義和歐洲文明之所以得以擴張,這當中的起源和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就在政治上沒被一統天下。」沒有什麼帝國體制能主宰歐洲,諸多小型政治實體的出現更具有回應內部利益團體的能力,這當中包括商人、製造商和工人的行會。地理當然也在歐洲的多元性上扮演了關鍵角色,但是對於政治理論的演進以及民主政府的建立而言,卻沒有直接的影響, 反倒是與中世紀歷史的許多面向一樣,基督神學才是政治自由實踐的思想基礎。

作者簡介
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
美國宗教社會學家,長期擔任華盛頓大學社會學和比較宗教學教授。目前是貝勒大學社會科學傑出教授,該大學宗教研究所的聯合主任,以及《跨學科宗教研究雜誌》的創始編輯。
譯者簡介
蔡至哲
筆名蔡安迪。臺大歷史系、歷史研究所、國發所博士。同時就讀政大宗教所博士。學術關懷在東亞儒學、基督宗教史。現職中研院博士後研究員、大學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