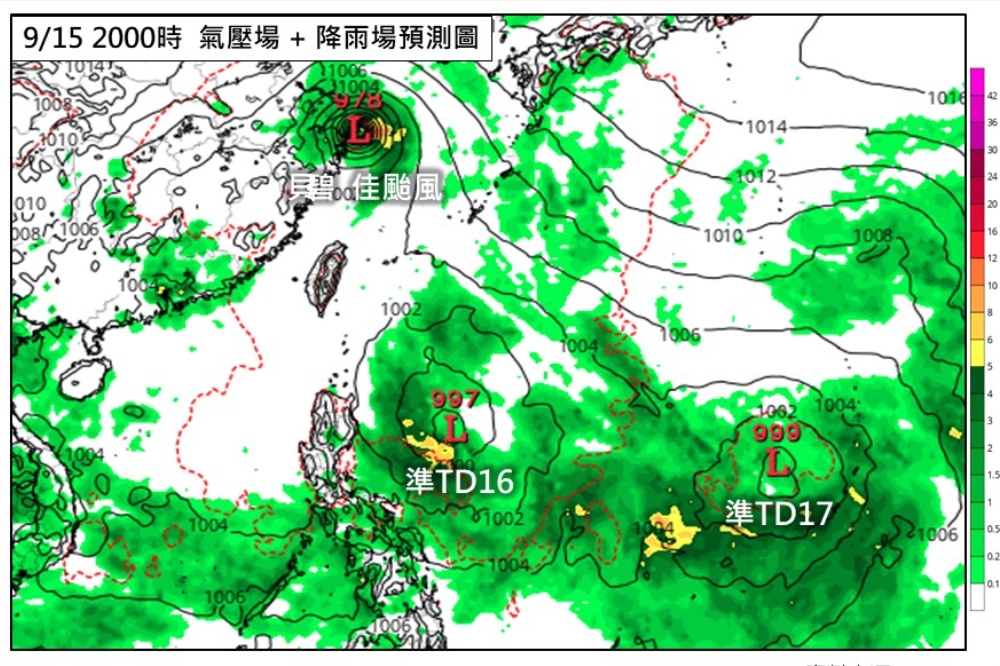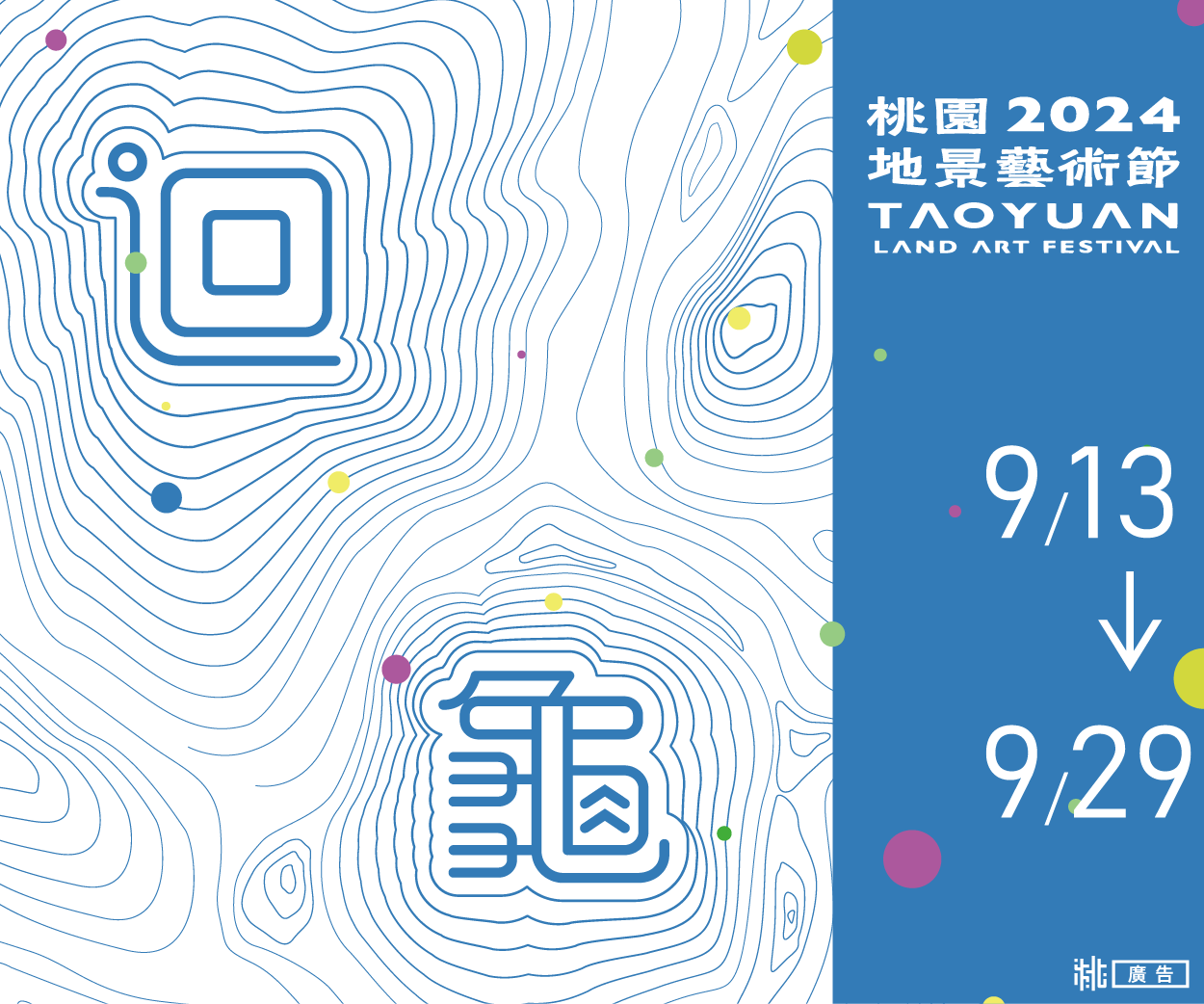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潛艦國造】7艘後續艦逾2840億列公開預算 國防部須向公眾清楚交代 2024-09-19 09:00
- 最新消息 【敬老優惠】台北 5 間飯店自助餐推長青樂齡優惠 最高壯世代吃到飽享 6 折 2024-09-19 09:00
- 最新消息 【潛艦國造】海鯤號海測改明年3月 顧立雄:重型魚雷分批交貨導致延4年結案 2024-09-19 09:00
- 最新消息 【有片】黎巴嫩再傳日本製無線電也被引爆 造成至少20死450傷 2024-09-19 08:30
- 最新消息 【有片】聯準會一口氣大幅降息2碼 防止勞動力市場進一步惡化 2024-09-19 07:45
- 最新消息 李濠仲專欄:想像倫敦市長那樣訪美 蔣萬安就該反「扭曲2758」 2024-09-19 07:00
- 最新消息 【內幕】賴清德換人「連招呼都不打」 蘇貞昌點滴在心頭 2024-09-19 00:45
- 最新消息 【內幕】李俊毅入主台鹽董座告吹 綠營「超重量級大老」親向層峰告狀 2024-09-19 00:30
- 最新消息 白黨雙黃別再散佈錯誤法律觀念 2024-09-19 00:01
- 最新消息 台菸酒董座丁彥哲轉換跑道 20日接任台鹽 2024-09-18 22:29

土耳其紅茶與砂糖。(陳品潔攝)
沒有「她」的土耳其茶館
我們在土耳其中部時曾經遇上一個卡車司機,他或許因為好客、又或許只是因為長途駕駛需要休息,在一個鄉間小鎮的茶館前停車,邀請我們一起下車喝杯茶。
帶領我們走進茶館時,卡車司機先是在空蕩蕩的茶館四處張望,然後對著我們說:「還好沒什麼客人,也還好你們一起出來,不然我還真的不知道怎麼帶妳來這裡。」他口中的「妳」,指的是和我一起搭便車的旅伴。原來在土耳其,女性光顧這種傳統小茶館,是件奇怪的事。
坐定後,司機跟送茶的小弟要來三杯熱茶,為我們驅除高原上的寒氣。我們圍著桌子用簡單的土耳其語,和司機說明我們如何從土耳其和保加利亞的邊界,一路搭了兩個禮拜的便車到這裡。離開茶館前,我的旅伴去了一趟洗手間,回來以後她有點困擾、又有點興奮地和我說,茶館裡「果然」連女廁都沒有。
乍看之下,茶館還真的是只有男人會來的地方。他們為了各種理由來此:看報、打牌、聊天、與朋友見面,有些甚至只是兩個行程間的空檔無處可去,便來茶館報到了。但無論如何,這裡都專屬於男人。不管是老闆、跑堂小弟,還是來此消費的顧客,清一色地全是男人。
就空間形式來說,傳統土耳其茶館的空間通常不是一個能讓女性感到舒服的環境。有時候,茶館裡的桌椅會擺得非常侷促,桌子也不是太大,除非有認識的男性同伴在旁,否則女性在這裡很難避免跟鄰座的陌生男人有肢體上的接觸。有些比較簡陋的茶館裡會使用較低矮的塑膠桌椅,女性要在這些貼近地面的椅子上維持「端莊」姿勢,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對於男人來說,這個可以放鬆心情、卸下心防,拉近彼此距離的座椅高度和桌椅配置,卻可能讓有些女人如坐針氈。
除了室內之外,茶館通常也會在店門口擺上一排椅子,以面向街道的方式排列;天氣好的時候,這些「露天雅座」頗受客人歡迎。椅子位於街道上、甚至全部面向街道,讓使用者視線得以向外(而不是面對面坐著),大概也意味這是一個「凝視者」的位置,可以自在地看著街道上來往的行人。對於以伊斯蘭教作為文化基底的土耳其來說,這些座椅通常也是專屬於男人的。
毫無意外地,司機婉拒了我們買單、請他喝茶的提議。他匆忙而篤定地將鈔票塞給跑堂的小弟,彷彿我們的好意冒犯了他。可惜司機的目的地是地中海岸,而我們則要繼續向高原東部走,沒有辦法跟著他的貨車前進太遠,最後他把我們放在貝雪希爾(Bey.ehir)湖畔的同名小鎮,就繼續往安塔利亞的方向開走了。
長途巴士司機澤其
我們沿著湖邊的小路向鎮上走,正好是日落前陽光最溫柔的時候。岸邊有把握陽光玩耍的孩子,還有枯木在染滿暮色的湖面上投射奇幻剪影。我們捨不得湖景,走得很慢,最後在黑幕完全籠罩天空之前才抵達埃許雷佛陸清真寺(E.refo.lu Cami)。埃許雷佛陸清真寺建於十三世紀,是安納托利亞高原上保存最完整的塞爾柱(Seljuk)清真寺,也是這個沒什麼知名度的小鎮最自豪的觀光景點。塞爾柱時期的清真寺與一般人印象中的土耳其清真寺不同,受拜占庭風格影響較小,所以沒有大穹頂,也沒有宏偉的室內空間,只有古樸的木製廊柱和平頂的天花板,寺內帶點壓迫感的空間,竟和茶館有些相似。
我們吃過自己帶著的乾糧後在清真寺後方找到合適的紮營地點:一輛大型遊覽車和草叢之間的縫隙。那個縫隙很窄,卻剛好足夠容身,在遊覽車和夜色的巧妙掩護下就算路人經過,也很難發現我們。
漂泊時,最開心的莫過於找到容身之處。帳篷圍塑的空間疆界明顯、範圍固定,而且還可觸可控,相對於移動的不定,總能帶給我們安全感。這種可以快速搭建、也可以快速拆卸的安全感,也許就是我們如此著迷這種旅行方式的原因。我們一邊得意自己居然找到這麼巧妙的遮蔽,一邊喜孜孜地搭起帳篷,然後鑽進帳篷裡倒頭就睡。
可惜掩護固然巧妙,但終究並不可靠。隔天一早我們被轟隆隆的引擎聲吵醒,趕緊爬出帳篷,才發現遊覽車正要緩緩開走,而我們的帳篷也少了掩護,在光天化日之下接受路人打量。
我們有點難為情地收拾好帳篷,扛起背包往小鎮邊緣走。
沿著聯外道路走了半小時之後,我們終於抵達通往科尼亞(Konya)的十字路口。在搭便車比搭計程車還方便的土耳其,我們每次攔便車都會計時,期待著不斷刷新最短等車時間的紀錄。那天早上我們的紀錄是三分鐘。為我們停車的光頭大叔,當時正要開車去科尼亞的汽車保養廠。
大叔的名字叫澤其,平時是一個長途巴士司機,經營不少副業,是個成功的商人。他在衣索比亞擁有大片農園,經商的足跡還到達過蘇丹和烏克蘭,幾年前又開始經營土耳其到聖城麥加的巴士路線,載送穆斯林前去朝覲。後來蘇丹和烏克蘭相繼陷入內戰,而土耳其通往麥加路上必經的敘利亞也成為國際強權角力的戰場,他自嘲自己是個掃把星,人走到哪,戰爭就打到哪。有次在敘利亞,澤其親眼目睹一輛近在咫尺的巴士爆炸,逃過一劫的他決定從此不再做朝覲的客運生意,改從麥加運聖水過來給那些「迷信」的穆斯林喝。
「我自己才不喝。不就是水嘛。」澤其市儈地笑著,或許和鄂圖曼帝國過去的統治者有點相似。據說有些土耳其蘇丹不是虔誠的穆斯林,一邊宣稱自己是穆斯林世界的哈里發共主,一邊卻又籠絡基督徒和東正教徒,甚至會在皇宮裡偷偷喝酒,總讓人搞不清楚他們到底是兼容並蓄,還是精巧世故。那些蘇丹也掌控了通往麥加朝覲的路線,成為聖城和朝聖者的保護者.還在做朝覲客運生意時的澤其,大概也能如此自居。
我們原本沒有打算在科尼亞這座城市停留太久,吃過午飯後就繼續搭便車向東。沒想到,澤其隔天正好就要開遊覽車載學生去卡帕多奇亞(Kapadokya)校外教學。
「不如我現在載你們去科尼亞逛逛,晚上你們回我家住一晚,隔天再搭我的巴士過去吧。」
於是當天晚上我們又回到了貝雪希爾,只是這次我們不在清真寺後面找掩護,而是住進了澤其在湖邊的家。
澤其自豪地向我們展示客廳,要我們放心休息,然後就轉過身去、收起笑容,吩咐妻子準備晚餐。雖然澤其從來不上清真寺做禮拜,但妻子朵朵卻像土耳其鄉間的其他女性一樣,只要出門必戴頭巾。
也難怪澤其如此好客地邀我們回家。從頭到尾,真正為了接待我們而忙進忙出的其實是他的妻子。澤其只要口出指令,朵朵就為他在餐桌上多變出兩人份的晚飯,在客廳地板上安頓好兩張舒適的床褥。朵朵什麼都沒說,總是微笑地向我們表達善意,但我們卻暗暗覺得不安,好像自己的唐突到訪只是加重了她的家務負擔。
相較之下,澤其才剛上小學的兒子歐古茲(Oguz)更像二號主人。歐古茲還有點嬰兒肥,面對我們兩個陌生人,他雖然起初有點害羞,但習慣之後便像爸爸一樣癱在沙發上對著電視機目不轉睛,像是我們不存在似的。
隔天吃早餐時,澤其說校外教學的行程延後一天,但他可以帶我們在鎮上晃晃。飯後我們坐在車裡看氣氛衰頹的村子,很快就發現,澤其可能是整個村子最體面的人。他的獨棟房屋嶄新氣派,遠離其他親戚鄰居;他經常在國外遊走,藉此避開湖區冬日的寒凍;他不斷買入新的轎車,最新的就是前一天我們在路口搭上,準備要送去保養的那輛。
不管我們一起走到哪裡,澤其都會興奮地向別人介紹我們,熱情地用他不算流利的英語為我們充當翻譯。頻繁出國的澤其一直都是這個村子、這個鎮上,少有的對外窗口.而澤其似乎以此為榮。
經過湖邊的沼澤地後,我們的目的地是村子裡的烤餅坊。烤餅坊供應全村日常所需,卻只是個簡陋的泥屋;如果整棟泥屋都被放進某個民俗博物館裡,或許也不會讓人覺得意外(可能裡面還會有幾尊蠟像)。在泥屋裡工作的三個女人都是澤其的姑媽,有人負責揉麵團、有人負責把麵團攤平放入烤爐,汗珠從她們布滿皺紋的臉上涔涔滲出。我們獲得了兩片剛出爐的麵餅,配著有點酸臭的乾酪,一邊咀嚼一邊想像那就是「前現代」的味道。
又見茶館
下午,我們繼續跟著澤其和朵朵去親戚家串門子,順道吃了兩頓土耳其式的下午茶。我們用簡單的土耳其語搭配地名和大家解釋我們的便車旅行,在場的女性都露出了匪夷所思的表情看著我們。聚會結束後,澤其又帶我們去了他在鎮上的辦公室,見識他口中那些遠從麥加而來的聖水。
大概是想不到還可以帶我們去哪裡,又或者只是他習慣喝茶的時間到了,我們最後還是進了一間茶館.雖然一整天下來,我們早就已經喝掉至少十杯熱茶了。這次,茶館裡倒是很熱鬧,坐了不少談天說事的男人。
就空間功能來說,茶館是個不折不扣的公共空間。男人來此交換生活經驗,對政治情勢或時事發表意見,而負責打理家裡的女性卻不屬於這個公共領域。澤其說,有時候他覺得在家裡坐不住了就會來這裡報到,畢竟家裡白天還是「女人的地方」,來了茶館才能讓他放鬆心情。澤其帶我們來的這家茶館裡,牆上還掛著土耳其國旗和國父凱末爾的肖像;和父權體制高度關聯的國族主義在這些陽剛的茶館裡成為外顯的符號,實在很難讓人覺得只是巧合而已。
穆斯林的性別空間
空間帶有的性別屬性,在穆斯林社會似乎總是特別外顯。比如說,同樣是做菜這件事情,如果在家裡做,那幾乎毫無疑問就是女人的工作;但如果是在戶外,就得輪到男人捲起袖子。
我們曾經搭到一群土耳其大學生包下的廂型車,當時他們正要去某個公園野餐,於是順勢邀請我們加入。下車後,女人只是聚集在小屋子裡聊天,而劈柴、生火、備料和烤肉這些事情,則從頭到尾都只由男人進行。在我們看來,烹飪這件事情本身在土耳其並不帶有性別的刻板印象,真正和性別角色有關的其實是空間。話說回來,搭上便車後被載去一起野餐這種事情,我們在土耳其遇過不只一次,只能說土耳其人真的很喜歡野餐。
看著茶館裡談興高昂的男人們,我突然想到,前幾個月在伊斯坦堡待了兩週,怎麼就沒有對那裡的茶館留下什麼印象。但仔細回想,伊斯坦堡當然也有茶館,只是那裡畢竟是土耳其面向世界的門戶,又是土耳其世俗主義支持者的大本營,氣氛較為開放,諸如咖啡館、甚至酒吧之類的公共空間更為多元。相較之下,專屬男人的傳統茶館就不如鄉下來得醒目,多半位在舊城區的市場角落或者城郊。
朵朵當然沒有跟著我們一起到茶館來,而是繼續去拜訪鎮上其他朋友。少了妻子在旁的澤其更加口無遮攔,開始聊起他到處趴趴走時在許多地方結識的女人。講起這些女人,澤其不只不覺得有什麼好避諱,反而還顯得十分得意。有次他在其他地方相好的女人找上門了,朵朵氣得要鬧家庭革命,最後動起拳頭把那女人趕走。澤其一邊形容朵朵憤怒的樣子,一邊舉起手臂在空氣中揮舞,「你們知道拳擊嗎,就像拳擊那樣」。
看著澤其揮舞著手,我不禁想起我的父執輩們。他們在一九六零年代的城鄉洪流之中離鄉打拚,前腳剛踩上城市的柏油路,後腳卻還站在農村的泥地上。臺灣經濟起飛之後,他們的自信也跟著衝上雲霄。他們無法以外國語言流利對話,卻可以信手拈來幾個外語單詞讓你見識他的見識。他們很土,卻又總能在其他各種物質成就的應援下,有點賭氣、有點底氣地張揚地土。他們的背後,也總有個女人在家裡洗衣燒菜,對偶爾入侵家庭的其他女人憤怒強硬。
隔天早晨,我們終於搭上遊覽車,重啟我們延宕了兩天的旅程。旅行這麼久,我們什麼便車都搭過,但校外教學的遊覽車,還真的是頭一次遇到。
車子上路後,我們在滿車學童的喧譁之中隔著玻璃窗回望這個我們意外待了兩天的小鎮。現在回想,依然無比懷念這個在地表上積聚湖水的美麗裂縫,以及我們緊湊便車行程中難得的悠閒間隙。當然,還有澤其這位跨在裂縫上意氣風發的中年大叔,以及他背後那些總守著麵包爐和廚房,但就是不會出現在小茶館裡的女人們。

作者簡介
李易安
端傳媒記者,用移動做田野,以田野為生活,為田野而移動。怕鬼,但喜歡逛墓園;喜歡旅行,也喜歡紀錄,文章散見《端傳媒》、轉角國際、Matters;第13屆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獲選者,曾入圍亞洲出版協會(SOPA)卓越新聞獎。兼職翻譯,譯有《歐亞帝國的邊境:衝突、融合與崩潰,16-20世紀大國興亡的關鍵》、《啟蒙運動》等書。
《搭便車不是一件隨機的事》,是他出版的第一本個人著作。
※本文擷取自《搭便車不是一件隨機的事:公路上3萬5千6百公里的追尋,在國與界之間探索世界》,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