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蔡壁如宣布將參選民眾黨中央委員 台中市府顧問「該辭就辭」 2024-12-22 15:34
- 最新消息 【拳上2024爆衝突】統神遭攻擊後腦勺喊告 蹦闆道歉爆對手收20萬妥協 2024-12-22 15:25
- 最新消息 【嘉義悄布局】交棒蔡易餘後未必入閣 英系有意讓翁章梁卸任後選立委 2024-12-22 15:15
- 最新消息 【2025 福袋】小北百貨「金喜歡福袋」開箱!一袋只要 299 元 開袋即刮 iPhone 16、現金 6000 元等大獎 2024-12-22 15:00
- 最新消息 《玉氏夫人傳》林智妍從奴婢逆襲成朝鮮律師 男主角秋英宇戲中出櫃震撼全網收視狂飆 2024-12-22 14:45
- 最新消息 政治盟友倒戈將提不信任案 加拿大總理杜魯道明年1月恐被趕下台 2024-12-22 14:42
- 最新消息 美新預算案閹割投資中國限制 民主黨轟:服膺馬斯克中國利益 2024-12-22 13:10
- 最新消息 馬辣公館店變身時尚餐酒館!「馬辣心潮麻辣鍋」最低 698 元吃到飽、16 款酒品無限暢飲 12 月壽星免費吃九孔鮑魚 2024-12-22 13:00
- 最新消息 韓國瑜將率團赴美出席川普就職典禮 王定宇盼循蕭美琴模式 2024-12-22 12:58
- 最新消息 學者示警:《老人福利法》等3案也可能三讀 籲應停止傷害世代正義修法 2024-12-22 12:53

人類健康由誰買單?提供什麼服務?服務在哪裡提供?誰提供這項服務?(CC BY-SA 3.0 Nick Youngson @Pix4free.org)
一九九○年,特麗.夏沃(Terri Schiavo)在心臟驟停後,腦部嚴重受創,被診斷為永久性植物人。多年治療無效後,她的丈夫(也是法定監護人)於一九九八年請求幫她移除進食管。這個決定引發了他與夏沃父母的法律糾紛。雙方對簿公堂,案子歷經不同法院的審理、申訴程序,甚至訴請州長及總統協助。二○○五年,法院做出最終裁決,移除她的進食管。夏沃在兩週後過世,然而十五年處於植物人狀態下,她在醫療與臨終照護累計的成本高達數十萬美元。所有醫療系統的財務資源都是有限的,我們有必要質問,幫夏沃維繫生命的那些錢,用來挽救其他人的生命是否更好?
更廣義地說,這帶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如何分配有限的醫療資金最好?
我們賦予生命及生活品質的價值,最能反映社會對公平性的看法。在延長壽命或改善健康上的花費,顯示我們投資未來的意願。社會對公平的評估取決於影響那投資決定的因素,例如個人的收入、預期壽命、治療費用、成功機率,以及那些因素的權重。我們賦予健康的價碼會影響個人決定(例如是否抽菸)和社會決定(例如是否優待富人、營利組織或關切其他問題)。
人類健康沒有固定的單一價碼,這個價碼取決於多種因素,包括誰買單?提供什麼服務?服務在哪裡提供?誰提供這項服務?更廣義地說,這個價格取決於我們如何定義健康。為了方便討論,我們採用比較狹義的健康定義,亦即無病無傷的狀態。
我們考慮的是誰的觀點?
決定健康的價值,或者更廣義地說,決定生命的價值時,最重要的考量之一是:我們考慮的是誰的觀點。我們是討論營利事業嗎(營利事業需要決定它要給付哪些治療,不給付哪些治療)?我們是在描述憲法規定國家健保必須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時,應該涵蓋哪些服務嗎?我們是在討論一個人願意為了挽救自己或孩子的生命而支付多少治療費嗎?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會衍生不同的健康價碼,促成不同的建議行動。
健康的價值不僅是監管機構及營利事業需要考慮的議題,一般人日常的優先要務也與健康有關。你的健康決策反映了你在時間與金錢運用上的優先考量,以及你對健康風險的看法。這些決策顯示你在現實中多重視你的健康與生命。你午餐是點沙拉,還是吃漢堡配薯條?你抽菸嗎?你是走路、騎單車,還是開車上班?你是投保綜合健康保險,以涵蓋大部分的醫療費用,還是依賴災難險來支應超過某個高自負額的醫療費用,還是冒險碰運氣,根本沒有健康保險?雖然這些決定與其他決定可能會改善或損害你的健康,但是在健康方面,沒有什麼事情是一定會發生的。
健康是一種投資
在二○一○年全球健康倡議策略(2010 Global Health Initiative Strategy)中,美國政府指出健康的根本重要性:「健康是人類進步的核心,決定父母能否工作養家,孩子能否求學,婦女能否安全分娩,嬰兒能否成長茁壯。在衛生服務健全又便利的地方,家庭與社群蓬勃發展;在衛生服務難以取得、脆弱或根本不存在的地方,家庭受苦受難,成人早逝,社群分崩離析。」
這段敘述凸顯出一個重點:我們不該只把維持及改善健康視為開支。健康是一種投資,可以帶來很大的回報,因為健康是強大的助力。健康的人更有生產力,更有能力參與經濟成長,貢獻社會。我們往往忽視健康的存在,直到失去了健康才萬般懷念。

賦予健康一個價碼很難,而且就像評價生命一樣,充滿了爭議。駕駛教練曾經半開玩笑地對我說,萬一開車輾過行人,「倒車把他輾斃」可能更省錢。九一一罹難者賠償基金的賠償金額顯示,駕駛教練的說法確實可以套用在一些個案上,因為一些傷者的賠償金超過了死亡賠償金。同樣地,一些民事案件的判決顯示,傷害賠償金可能超過不當致死的賠償金。這種判決看似有悖直覺,但它的理由是:終生的醫療費用及失能限制可能是非常高昂的代價。這種邏輯很容易遭到批評,畢竟,我們還有另一種解讀的可能:我們對生命的重視不夠,只要賦予生命更高的價值,生命的價值將總是高於受傷的價值。
衡量指標與監管機構的責任
監管機構的任務是考慮社會受到的影響,而不是像營利事業那樣只關注淨利。不同的監管機構對健康的價值有不同的看法,那些看法會影響他們如何估算及使用健康的價碼。前面我們看到,環保監管機構使用「統計生命價值」來判斷,提高空氣、水、其他環保標準所拯救的生命及保護的健康可創造多少效益。提高環保標準也可以減少疾病與傷害的發生率。為可能的新法規做成本效益分析時,需要考慮新法規挽救生命及防止疾病與傷害的效益。健康受損的代價包括痛苦、虛弱、無法執行原本可行的基本功能、無法享受休閒活動等等。
對環境監管機構來說,要評估新環保標準對健康的效益,首先需要瞭解暴露在污染物下與罹病風險之間的關係。訂定水中毒素(例如砷)的可接受濃度時,需要先瞭解較高的砷濃度對健康有何影響,包括更容易罹患哪些疾病(例如癌症、心血管疾病)。同樣地,在規範燃煤發電廠製造的污染時,需要先瞭解主要污染物(例如二氧化硫)與它們造成的健康衝擊(例如支氣管收縮和氣喘增加)之間的關係。監管機構量化了污染物與疾病之間的關係後,接著會估計每種疾病可能影響多少人。最後,他們會為大眾健康受損及失去的生命附上價碼。
衛生技術監管機構做決策時,考量的因素與標準異於環境監管機構。衛生技術監管機構需要判斷,如何在固定的預算下拯救最多的生命。他們審查的技術類型包括藥物、裝置、療程(例如疫苗和抗生素、電腦斷層掃描與磁振造影,以及追蹤患者活動與服藥遵從性的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之類的數位健康技術)。衛生技術監管機構在評估是否投資衛生保健干預、藥物或療程時,考慮的因素很多,包括在成本與效益之間拿捏平衡。
例如,這項新技術對健康的效益真的值得花那麼多錢取得嗎?更廣泛地說,衛生保健規畫者(無論是政府、還是健保局)都需要決定投資報酬是否值得。無論採用哪種方法來評估健康成本,我們在很多其他的情況中看到,折現會使分析結果更有利於當前患者的健康,而不是未來患者的健康。折現也常導致大家對治療的重視,更勝於可能避免重大健康問題的疾病預防措施。
健康價碼
決定健康價碼就像決定生命價碼一樣困難。有開放的競爭市場可以交易產品時,很容易看到產品的價格。例如,我們可以輕易看到大家願意為雞蛋、柳橙汁、汽油付多少錢。但是健康不是在開放的競爭市場上交易的商品。我們不是直接在年初支付某個固定價格,以購買未來一年的健康。由於健康無法像商品一樣公開交易,健康的估價需要經濟學家開發出聰明的方法,為那些無法買賣的項目指定價碼。
衛生經濟學家設計了多種衡量健康價值的指標,包括一些追蹤健康成本與健康影響的指標。根據這些指標所做的決定可能產生深遠的影響,決定誰能獲得什麼樣的醫療保健。因此,這些決定會影響到誰的壽命得以延長,誰的壽命提早結束。儘管選擇一種衛生經濟指標而不選另一種指標可能產生很大的影響,指標的決定權往往落在技術專家的手中。若能對常用的指標及其影響做清楚的審查,對大眾來說是非常寶貴的,可以讓大眾更了解挑選某些指標的影響,然而現實中往往沒有這樣的審查。
指標的挑選是看決策者的觀點與優先要務而定,包括他們認為怎樣算「公平」。有些情況下,目標只是要盡可能降低醫療成本。在這種情況下,預算有限,他們會盡量削減成本,對健康受到的影響僅有些許注意。但即使唯一的目標是盡量削減成本,仍需考慮一些關鍵因素,例如預防醫學(目的是減少罹病機會)和治療醫學(焦點是治療需要護理的病患)之間的取捨。
※本文擷取自《人命如何定價:從法律、商業、保險、醫療、政策、生育等切面,探究社會為人命貼上價格標籤的迷思、缺陷與不正義》,臉譜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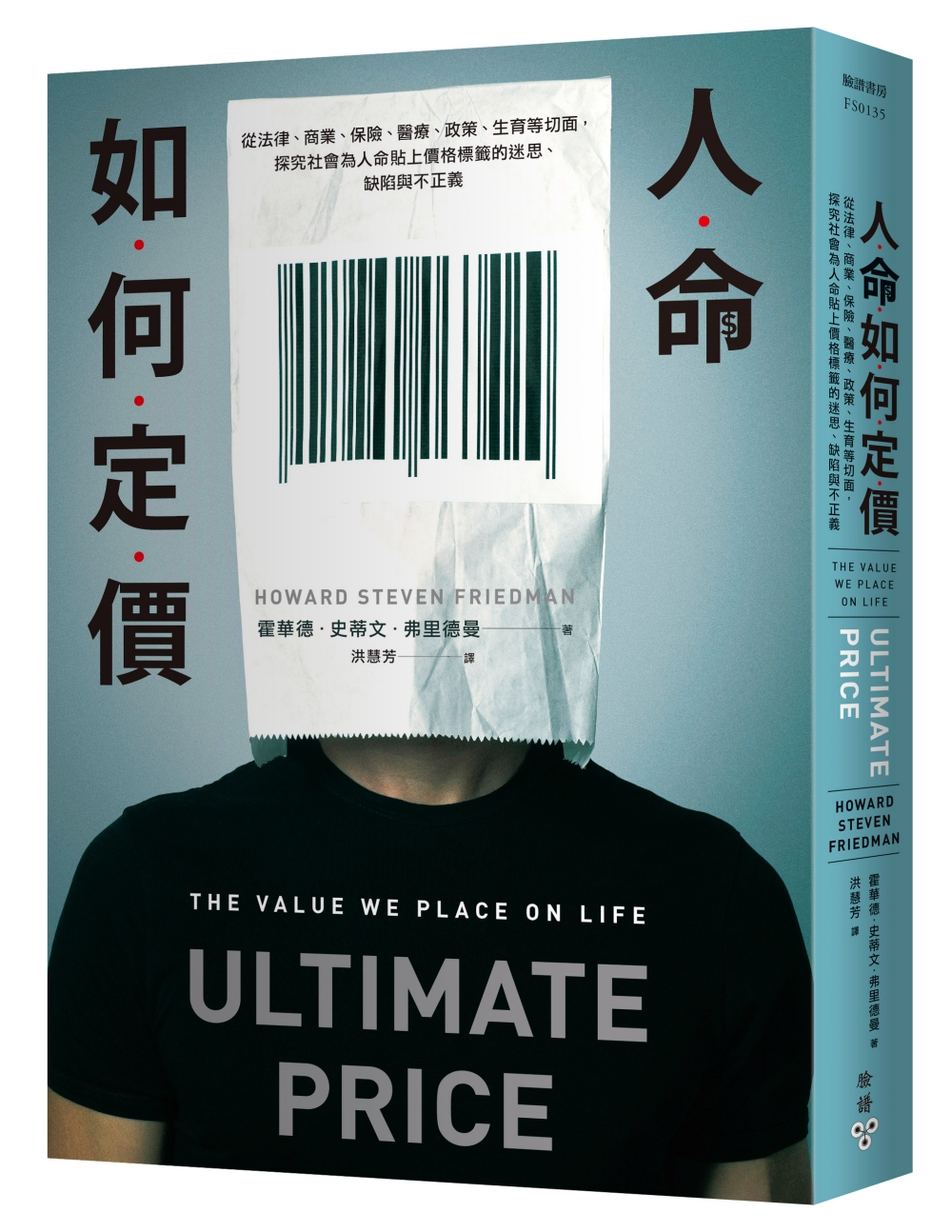
作者簡介
霍華德.史蒂文.弗里德曼Howard Steven Friedman
霍華德.史蒂文.弗里德曼是頂尖的統計學家與衛生經濟學家,是資料科學及成本效益分析應用的專家,目前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弗里德曼因在聯合國許多重要項目中擔任首席統計模型專家以及在統計、數據科學和衛生經濟學領域的廣泛出版物而廣為人知,前一本著作《國家的測量》(The Measure of a Nation)探討美國與世界各國的競爭力比較,也被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譽為是二〇一二年年度最佳作品。
譯者簡介
洪慧芳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畢業,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管理碩士,曾任職於西門子電訊及花旗銀行,現為專職譯者,從事書籍、雜誌、電腦與遊戲軟體的翻譯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