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謝宜容起碼幹掉賴清德半壁江山 2024-11-22 00:02
- 最新消息 投書:立院惡鬥 只會讓更多科技人企業人不敢投身政壇 2024-11-22 00:00
- 最新消息 勞動部稱謝宜容失聯明天不出面 吳母淚控:霸凌太過分、太惡毒 2024-11-21 22:05
- 最新消息 俄烏戰況恐升級 烏克蘭是否有能力攔截ICBM 2024-11-21 21:50
- 最新消息 明後兩天各地氣溫回升 北部、東北部18到23度濕涼舒爽 2024-11-21 21:45
- 最新消息 劍橋詞典2024年度代表字出爐 「manifest」反映人們追求身心健康趨勢 2024-11-21 21:43
- 最新消息 為了9萬元勒斃馬國女大生 陳柏諺一審判賠父母逾638萬元 2024-11-21 21:32
- 最新消息 觸犯戰爭罪、違反人道法 ICC對納坦雅胡、哈瑪斯領導層發出逮捕令 2024-11-21 20:47
- 最新消息 【世棒四強賽】「CT AMAZE」自費飛東京應援 推掉台灣活動損失近10萬 2024-11-21 20:45
- 最新消息 蔡英文抵達加拿大 感謝台灣鄉親熱情接機 2024-11-21 20:37

與其在《梅豔芳》裡徒勞地回憶那個永不再的舊香港,還不如在《智齒》裡直面那個修羅場一般的新香港。(圖片取自《智齒》劇照)
「與其在《梅豔芳》裡徒勞地回憶那個永不再的舊香港,還不如在《智齒》裡直面那個修羅場一般的新香港。」這是我聽說電影《智齒》在香港的票房慘淡,下意識給他們想的告急宣言。
但當然,人總是願意懷緬,而不是直面的。
鄭保瑞的《智齒》以極端的暗黑、絕望,告訴那些香港在電影業以外的「演員」們:你們粉飾太平的新香港,不過是垃圾與殘肢充塞的修羅場。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躲藏在車水馬龍街道背面、下層的垃圾場,像幻象上撕開的缺口,更像那些女子斷腕處露出的猙獰血骨。
原著故事本來不是發生在香港的。電影移植了一個黑死金屬搖滾一般的香港給它,老刑警展哥(林家棟飾)和新紮警官任凱(李淳飾)被一樁連環殺人毀屍案難住,遭遇曾經意外傷害展哥家人的女流氓王桃(劉雅瑟飾),展哥對她展開報復之餘還想利用她去破這樁迷案,但兇手比想像中聰明強悍,隨著任凱失槍、王桃被擄,展哥陷入寸步難行的困頓⋯⋯而包圍著他們的,或者說像他們一樣被包圍的,皆是香港。
整部電影最讓人難忘的當然是凌厲的黑白影像和末日廢墟一般的置景,這引起影評兩極的反應,一是覺得形式是掩飾內容的空洞和陳套,一是覺得形式本身就是內容的寄寓,我比較傾向後者。再說,三個主角的賣命演出,也許可以讓觀眾拋開劇情的薄弱和硬傷,多一些共情。
「你可曾想象被當垃圾的感受?」王桃這句台詞是最令我難忘的,這部片就讓觀眾代入這種被侮辱和被傷害的感受,同時也感受著香港被「糟質」(蹂躪)得奄奄一息的當下,我們一再地隨著攝影機和王桃被摜摔在污水和瓦礫裡,一面掙扎抬起頭呼吸。
不要忘記王桃的另一句震撼的話是:「我要活!」千言萬語,她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命運中的梅豔芳?「錯就要認,打就企定」,在贖罪意識上,女孩比片裡片外所有人都有擔當得多。
但同時,為了活,她也必須殺掉某人,那是她的心理智齒——我不認為這是意外,她的開槍實際上是她的潛意識行為,否則智齒會折磨她一生。與此相比,那個被肉身上的智齒折磨的精英警官任凱,他一邊牙痛一邊尋槍的片段才是最顯得荒誕陌生感的,但這是很多自以為在大時代的傾軋中自己是被無辜牽連的人的縮影。
與鋪天蓋地的垃圾、殘骸相對應,是靈感來自華富邨的滿山神佛像——其實不止華富邨有,香港人「敬畏神明」,不敢貿然扔棄破舊的佛像,都會找一個荒坡成群安置之,華富邨的規模最大,我還在裡面見到過魯迅像。喪失信仰的寄託後,千佛還原為被遺棄的垃圾;對於無法拯救的香港,虔誠的良心漸漸也變成智齒:無用但持續作痛。
最終,這部電影問了我們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智齒真能拔掉嗎?limbo(電影的英文名,意為靈薄獄)真能超越嗎?電影不如真的叫《垃圾》或者《修羅》好了,靈薄獄幽靜平和但置身其中的靈魂永遠不能解脫,修羅場血肉紛飛卻有可能終結嗎?在鄭保瑞一貫的悲觀中,竭力求生的少女王桃似乎提供了零點零一的希望。
如果這顆智齒拔不掉,那就讓它持續作痛吧,讓所有人都感覺到這種痛,總比吃了麻醉劑傻笑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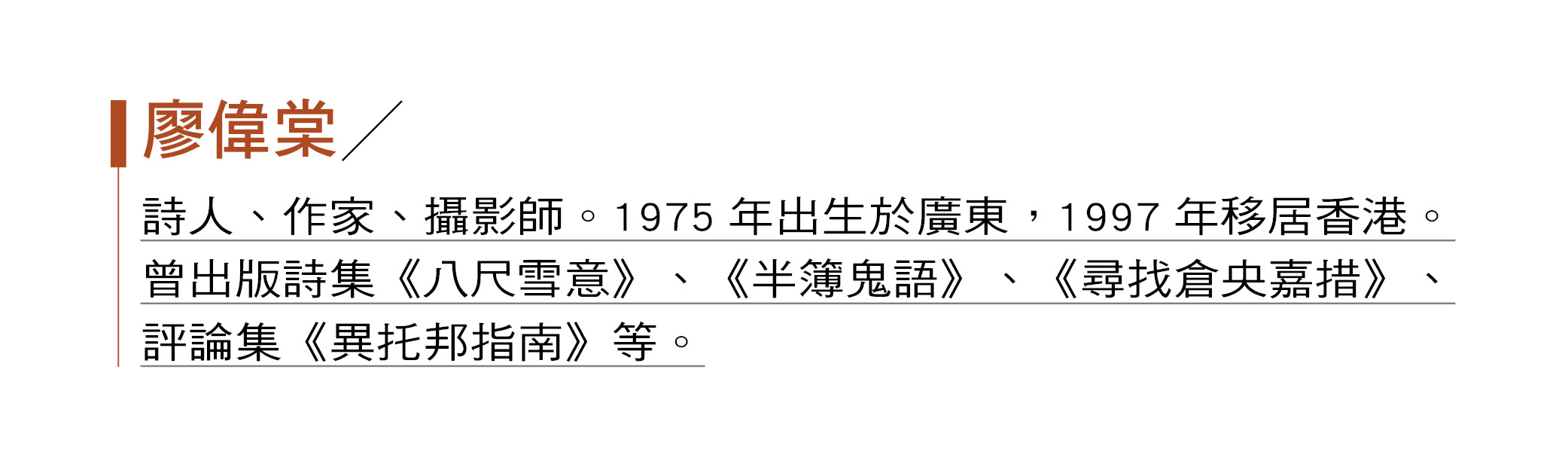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起底謝宜容!傳身家背景雄厚「善做公關」 先生和綠營高層有交情
- 一元特典!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釋出「零星票券」,11/24 採實名制一般販售
- 【世界棒球12強賽】滿足「2條件」台灣確定晉級4強 今晚是關鍵
- 先搶先贏!Ado 五月林口體育館演唱會採實名制入場,11/19 輸入「指定代碼」可優先預購
- 【內幕】T112步槍裝彈器採購案疑專利侵權 以色列向軍備局寄存證信函
- 王一博金雞獎典禮被抓包視線離不開趙麗穎 網揭兩人4年戀情無法曝光背後真相
- 勞動部涉職場霸凌不只謝宜容? 何佩珊:與輕生者中間還有2個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