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謝宜容起碼幹掉賴清德半壁江山 2024-11-22 00:02
- 最新消息 投書:立院惡鬥 只會讓更多科技人企業人不敢投身政壇 2024-11-22 00:00
- 最新消息 勞動部稱謝宜容失聯明天不出面 吳母淚控:霸凌太過分、太惡毒 2024-11-21 22:05
- 最新消息 俄烏戰況恐升級 烏克蘭是否有能力攔截ICBM 2024-11-21 21:50
- 最新消息 明後兩天各地氣溫回升 北部、東北部18到23度濕涼舒爽 2024-11-21 21:45
- 最新消息 劍橋詞典2024年度代表字出爐 「manifest」反映人們追求身心健康趨勢 2024-11-21 21:43
- 最新消息 為了9萬元勒斃馬國女大生 陳柏諺一審判賠父母逾638萬元 2024-11-21 21:32
- 最新消息 觸犯戰爭罪、違反人道法 ICC對納坦雅胡、哈瑪斯領導層發出逮捕令 2024-11-21 20:47
- 最新消息 【世棒四強賽】「CT AMAZE」自費飛東京應援 推掉台灣活動損失近10萬 2024-11-21 20:45
- 最新消息 蔡英文抵達加拿大 感謝台灣鄉親熱情接機 2024-11-21 20:37

擁有龐大人口的中國經八九重創,試圖走出一條經濟起飛、大國崛起的道路,為此不惜一切代價,變成了一個霧霾重重包圍的國度,一波一波的反抗、維權、呼喊都被無情地撲滅了,許許多多的人付出了沉痛的代價,並且繼續在支付著代價,日復一日。(湯森路透)
1987年1月,因一場波及全國許多城市的學潮導致胡耀邦下臺,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三人被開除黨籍,在此之前,我唯讀過劉賓雁的《人妖之間》、《第二種忠誠》等報告文學,對於方勵之、王若望頗為陌生,但因為報紙上對他們的批判,引用他們的言論,反而讓我瞭解了他們,對他們心存好感,也由此開始了我對現實制度、民族命運的嚴肅思考,那年我20歲。
我最初的政治啟蒙即是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喧囂中完成的,我感謝那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言論,甚至喜歡「自由化」這個說法,不管給它帶上什麼帽子,這個詞都讓我感到親切。雖然離開「文革」已經十多年了,整個大陸的政治生活、話語體系其實還是充滿禁錮、僵化、教條,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氣。《開放》雜誌的前身《解放月報》就是那個時候在香港問世的,其時香港尚在英國殖民地時代,我當然無緣見到這本雜誌。
延伸閱讀:香港新移民的困難源自歸化政策的缺憾
兩年後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八九民運,我從官方媒體批判劉曉波的文字中獲知,他的許多重要言論就是首先在這本雜誌上發表的,特別是他那驚世駭俗的「三百年殖民地」說。此後,陸陸續續聽聞、甚至見過這本雜誌。我從來沒有想過將來還會與《開放》結緣,自2001年起,我為它撰稿前後跨了14個年頭,直到2014年12月出完最後一期紙版。1987年距今正好30年,東漢的智者王充在傳世之作《論衡》中有一句話:「且孔子所謂一世,三十年也。」30年幾乎是一個世代,我也從20歲到了50年。30年來,世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中的預言幾乎都應驗了,雖然要實現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嚮往的「烏托邦」還任重而道遠。
柏林牆的轟然倒塌,蘇聯、東歐的紅旗落地,鐮刀斧頭的圖騰被拋棄,20世紀最重大的社會主義實踐在世紀末宣告失敗,即使中國以血腥方式暫時阻止了歷史的進程,卻也早已不再是當年的那種社會主義,深入到社會肌體每個毛細血管的腐敗,特權階層掌握並消費超過人類想像力的資源,都讓社會主義的標籤變得難堪。臺灣自1987年以來開放黨禁、報禁,已經完成數次政黨輪替,充滿恐懼不安、人權沒有保障的那一頁已翻過去了。香港在1997年「回歸」之後也經歷了重大變化,這個昔日的世界自由港在「雨傘革命」的創傷中前途未卜,擁有龐大人口的大陸經八九重創,試圖走出一條經濟起飛、大國崛起的道路,為此不惜一切代價,變成了一個霧霾重重包圍的國度,一波一波的反抗、維權、呼喊都被無情地撲滅了,許許多多的人付出了沉痛的代價,並且繼續在支付著代價,日復一日。
洋洋大觀的30年史
作為一本小小的期刊,能夠親歷這樣一個大時代,一個處在急劇變化之中、不可預測的轉型時代,真是有幸。這也得益於它在香港的獨特地位,可以關注世界上發生的重大變化,尤其是兩岸三地的變化,當然焦點還是在這塊古老而充滿了苦難的大陸。30年來,這裡的權力依然高度神秘、壟斷,不容批評,即使互聯網的普及也絲毫改變不了這一點。放在整個中國史上、乃至世界史上來看,這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時代?《開放》的30年從紙刊最終轉為網刊,見證了這個時代的歡笑和血淚、憤怒與荒誕,30年間發表的上萬篇文章,幾乎觸及了這個時代的方方面面,合在一起就是一部洋洋大觀的30年史。
站在1987年的起點上,當時正年富力強的創辦人也許都沒有想像過30年後的中國,時間無情,許多曾經在《開放》發表過文字的作者或《開放》採訪過的物件已然離世,30年前正在風口浪尖上的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不在了,在香港有廣泛影響的司徒華不在了,林昭在1957年的同行者張元勳、沈澤宜不在了,劉曉波還在錦州的監獄中。寫到這裡,我想起趙紫陽先生,12年前的今天,他在北京黯然離世,當時的《開放》曾有沉甸甸的悼念專輯。在歷史深處,1989年5月19日,他在天安門廣場上留下的那一句—「你們還年輕啊,來日方長!」仿佛還在耳畔,而當年聽到過這句話的一代人也多已達知天命之年。來日方長,到底要叫一個民族等待到何時?在鞭子、蠍子鞭下負著重軛還要多久?也許沒有人回答得了這一問號。
30年來,《開放》所做的只是與這個鞭下的民族同行,同哭,同樂,辦刊物也是在參與書寫歷史。我想起在國共內戰之際影響廣泛的《觀察》週刊,從1946年9月到1948年12月只有短短不足兩年半,更早的《新青年》的黃金時代也不過三四年,胡適他們自辦的《新月》、《獨立評論》存在的時間也都不長,像《東方雜誌》這樣從晚清到民國,在動盪不安的亂世中持續出版近半個世紀的刊物,真不多見。1949年在臺灣誕生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有將近11年的生命,只是在特殊情況下的存在,最終還是為蔣介石所不容。毫無疑問,《開放》可以與這些刊物一起進入百年中國言論史的序列中,以微薄的人力物力在漫長的時間中月複一月,關注兩岸三地乃至世界各國的風雲變幻、世道人心,如果不是有極大的堅韌,對言論事業有著信心和抱負,也是很難堅持下來的。
中國的1984
在告別紙版之後,金鐘先生有個心願要編選一冊30年的選本,以紀念這段不平凡的歲月。他在上萬篇文章選出了一百篇,雖遠遠無法涵蓋30年來對歷史與現實、中國與世界及時、尖銳、豐富的洞察,卻也足以彰顯言論報國的情懷,我從選目中看到許多熟悉的篇目、許多曾打動過我的文字,比如董樂山先生的遺稿《中國的1984》,這是1999年董先生故世後發表的,相隔18年,再讀此文,依然有深深的共鳴,我們還生活在「1984」。董先生也是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翻譯過《第三帝國的興亡》,也翻譯過《1984》。
還有巫甯坤先生的《我歸來:目睹燕京末日》,巫先生的回憶錄《一滴淚》記錄了一個荒謬的時代,在平靜的敘述中超越了那個時代加給他的巨大傷害,感動過無數西方讀者。他的女兒巫一毛也有一本回憶《暴風雨中一羽毛—動亂中失去的童年》,選本中有她的一篇《我們這些小右派》,那是父女兩代人親歷的時代。當他們寫下這些文字時,那一頁似乎翻過去了,但又沒有翻過去。巫一毛曾引述哈金《狂人》中的一段話:
“我看見中國的形象是一頭老母豬,既老朽又瘋狂,竟然會吞下自己的孩子來維持自己的生命。她貪得無厭,過去就吃掉許多幼嫩的生命,現在又狼吞虎嚥新的肉和血,而且肯定還會吞下更多的。”
《開放》30年來的文字就是目擊一個時代帶給國人的傷害,同時也看到許多知識份子在歷盡劫難之後的覺醒,經濟學家千家駒先生曾經顯赫一時,被這個體制所高抬,八九之後,他看清了一切,2002年11月,千家駒去世後,《開放》以《千家駒看破紅塵痛心疾首》為題,對《千家駒自撰年譜》做了獨家報導, 千家駒自述之所以看破紅塵,「一句話,看破紅塵,紅者共產主義也。」
在早年的紅色潮流追隨者中,又豈只千家駒看穿了,司馬璐、戈揚、張顯揚、李志綏、郭道暉…也包括趙紫陽晚年都有反省,選本中有他們的聲音。在1949年以後出生,成長起來的知識人中,蘇曉康、茉莉、劉曉波等人也都看清了這個時代的本相,還有更年輕的八九一代、以及後八九一代,成為《開放》的作者,與時代一同歌哭。一本雜誌,集中海內外幾代華人中敢於直言的思想者、寫作者,將他們的回憶、反省、思索傳遞出去,完成了一個莊嚴的歷史使命,就是在中國大陸尚無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之時,依然用中文來表達自由的聲音,年深月久,當紙版都停印之後,在合訂本中再見這些文章,將會有怎樣的一種驚喜。《開放》打開的是一扇自由的門,從過去通往未來,它創造的歷史不僅在文字之間,也在文字之外。前幾天,金鐘先生在太平洋彼岸來電,希望我為將要出版的三十年選本寫一小序,我在寒夜孤燈之下,想起《開放》的許多舊事,寫下這些話,不僅為《開放》,也為這個正淪陷在鋪天蓋地的霧霾中的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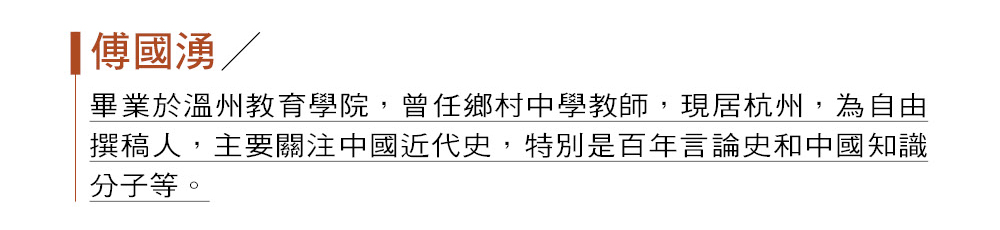
【上報徵稿】
上報歡迎各界投書,來稿請寄至editor@upmedia.mg,並請附上真實姓名、聯絡方式與職業身分簡介。
一起加入Line好友(ID:@upmedia),或點網址https://line.me/ti/p/%40zsq4746x。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起底謝宜容!傳身家背景雄厚「善做公關」 先生和綠營高層有交情
- 一元特典!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釋出「零星票券」,11/24 採實名制一般販售
- 【世界棒球12強賽】滿足「2條件」台灣確定晉級4強 今晚是關鍵
- 先搶先贏!Ado 五月林口體育館演唱會採實名制入場,11/19 輸入「指定代碼」可優先預購
- 【內幕】T112步槍裝彈器採購案疑專利侵權 以色列向軍備局寄存證信函
- 王一博金雞獎典禮被抓包視線離不開趙麗穎 網揭兩人4年戀情無法曝光背後真相
- 勞動部涉職場霸凌不只謝宜容? 何佩珊:與輕生者中間還有2個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