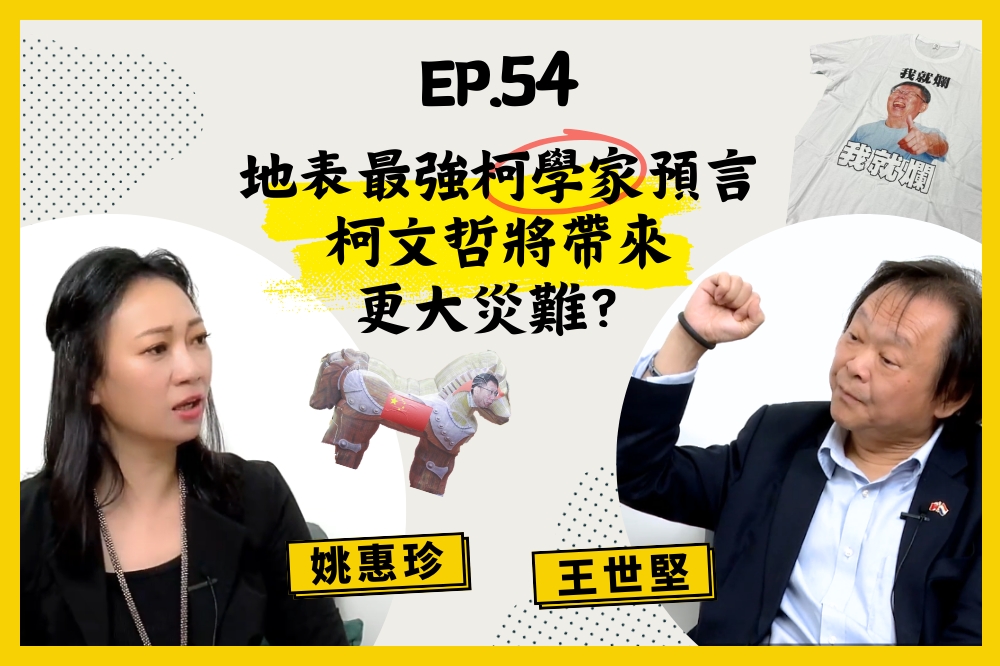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不斷更新/【世棒四強賽】開轟啦!「中華隊 vs 美國」潘傑楷陽春砲 中華隊5局上3:1領先 2024-11-22 12:47
- 最新消息 賴清德總統任內首次出訪選擇南太 黨政人士曝戰略考量 2024-11-22 12:40
- 最新消息 《大夢歸離》侯明昊錄真人秀在非洲草原拉屎 全程被外國遊客拍下秒登熱搜糗爆 2024-11-22 12:34
- 最新消息 【有片】露面了!謝宜容鞠躬道歉 落淚稱對不起家屬:孩子成冷冰冰遺體 2024-11-22 12:20
- 最新消息 美特使還在以色列進行調停 以軍持續對黎巴嫩空襲釀47死 2024-11-22 12:03
- 最新消息 徐千晴重提高虹安「北一女案」 批大官對「良善」解讀與大眾脫節 2024-11-22 11:59
- 最新消息 《永夜星河》丁禹兮霸氣砸48萬買虞書欣封面雜誌 他這舉動暗藏「超甜細節」全網嗑翻 2024-11-22 11:44
- 最新消息 【擴大健保財源】健保署改革補充保費 擬增售屋、賣股票項目 2024-11-22 11:40
- 最新消息 對俄天然氣工業銀行祭出制裁 美財長葉倫:使俄軍更難取得資金 2024-11-22 11:23
- 最新消息 西方國家官員表示 北韓高階將領首度在俄國庫斯克地區遭攻擊受傷 2024-11-22 11:00

俄烏戰爭的爆發不可避免地將烏克蘭直接且徹底地歸入至由波蘭所主導的「反俄命運共同體」與「統一反俄陣線」當中。圖為波蘭的反戰示威人士。(美聯社)
爆發於今年2月24日的俄烏戰爭作為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The Crisis in Crimea and Eastern Ukraine)的「延續」,已在原蘇東(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及蘇聯地區(Post-Soviet States)掀起了新一波不同程度的「反俄浪潮」,其內涵伴隨戰事的進一步發展呈現出不同的思想形態和邏輯特徵。
其中,波蘭作為維謝格拉德集團(Visegrad Group)中唯一一個長期連續遭受沙俄及蘇俄分割且佔領的國家,屬中東歐地區反俄情緒最高的北約及歐盟成員國,可謂歐陸「抗俄急先鋒」。早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前,波蘭就以美國「新興盟友」的身份在「原蘇東地區」長期發揮著「自由燈塔」的作用,一方面憑藉北約軍事力量嚇阻「敵對勢力」就範,另一方面则憑自身「軟實力」持續指引東歐各國「回歸歐洲」。
而原屬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波羅的海(Baltic States)三國(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雖在獨立後,成功加入北約及歐盟,但始終對俄羅斯保持著高度的警惕,從不鬆懈麻痹。面對咄咄逼人的俄羅斯,波羅的海三國國防部就曾率先共同發表聲明堅定支持烏克蘭的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並且在美國的批准下將其所屬美制武器運輸至烏克蘭,協助其「抵禦入侵」。其中,最為積極的立陶宛(Lithuania)還曾被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Lloyd Austin)稱之為該地區「民主燈塔」。

歐陸「俄國威脅論」與「反俄大本營」的由來
不同於中亞(Central Asia)、高加索(Caucasus)及東歐烏克蘭,波羅的海三國與波蘭之間的「反俄戰略」可謂一脈相承。與此同時,波蘭與捷克(Czech Republic)、斯洛伐克(Slovakia)及匈牙利(Hungary)之間的「反俄歷史」則更加緊密相連。不僅如此,波蘭還是此次俄烏戰爭爆發以來自始至終都堅定援助並力挺烏克蘭的北約及歐盟「前線國」。由此可見,波蘭是整個歐陸東端「反俄大本營」的中心及樞紐,在捍衛歐洲正統拉丁文明(Latin Civilisation)的歷史長河中一直無畏地發揮著「主力軍」的作用。
自近代俄國崛起以來,波蘭首先被沙俄率先瓜分三次(Partition of Poland),後又被蘇俄連續瓜分兩次,迫使其由原先歐陸一雄長期淪為「亡國奴」與「衛星國」(Satellite State),導致波蘭民族在近兩個世紀的時間內與其所屬「母體文明」處在極為被動的半隔離狀態中。回顧歷史,不難發現俄國雖不是唯一一個危害且剝奪波蘭獨立、主權及領土完整的國家,但卻是最終決定波蘭「命運」的關鍵大國。受此影響,抵禦俄國侵犯或削弱其「元氣」不僅是波蘭國家安全的核心,而且還是自身生存與發展的重要保障。
歐陸「反俄命運共同體」與「統一反俄陣線」的延伸
波羅的海三國與波蘭實質上是區域名副其實的「安全命運共同體」,但將其一分為二的卻是俄屬「白俄羅斯」(Belarus)。毋庸置疑,組建於十六世紀中葉的波蘭—立陶宛聯邦(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是當時繼蒙古—突厥之後,第二個直接且全面影響俄國內政的區域大國,同時也是第一個自西向東對俄國歐陸核心地帶構成威脅的西方國家。對此,出生德意志(Germany)貴族家庭的沙俄葉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在其兩輪瓜分波蘭的過程中,一方面憑藉其德意志人口占多數的東普魯士(East Prussia)作為地緣屏障,另一方面則通過人為地在原波蘭—立陶宛聯邦領土上採用構建「白俄羅斯」的方式,徹底將波蘭與立陶宛一分為二,使其成為互不相同的兩個獨立區塊,進而將其逐一吞併,重新書寫歷史。
因此,對自蘇東劇變(Fall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及蘇聯解體(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後完成轉型且重獲獨立的波蘭及波羅的海三國而言,實現其國家「絕對安全」的核心前提就是持續推動當今白俄羅斯的「去俄羅斯化」及「西歐現代化」進程,即波蘭式「西斯拉夫化」。在此過程當中,各方須全力阻止「大俄羅斯主義」(Great Russianism)死灰復燃或東山再起,而烏克蘭則是俄國實現其「大國再崛起」的關鍵之所在,因此自然而然地成為各方爭奪的關鍵對象。
相比之下,對同樣身為維謝格拉德集團成員國的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而言,波蘭是防範俄國長驅直入及全面滲透的唯一一道「堡壘防線」,所以波蘭「淪陷」等同於區域「大亂」。但不同于波蘭的是,上述三國的「反俄歷史」僅限於蘇俄,而非沙俄。故此,其對東歐地區地緣政治格局演變的關注度遠低於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而所屬「反俄戰略」也只基本限於國家制度與思想領域上的「反滲透」,而非「全面對抗」。
烏克蘭「脫俄入歐」的實施與「獨立自主」的鞏固
由於烏克蘭和俄羅斯同屬東斯拉夫民族(East Slavs),因此所持「俄國威脅論」明顯不同於屬西斯拉夫(West Slavs)的波蘭,其核心分別由蘇聯解體後逐漸相繼成型的「回歸觀」與「仇俄觀」所構成,可謂「異源同流」。
自獨立三十年來,導致俄烏兩國漸行漸遠的根本性原因是長期不間斷的經濟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而非單一的制度選項或軍事技術的「輸入」與「輸出」。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由蘇聯首任總統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所被迫開啟的「體制性改革」(Perestroika),因在其先經濟後政治的變革過程中觸碰到俄白烏三國百年不變之利益根基,進而導致維繫「東斯拉夫命運共同體」的基輔(Kyiv)地方精英與莫斯科(Moscow)中央精英間產生難以化解的矛盾,最終不可避免地迫使其分道揚鑣。
經濟全球化在衝擊俄國經濟實力的同時,不僅有效將其「空虛化」,而且還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加深了俄烏兩國之間的「經濟隔閡」。「外強中乾」的俄國僅憑其單一的能源優勢已無力再與烏克蘭政治精英保持全方位的「經濟掛鈎」。受此影響,烏克蘭政治精英也只能在新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逐漸尋求新的境外政治及經濟資源,以便強化並鞏固自身實力,「回歸歐洲」由此問世。
起初,烏克蘭經濟領域的「向西靠近」之勢基本只限於其共和國西部原屬波蘭的加利西亞(Halychyna)和沃裏尼亞(Volhynia)地區,但後期伴隨烏克蘭地方新精英階級的形成,以及其與地方基層民眾之間的對接逐漸開啟了共和國政治權力平衡演變的新序幕。直至2013年烏克蘭「廣場運動」(Euromaidan)爆發為止,烏西地區是在吸收歐盟經濟資源的同時,輸入由布魯塞爾(Brussels)為中心的「新經濟秩序」,進而壯大自身的內部政治勢力。相反,烏東地區則是持續保持與莫斯科之間「跨國國防軍工體系」的正常運作,並且進一步延續以莫斯科為中心的「舊政治秩序」。其中,前者為新興親歐的地方精英,而後者則是親俄的前朝遺老,即中央精英。

反觀烏克蘭「廣場運動」不難看出,以時任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為首的烏克蘭親俄中央精英,在面對本國親歐地方精英挑戰時,嚴重缺乏烏克蘭族基層民眾的支持。由此可見,通用俄語的親俄中央精英自獨立以來未能實現自上而下的「自我轉型」,始終與通用烏克蘭語的共和國主體民族間保持著原蘇聯時期的「脫鉤狀態」。而俄國在烏克蘭的「經濟遺產」也伴隨時間的推移幾乎消耗殆盡,其直接經濟影響力相比歐盟可謂微乎其微,因此自下而上的「改朝換代」勢在必得。
烏克蘭「俄烏記憶」的破碎與「俄國威脅論」的強化
自2014年烏克蘭親歐勢力通過「廣場運動」徹底壓倒親俄勢力之「中央核心」之後,隨即引發歐陸冷戰(Cold War)結束以來,規模最大的地緣政治危機,致使區域長期以來的「美俄」與「俄歐」博弈由「暗鬥」轉向「明爭」,導致烏克蘭不可避免地成為北約與歐盟東擴及俄國西阻的「前線陣地」,進而引發曠日持久且愈演愈烈的「民族危機」,其影響延續至今並日益「升級」。
克里姆林宮(Kremlin)為持續維繫以歐亞大陸「心臟地帶」(Heartland)為軸心的「帝國秩序」,不惜動用武力「忍痛割愛」,通過製造克里米亞危機的方式終結「俄烏百年友誼」,迫使其共同記憶「支離破碎」。克里米亞半島(Crimea)的吞併與頓巴斯(Donbas)地區的叛亂直接激發烏克蘭主體民族的「抗俄」意識,而所謂「抗俄」實則為「反俄」。
在長達八年之久的「危機鬥爭」中,檢測境內俄裔「可信度」與「忠誠度」,以及反思民族歷史相繼成為烏克蘭「反俄民族主義者」與「抗俄愛國主義者」的「使命」與「任務」。之前被蘇俄政府定性為「人民公敵」(Enemy of the People)的爭論人物開始一一被民眾「私自平反」,象徵反蘇的烏克蘭反抗軍(Ukrainian Insurgent Army)也隨之「復活」,與俄國軍事入侵與干涉一道呈現出舊仇未消新恨劇增的「惡性」循環趨勢,導致俄烏關係全面持續惡化。
俄烏戰爭的爆發不可避免地將烏克蘭直接且徹底地歸入至由波蘭所主導的「反俄命運共同體」與「統一反俄陣線」當中。直至今日,已有四百萬公民受戰爭影響逃離烏克蘭,其中超過一半以上的人逃至波蘭,使波蘭成為名副其實的東歐「自由燈塔」及「大後方」,賦予每一位烏克蘭公民自由的希望與未來。而經過此輪戰爭血洗的烏克蘭民族已經清楚地重新認識到所謂「同宗同源」和「血濃於水」純屬烏托邦,唯獨「為自由抗爭到底」才是擺脫奴役與壓迫的唯一出路,而「重獲獨立」才是世間與人生之真理。
※作者為哈薩克國立大學經濟科學碩士、曾任哈薩克國立大學經濟與商業高等學院教師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起底謝宜容!傳身家背景雄厚「善做公關」 先生和綠營高層有交情
- 一元特典!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釋出「零星票券」,11/24 採實名制一般販售
- 【世界棒球12強賽】滿足「2條件」台灣確定晉級4強 今晚是關鍵
- 先搶先贏!Ado 五月林口體育館演唱會採實名制入場,11/19 輸入「指定代碼」可優先預購
- 【內幕】T112步槍裝彈器採購案疑專利侵權 以色列向軍備局寄存證信函
- 王一博金雞獎典禮被抓包視線離不開趙麗穎 網揭兩人4年戀情無法曝光背後真相
- 楊冪人氣暴跌與《慶餘年》張若昀演新片淪鑲邊女主 造型曝光全網夢回《三生三世十里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