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國發會員工千字文控訴處長霸凌 謾罵羞辱還威脅「我會殺了你」 2024-11-22 21:18
- 最新消息 「女兒餓到吸手指」加薩瀕臨飢荒 遇難人道援助者卻創歷史新高 2024-11-22 21:18
- 最新消息 【世棒四強賽】被觸身球打傷腳 陳傑憲喊:明天可以當然一定想上場 2024-11-22 20:59
- 最新消息 旅外健保12/23起不可停保 出國逾6個月仍要繳費 2024-11-22 20:24
- 最新消息 吳慷仁確定出席金馬獎 頒發女主角獎項但不走紅毯 2024-11-22 20:15
- 最新消息 拆除和平新生天橋遭批「野蠻」 文化局:流程合法合理 2024-11-22 20:15
- 最新消息 「不能永遠要求吹哨者當烈士」 民眾黨團拚《揭弊者保護法》本會期通過 2024-11-22 20:05
- 最新消息 全球最強護照排名出爐 台灣免簽減4剩141國、排名不降反升至34名 2024-11-22 19:27
- 最新消息 江振誠攜手SSAW 進擊高雄極致餐飲市場 2024-11-22 19:00
- 最新消息 勞動部即日起停職謝宜容 移送監察院、新北地檢署偵辦 2024-11-22 19:00

即便傷心依舊,小燈泡雙親不改初衷,直指社會應該面對的問題根源。然而,判決的內容,與媒體框定以供社會理解與討論精神障礙與犯罪間關係的方式,卻一定程度上,踐踏了被害者家屬的痛;亦阻絕了找到有可能真正貼近、撫慰、修復被害者或被害者家屬的可能。(中央社)
日前,龔重安與王景玉兩宗隨機殺人案的判決分別出爐,免殺,但無期徒刑。媒體不意外地再一次針對「精神疾患殺人免死」的標籤反覆強化;而因社群媒體的直播功能快速便利,隸屬公廣集團的華視甚至針對後者辦起直播投票,詢問閱聽眾是否願意「浪費公帑」養「殺人魔」;或找來同受失親之苦的湯姆熊殺人案受害者家屬方姑姑、王昊虐死案受害者家屬王薇君「痛批」司法已死。
媒體的做法引人厭惡。因其放棄可透過凝視、爬梳所能抵達的思考與教育功能,而淺薄、二元的再現視角,則進一步毀壞此前各界試圖拉出的對話軸線。然媒體的凝視視角其實是一面鏡—在市場機制的影響下,其對新聞議題的設定框架,一定程度反映了社會的偏好與價值。而若閱讀地方法院新聞稿,更可窺見,執法者過於扁平看待「罪/罰」且媚於社會價值的判決考量。
士林地院在新聞稿裡指出,合議庭法官對受害者與其家屬的遭遇「同感哀戚」,且對嫌犯的冷酷惡行同感震驚。案發後民意調查顯示「社會瀰漫將殺童者除之而後快之氛圍,本院置身相同社會體系,豈能不察?」然社會觀感是否為一扁平、單一的集合體?對殺人者之厭惡、恐懼,能不能被細緻劃分、理解?社會對被害者家屬的「同感哀戚」,是自身的投射或是真正切身的同理?
通往正義之路複雜而多元
去年筆者曾寫下《無癒之傷:北捷殺人案的對話邊界》與《寬宥的岔路:北捷案裏的道歉、平撫與司法歷程》兩篇報導。從報導裡被害者家屬的傾訴,社會可以得知,並非所有北捷被害者家屬都不能原諒、在第一時間就要鄭捷立刻去死;而就算鄭捷已死,被孤獨遺留在這世上的北捷案被害者家屬並未因此走向光明、不再恐懼;而之於社會大眾,是我們依舊遭遇了小燈泡案所帶來的社會衝擊。
上述問題與歷程,顯現了正義或分階段,或更多元、且必須關照每個涉事者的需要。這意味著當審判過於急切地回應「同感哀戚」,非但會折損不同受害者與其家屬對正義的期待,同時也提醒,用刑罰處理「同感哀戚」,將導致背後隱藏的,對「為什麼會有這些事發生」的恐懼難以被釐清,甚至降低恐懼再度發生的可能。這正是小燈泡雙親為何選擇成為非典型被害者家屬—他們不大聲疾呼「非殺不可」,他們寧可讓自己的受苦轉化為更有意義的歷程,對司法進行提問、對審判可能性抱持期待,以求小燈泡不虛此生。

先是理解 才有論罪
小燈泡雙親在案發後其中一項重要訴求,是「理解王景玉為何殺人」,先求理解,而不妄下判斷或判刑。而之於審判,理解犯罪動機與成因,更該是量刑的重要基礎。
但回溯目前發生在台灣的隨機殺人案,檢方第一時間因著對正義的想像僵固,其反應很難是「企圖理解」,而是「公式套用」。套用過程中,多為形容詞所堆砌的如「極端殺人判死」,或僅根據其行為與當下回應的內容作為起訴根據。但一個生命殘害另一生命難道是這麼簡單的事?其所自白的是否為真(如湯姆熊殺人案)?若那話語有假,不夠細緻的叩問,即是讓我們錯過承接與改善的可能,並使審判淪為僅是量刑的競技場。
小燈泡案一共進行兩次鑑定,第一次為榮總精神部劉英杰醫師的團隊進行,第二次由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系教授陳若璋的團隊主持。兩次鑑定,差異極大。劉英杰出庭時指出,王景玉因預知自己被抓後兇刀會被扣案,因此特別買了一把新刀,此外他也擔心被抓後機車會在外頭颳風淋雨,所以預先把機車騎回家,這兩個動作顯示他知道殺女童的行為為現行法律所不容,因而判斷王景玉犯案時有責任能力。
但這判斷,引發王景玉的辯護律師質疑,其中一點是,律師認為,醫生只能認定精神障礙,法官才能判斷犯案時有無責任能力,但北榮精神鑑定報告卻直接寫王有足夠能力,結論已經「跨界」;不僅如此,被害者家屬也認為法院在這精神鑑定過程中,缺乏對王景玉的深入了解。這樣的鑑定內容,並非出自精神鑑定專家的武斷,而是「因為檢方囑託醫院的鑑定標的就是犯案時有無行為辨識能力,所以院方就依此導出結論。」
一直要到陳若璋對王景玉家屬、本人與少數友人進行多次心理測驗與訪調,小燈泡的雙親才終於得知,王景玉因家庭因素,人際互動少且個性自卑,在家庭壓力下開始行為偏差,未能完成高中學業;當兵後工作一陣子,王景玉失業,開始有不對勁的行為出現,但無人察覺他的精神情況已亮警示。事實上,在他犯罪前,王景玉其實兩度病發、被送急診,確診有思覺失調,但他並未被要求強制住院,而其雙親一再否認兒子的罹病事實。而也正因其缺乏支撐,使王景玉的再犯風險相當高。
應報的界線
審判走到尾聲,餘剩法官對責任認定的判斷與量刑的權衡。那麼,合議庭法官如何理解精神障礙與智障和犯罪行為的關聯?
合議庭認為,雖王景玉確認罹患思覺失調,但因懂得躲避他人監督,判斷王景玉不符刑法第十九條之「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顯著減低者,得減刑」的不罰或減刑規範。而若併同合議庭新聞稿所說的「同感哀戚」與「社會冀求除之後快」的說法,可以知道,合議庭其實十分想判王景玉死,但因受兩公約已國內法化的限制而被拘束。若單從鄉民觀感來看法院判決,合議庭法官並不恐龍。然而,兩公約難道是莫名排除精障者犯罪的死刑責任?
針對判決中法院如何理解精神疾患與責任判定的關聯,精神科醫師沈政男已撰文指出法院的矛盾,在此不贅。於此想進一步指出的是:兩公約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為何要排除精神疾患與智障者於死刑之外?前者的理由,與台北市聯松德院區精神科主治醫師楊添圍著作《以瘋狂之名:英美精神抗辯史》中,曾提及特魯里街皇家歌劇院槍殺案的思考相呼應:
此案的辯護律師厄斯金認為,精神異常者,很少完全精神錯亂到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家人,而且如果真有如此之人,這樣的人也很難犯下罪行──「不同於完全癡愚者,理性並沒有遭到驅離,但是滋擾卻進駐在理性之旁,竄動不休、凌駕其上,使理性無所適從,無法節制。」厄金斯指出,精神異常的準則,不應限定在思考能力或僅是察覺對錯,而應該是「妄想」的有無。也就是,一個人或許可以完美地表達道德與法律上的純正,但無法正確將這些標準運用在自己的行為上,「因為他對於事物的感受有着根本的錯誤」。
這是在說,精神疾患犯罪者,很可能在某部分行徑能與常人邏輯判斷無異,但其犯罪行為卻是受到妄想的驅動,意即脫離現實。在此情境下,其犯罪原因是「病」而非「惡」,更非「魔」。
目前精障能否判死,確實還有很大爭議,因判斷犯人在犯罪時究竟有沒有受到精神疾病影響有其難度,但無論如何,保護精障者與智障者免於死刑背後的精神是:他是壞人或病人?若是病人,報復病人的意義何在?精神障礙會發生在任何年齡、性別的人身上,其發生與否還牽涉家庭與社會因素──試想,若王景玉第一次病發即獲得醫療資源、社區的看護,小燈泡案,是否有可能不會發生?而若報復是重要的、必要的,報復的界線為何止於個人?
從移情到同理
辯論當日,小燈泡雙親發布聲明,明確表示:變態心理的形成以及因此的犯罪行為並非單獨環節的錯漏,對於變態心理與犯行的防治,亦需要多方的支援與努力。個人需要建立病識感、家庭也必須建立病識感,乃至於整個社會都需要建立集體的病識感,承認人會出錯、家庭會出錯、社會系統會出錯,每一個人、每一個社會環節,都必須建立預警與懂得實施適切的關懷與支持,如此,方能抑制此類極端犯罪行為的發生率。
即便傷心依舊,小燈泡雙親不改初衷,直指社會應該面對的問題根源。然而,判決的內容,與媒體框定以供社會理解與討論精神障礙與犯罪間關係的方式,卻一定程度上,踐踏了被害者家屬的痛;同時,亦影響、阻絕了法院與檢方,檢討自身面對精神障礙理解的不足,進而找到有可能真正貼近、撫慰、修復被害者或被害者家屬的可能。最後,是使社會對於廣泛性發展障礙的偏見和恐懼持續強化,最終回頭威脅整個社會的安全。
每當想起隨機殺人案的社會觀感與審判,總會想起《城市暴力的終結》一書的這麼一段話:
「暴力有一個根源:被否定、被排斥、承受著痛苦的主體變成了暴力施動者,尤其是當他們的苦難和不幸被掩蓋和被忽視之際,以及他們周圍的人和社會也沒有考慮過其存在的意義之時。」
我以為那正是小燈泡家屬始終未對量刑表示意見,也從不希望小燈泡的死,成為廢死與否的擂台的原因。這對善有信、認為愛有可能、對自己所不知的世界抱持謙卑的一雙慎重的人,為我們揭示「罪」與「罰」並不一定要是一對連體嬰。社會,能否穿越義憤的移情,真正走向同理,跳脫陳腐迴圈,使生命的隕落遠離悲傷?
【延伸閱讀】
張娟芬:死刑判決書連被告名字都寫錯
8成民意反廢死 短短4年18人命喪國家槍下
法院拿兩公約當「免死金牌」 馬英九批:兩公約從未廢除死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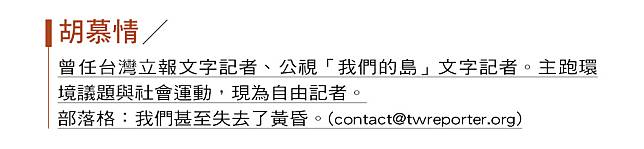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起底謝宜容!傳身家背景雄厚「善做公關」 先生和綠營高層有交情
- 一元特典!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釋出「零星票券」,11/24 採實名制一般販售
- 【世界棒球12強賽】滿足「2條件」台灣確定晉級4強 今晚是關鍵
- 先搶先贏!Ado 五月林口體育館演唱會採實名制入場,11/19 輸入「指定代碼」可優先預購
- 陳妍希與陳曉鬧婚變疑復合 她素顏與閨蜜聚餐模樣超清純全網夢回《那些年》
- 【內幕】T112步槍裝彈器採購案疑專利侵權 以色列向軍備局寄存證信函
- 楊冪人氣暴跌與《慶餘年》張若昀演新片淪鑲邊女主 造型曝光全網夢回《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