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賴清德就任總統後首度出訪 將訪南太平洋3友邦 2024-11-22 10:10
- 最新消息 衛星畫面顯示 北韓以軍火、作戰人員換取大量俄國原油 2024-11-22 10:03
- 最新消息 直播/賴清德就任後首度出訪 總統府10:00記者會 2024-11-22 10:02
- 最新消息 【世棒四強賽優惠】狂賀中華隊前進東京!勝政日式豬排等 6 品牌推脆薯、鬆餅限期半價 新竹巨城店「豬排買一送一」 2024-11-22 10:00
- 最新消息 快訊/勞動部霸凌案延燒 何佩珊請辭部長獲准 2024-11-22 09:49
- 最新消息 【世棒四強賽】「中華隊 vs. 美國」不能輸的壓力 最新運彩賠率曝光 2024-11-22 09:31
- 最新消息 【世棒四強賽】中華隊今11:00對美國背水一戰 派「左投奇兵」先發 2024-11-22 09:14
- 最新消息 美中防長會談取消 中國稱因美方不尊重台灣問題 2024-11-22 09:00
- 最新消息 親上火線!《英雄聯盟》T1 CEO 回應「轉會風波」,Zeus 經紀公司再發聲明:與真相不符 2024-11-22 08:39
- 最新消息 蓋茲涉性愛趴退提名 司法部長改由「佛州首位女總檢長」出任 2024-11-22 08:25

聶魯達電影的譯名,讓我想起一位朋友,他會在認識每一個新朋友的時候自我介紹:「我是一個詩人」,沈默數秒之後,看別人還沒反應,他就會補充一句:「我坐過共產黨的監獄。」(翻攝自IMDb)
電影《流亡詩人聶魯達》(又譯:《追捕聶魯達》)的中譯名,在單純的「聶魯達」上面加上了兩重前綴,又是「流亡」又是「詩人」,當然是擔心知道聶魯達的主流華人觀眾不多。這讓我想起我的一位朋友,他會在認識每一個新朋友的時候自我介紹:「我是一個詩人」,沈默數秒之後,看別人還沒反應,他就會補充一句:「我坐過共產黨的監獄。」
不過這次我對中譯名收貨,因為恰恰是在聶魯達身上,流亡二字使他真正回歸詩人身份,既不是尊貴的議員、也不是共產黨的喉舌、也不是窮人景仰的聖徒。這樣一個名滿天下的詩人聶魯達,只有在流亡狀態他重新身歷憂患,重新體會他之前掛在嘴邊的「我是人民的兒子」這句話的滋味,因為要不是人民,聶魯達不可能在獨裁者總統發起的300名警察的大追捕中活下來。
1948年的這次流亡,成就了聶魯達一生最輝煌的集大成之作詩集《漫歌》,包含了248篇詩,其中一章《逃亡者》就是專門吟誦電影所涉及的那一段流亡生涯的。電影裡有不少對此篇詩歌的呼應,主要呈現在一個個無名的工人、農民、妓女、學生等等對流亡的詩人的庇護與幫助。但電影還塑造了一個與聶魯達和他的朋友們迥異的角色:一位癡迷於追捕聶魯達的警探,由他的迷失與再生,證明詩的力量。
但當然,《流亡詩人聶魯達》並非一部雄辯的正能量宣傳電影,畢竟,那是一個詩人在流亡,而不是一種主義在流亡。導演帕布·羅拉雷恩這次有如詩神附體,用聶魯達的手段鋪陳瘋狂的細節之餘,更用波赫士的手段營造語言、影像乃至命運的迷宮。
妓女之子、黑警奧斯卡的命運與聶魯達的命運構成了一個神秘的迴圈,安第斯山的藍雪迷濛中,不只是聶魯達的詩句改變了奧斯卡,而奧斯卡對聶魯達名字「巴勃羅」的大聲呼喚,也是在叫喚詩人的初心歸位—作為美洲惠特曼傳統的繼承者,聶魯達承認生之喜悅,這是他詩歌的根柢,也是他超越史達林主義的跳板。
電影裡這種詩與主義之間的矛盾的張力一觸即發,尤其一位典型的窮苦出身的共產黨幹部質問聶魯達:「革命成功之後,是我們變成你這樣,還是你們變成我這樣?」聶魯達的答案是:「我們將在床榻上吃喝,在廚房裡做愛。」他畢竟選擇了詩歌,因為詩歌的超現實,是最誘惑人的革命。
另一個呼應的戲劇性高潮,在奧斯卡要拘捕聶魯達的愛人德莉亞的時候,德莉亞宣佈:奧斯卡是聶魯達虛構的逃亡史詩中的一個配角,奧斯卡不服氣地反問:哪你呢?你也是虛構的嗎?德莉亞一笑:不,我是永恆。這裡有個典故,歌德在《浮士德》所寫:「永恆的女性,引領我們上升。」毫無疑問,女性與公義,是驅動聶魯達詩歌的兩大原力,而如果沒有對前者的愛情,後者將會索然寡味,這也是導演一次次安排聶魯達朗誦「今夜我可以寫出最哀傷的詩篇」—《二十首情詩與一首絕望的歌》的第 20首—的意義。那個變性人通過詩的魅力學習了詩人的眾生平等,反之亦然,只有信奉眾生平等的詩人才能寫出這麼動人的詩。
在虛構中,黑警奧斯卡上升,成為人民之子;同時,被神化的詩人聶魯達下降,也成為人民之子—妓女和走私販、牛仔之子。有一個細節最有深意,當奧斯卡坐上摩托車奔馳在南美狹長的大地上的時候,眼尖的影迷都能看出這是切格瓦拉《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的影子,一個為獨裁者賣命的黑警和解放者切格瓦拉本來是死對頭,卻同在聶魯達的召喚下合為一體(切格瓦拉輾轉沙場時身上帶的也只有聶魯達和韓波的詩集)。
存在主義之後,每個人都是流亡者,流亡使個體從集體脫離,使巴勃羅從黨員聶魯達身上脫離,使奧斯卡從警隊的鐵血意志中脫離,使我們從一部想像的偉人傳記片中脫離,回到詩歌本身:追蹤蒼鷹的人,最終將學會飛翔。
【延伸閱讀】
廖偉棠專欄:這樣活 才算活過
廖偉棠專欄:殺死一間書店暴露一個城市的本質
廖偉棠專欄:與香港的救世主訣別
廖偉棠專欄:不許記憶也不許憧憬的此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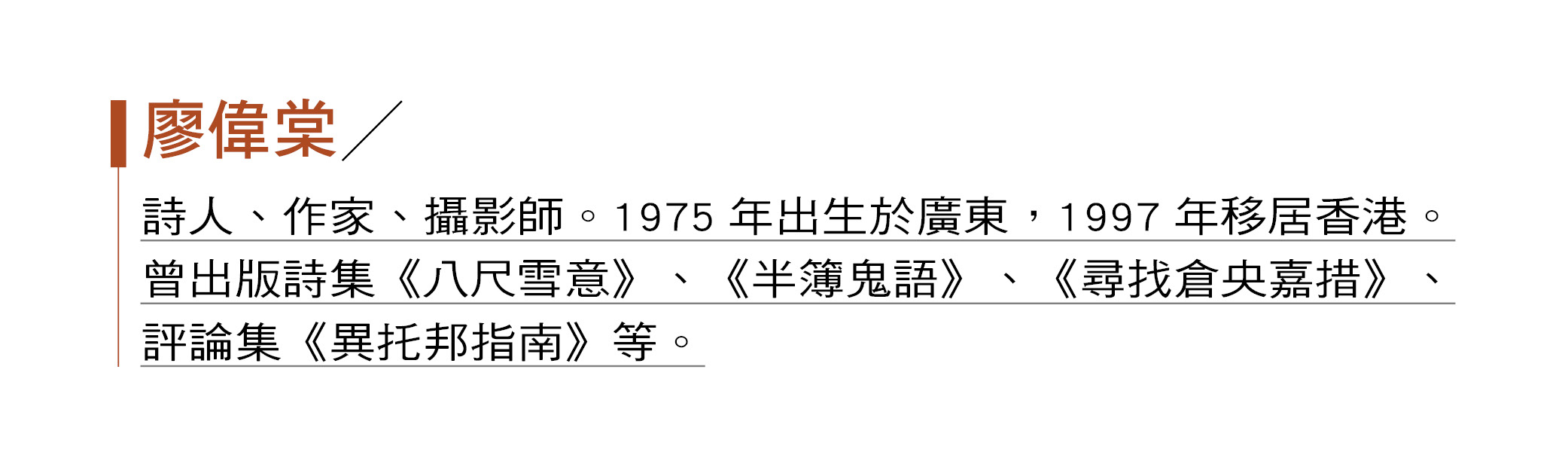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起底謝宜容!傳身家背景雄厚「善做公關」 先生和綠營高層有交情
- 一元特典!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釋出「零星票券」,11/24 採實名制一般販售
- 【世界棒球12強賽】滿足「2條件」台灣確定晉級4強 今晚是關鍵
- 先搶先贏!Ado 五月林口體育館演唱會採實名制入場,11/19 輸入「指定代碼」可優先預購
- 【內幕】T112步槍裝彈器採購案疑專利侵權 以色列向軍備局寄存證信函
- 王一博金雞獎典禮被抓包視線離不開趙麗穎 網揭兩人4年戀情無法曝光背後真相
- 勞動部涉職場霸凌不只謝宜容? 何佩珊:與輕生者中間還有2個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