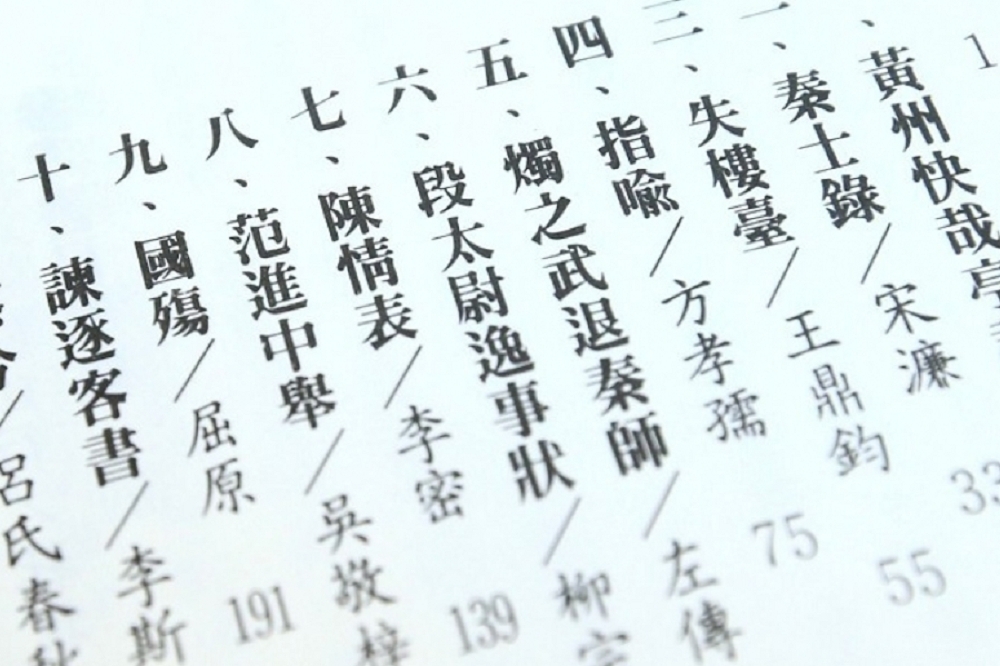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謝宜容起碼幹掉賴清德半壁江山 2024-11-22 00:02
- 最新消息 投書:立院惡鬥 只會讓更多科技人企業人不敢投身政壇 2024-11-22 00:00
- 最新消息 勞動部稱謝宜容失聯明天不出面 吳母淚控:霸凌太過分、太惡毒 2024-11-21 22:05
- 最新消息 俄烏戰況恐升級 烏克蘭是否有能力攔截ICBM 2024-11-21 21:50
- 最新消息 明後兩天各地氣溫回升 北部、東北部18到23度濕涼舒爽 2024-11-21 21:45
- 最新消息 劍橋詞典2024年度代表字出爐 「manifest」反映人們追求身心健康趨勢 2024-11-21 21:43
- 最新消息 為了9萬元勒斃馬國女大生 陳柏諺一審判賠父母逾638萬元 2024-11-21 21:32
- 最新消息 觸犯戰爭罪、違反人道法 ICC對納坦雅胡、哈瑪斯領導層發出逮捕令 2024-11-21 20:47
- 最新消息 【世棒四強賽】「CT AMAZE」自費飛東京應援 推掉台灣活動損失近10萬 2024-11-21 20:45
- 最新消息 蔡英文抵達加拿大 感謝台灣鄉親熱情接機 2024-11-21 20:37

文白之爭本就是一場註定沒有勝負的戰事,纏鬥無益;諸子百家誰高誰下,各有所宗,從來就不是定論;怎樣有恥如何無禮,更不是國文教科書或授業者可以定奪扭轉。(圖左為顧炎武畫像,合成圖片)
以古非今或以今非古,都不是教育的必要,尤其文言白話間的優劣評等。文白之爭,其來有自,百餘年前,爭的是書寫方式,搶的是普羅市場,所以有文言文是死東西不應繼續供奉之說;近年在意的是文化認同,所以有不讀文言文就是去中國化的焦慮。如果文言文等於中國化,那麼不太讀文言文的中國,文革起就已經去中國化了。
二十世紀前,口說手寫不同道,雙軌分明。孔子一句「大家來談談各自的志向吧」,門弟子們筆記下來的是「盍各言爾志」,而「願無伐善無施勞」也肯定不是顏淵的口語,誰會那樣說話。在語文雙軌的那二千年裡,任誰都能言詞便給指天畫地,卻未必能落筆成文,畢竟這是兩種不同本領。只不過這部一點也不口語的論語,偏偏被說是儒家重要的「語錄」。
二十世紀初,胡適的「我手寫我口」驚世現身,終結了語文雙軌的千年命祚,一舉把書寫跟口語綁作堆。胡先生屢屢親自示範白話文無拘無束免章免法的書寫速效,沒想卻讓「朝朝頻顧惜夜夜不相忘」這滿溢文言風采的白話,迄今仍被視為美句,沒給丟進垃圾桶。胡適的書寫革命,歷經百年洗鍊,鬆綁成了今天怎麼說就怎麼寫的不講修辭不必文法的書寫風格。然後人人能寫,也個個不解古文。
不解古文不是大罪過,就如同不懂俄文德文芬蘭文一樣而已。想了解康德,找懂德文的來協助,懂了,也不會變成康德;讀不懂報任安書,找懂古文的來搭橋,懂了,也不會變成司馬遷。文言白話都只是書寫的方式達意的載體,無干禮義廉恥忠貞廉潔等德目之稼接。置身客觀材料裡就能變身成材料中人,大概只有變色蜥蜴有此能耐,非人類所能及。畢竟,春秋經寫定已二千年,讀書人搖頭晃腦地讀出長篇巨論,可中國各朝各代不是照舊亂臣賊子百出,何來「春秋經成亂臣賊子懼」;在那苦讀而且只讀四書的科舉時期,千百年的時間,終究沒能產出另一組孔孟;不喜蘇東坡詩文的,再憤恨也不會因此變成王安石;沉迷俠義小說不能自拔的,怕也不會就此義從膽邊生,雖千萬人吾往矣。文言白話一樣有力,也一樣無力。
材料是客體,能否內化為個人品格或行事章法,乃存乎一心,迎拒之間,不是以何種方式書寫的問題,也不是考試分數或篇章多寡的結果。否則胡適不會批人「兩腳書櫥」,顯見「人書雙軌」從來不是特例,因此,不必對文言文期待太高奉為靈丹,也不必抬舉白話文說他能改造人心。

經史諸子都只是材料供給取用,要把材料形上成操守品德,聖人怕也無法承諾;但是,要把材料形下為實用物件,冬烘業師就能做到。詩經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讀了,離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罵名就遠一些,很實際;看到標緻佳人,有一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以獻寶,別有格調。看不慣門門通樣樣鬆的愛炫半調子,嘆一句「真是鼯鼠五技」,大概不會失禮;說不動兒女去追垃圾車,搬出「有事弟子服其勞」,可能可以少聽幾次為什麼是我的回嘴。
要文言文扛起移風易俗的大任,言之過重;要文言文讓口語優雅達情,卻是妥妥能行。一句士大夫之無恥謂之國恥,拿來說人鏗鏘有力,拿來律己就看自己高不高興,誰能奈何。學子之所以不喜古文,與其說是教忠教孝令人嫌厭,不如承認是章句註解的背誦惹人惱怒。是以,文言文不是寇讎,何必反目。就像,莎士比亞的戲劇慫恿不了天下男女都去私奔殉情,但是「to be or not to be 」「玫瑰不管叫它甚麼名字 都依然芬芳」,其俐落優美,卻是人人擷取。
文白之爭本就是一場註定沒有勝負的戰事,纏鬥無益;諸子百家誰高誰下,各有所宗,從來就不是定論;怎樣有恥如何無禮,更不是國文教科書或授業者可以定奪扭轉,不如把心力兜轉到眼下「天生就懂不必註解」的白話文。白話文不講文法不重文化,恐怕才是現今教育該看緊的事。
再怎麼直接的我手寫我口,總還有文法與對錯作為綱領,不是見仁見智歡喜就好。現今,尊稱自己是「王先生 張小姐」,稱美「黑道」為「人士」,介紹自己「已經將近二十幾歲」,打開電視「自強號列車撞到七十八歲老翁當場斃命」,轉台聽到「校長已經到達醫院對學生作出探視的動作」,林林總總的無章無法,明白彰顯了人文基本教育的低落,畢竟口說筆寫是人文素養與人文品質的表徵,實不容放任。把白話文章法端進教室,或許哪一天我們寫白話文的世世代代,能分辨:「學校的新規定,全校學生職員老師今天起進出校門都要配戴員工證教師和學生證」是錯誤的陳述(中國 大學入學考試考題),屆時,或許才能坦然面對白話文運動而無愧。
至於顧炎武,他不過是讀冊有感寫了篇名為廉恥的心得而已,就饒過他吧!
※作者為大學退休教師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起底謝宜容!傳身家背景雄厚「善做公關」 先生和綠營高層有交情
- 一元特典!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釋出「零星票券」,11/24 採實名制一般販售
- 【世界棒球12強賽】滿足「2條件」台灣確定晉級4強 今晚是關鍵
- 先搶先贏!Ado 五月林口體育館演唱會採實名制入場,11/19 輸入「指定代碼」可優先預購
- 【內幕】T112步槍裝彈器採購案疑專利侵權 以色列向軍備局寄存證信函
- 王一博金雞獎典禮被抓包視線離不開趙麗穎 網揭兩人4年戀情無法曝光背後真相
- 勞動部涉職場霸凌不只謝宜容? 何佩珊:與輕生者中間還有2個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