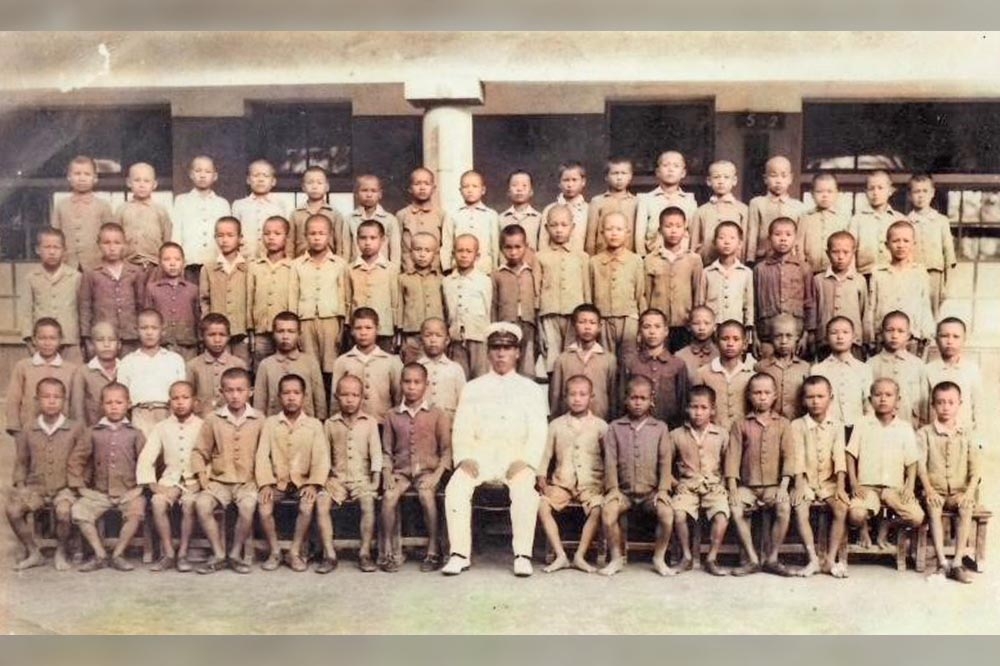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謝宜容起碼幹掉賴清德半壁江山 2024-11-22 00:02
- 最新消息 投書:立院惡鬥 只會讓更多科技人企業人不敢投身政壇 2024-11-22 00:00
- 最新消息 勞動部稱謝宜容失聯明天不出面 吳母淚控:霸凌太過分、太惡毒 2024-11-21 22:05
- 最新消息 俄烏戰況恐升級 烏克蘭是否有能力攔截ICBM 2024-11-21 21:50
- 最新消息 明後兩天各地氣溫回升 北部、東北部18到23度濕涼舒爽 2024-11-21 21:45
- 最新消息 劍橋詞典2024年度代表字出爐 「manifest」反映人們追求身心健康趨勢 2024-11-21 21:43
- 最新消息 為了9萬元勒斃馬國女大生 陳柏諺一審判賠父母逾638萬元 2024-11-21 21:32
- 最新消息 觸犯戰爭罪、違反人道法 ICC對納坦雅胡、哈瑪斯領導層發出逮捕令 2024-11-21 20:47
- 最新消息 【世棒四強賽】「CT AMAZE」自費飛東京應援 推掉台灣活動損失近10萬 2024-11-21 20:45
- 最新消息 蔡英文抵達加拿大 感謝台灣鄉親熱情接機 2024-11-21 20:37

P-51 長程戰鬥機護航B-52。(圖片摘自網路)
美機空襲、疲於奔命
有一天患重感冒,發高燒,咳嗽不停,完全失聲,頭部痛得要用毛巾綁緊,方能入睡。白天到醫院看病,軍醫從背部打了一針,叫我趴著休息。但很不巧,空襲警報響了,醫生、護士全都不見了,也沒有叫我躲避。我一起來迷迷糊糊地,就往工廠方向跑過去。只見工廠內空無一人,發覺不對勁,一慌張,也不會躲進防空壕,反而跑向利根川河岸,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回頭一看,挺進隊已放出煙幕彈,把工廠包圍在煙霧中。遠處看到美機正在轟炸一、二十公里外的太田飛機工廠,那時若美機空襲本廠,我大概凶多吉少了。
往後空襲警報的次數越來越多,連中餐時間也響。每次警報一響,大家趕緊掏出手帕,把飯一倒,包起來,然後一口氣喝完了湯,就往河岸跑去。工廠離利根川約二公里遠,有一回實在跑不動,竟然哭了出來。
有一天晚上,工廠遭遇轟炸。美機從空中投下的照明彈,劃過天空,恍如白晝。從防空洞口往外看,一草一木皆看得很清楚。第二天我們照常上班,但工廠已被炸得面目全非,水、電設備全壞了,無法動工生產。大家口很渴,只好拿了一個水桶,鏟了雪放在火裡燒。不過溶解的水不能喝,因為是油漆桶,油漆味太濃了。不得已,只好抓了雪放在嘴裡,含了半天,舌頭都凍僵了,而嘴裡的水卻只有一點點而已。
第二天不用上班,大家高興得不得了。全都跑到外面堆雪人,打雪仗,或在宿舍裡亂搗蛋。(恰巧這天是六十年來最冷的一天,攝氏零下二十七度)。小隊長一不高興,就把我們兩個寢室的十幾個人,集合在雪地上,做五分鐘的伏地挺身。手掌壓在雪地上,有如針刺般的難受,每人都哭了,很多人的手指,後來因凍傷而潰爛。
我們一中隊分為三小隊,住在同一寮。我們第三小隊的小隊長,對我們的管教特別嚴格。有次晚點名時,其他兩小隊都解散準備就寢了,但我們這一隊卻還在說教、體罰。大家實在忍無可忍,這時候幾個年紀較大、個子較高的同學,竟把小隊長狠狠地揍了一頓。後來這個小隊長就被大隊長調走了,大家都高興無比。
因為沒有工作可做,不久就被調回高座廠。工廠顯然已開始在做疏散工作,要我們搬運機器、材料等往山谷中的隧道送,並加以安裝。為了穩固機器的基座,也要搬運大石頭。一不小心,右手無名指被石頭壓到,雖然浸入麻醉劑中,還是痛的不得了,抖了兩、三個小時才停止。大概是骨頭被壓碎了,直到現在右手的無名指仍比左手的大些。
有一次於小徑上拉手推車時,美機忽然俯衝下來用機搶掃射。我們嚇得落慌而逃,猛往栗樹林逃竄,一直等到美機飛走了,才聽到警報聲響。敵機的空襲一天比一天激烈。日子久了,躲在隧道內,就能以飛機的引擎聲分辨出日軍、美軍一、二十種的機種、機型,並叫出它們的名字來。
我們的高座廠和橫濱港都,皆屬神奈川縣轄地。B-29都從相模灣的九十九里濱,飛進關東地區,這其間必須經過厚木的上空去空襲橫濱或東京。晚上空襲警報響了。我們趕緊背起行李,拿起棉被,有的躲進隧道或防空洞,我則跑往空曠的麥田去避難。
有一天清晨,上完夜班,回宿舍途中,美機又來轟炸鄰近的厚木海軍航空基地。平常我們都走森林小徑,但工廠與森林間,必須經過一片麥田,是屬危險地帶。突如其來的,美機向我們以炸機場的空中炸裂彈攻擊我們,我趕快臥倒在一棵大樹下的根部。瞬間有五、六個同學壓在我的身上,使我透不過氣來。美機飛走後,心神甫定,才慢慢爬起來。一看每個人的臉都嚇得面無血色。回到宿舍,才知道有六位台灣同學犧牲了生命。
精確轟炸、恐怖攻擊
白天從美軍太平洋艦隊起飛的艦載機,一波又一波地做小規模的轟炸與掃射,使日方的交通與農、漁牧生產陷於停頓、癱瘓。晚間則是從關島與塞班島起飛的B-29超級空中堡壘轟炸機,這種四引擎重型轟炸機航程達八千公里以上,運用當時最先進的雷達導引,在雲層中也能瞄準投彈,專門為精確轟炸設計。美軍用B-29做大規模的城市或軍需工廠的戰略轟炸,日夜不停,使得日本全國軍民都疲於奔命。

B-29在白天為躲避地面的炮火,飛得很高。因此發亮的機身,看起來只有幾公分大小。然而在晚間,就降下飛行高度,機身變大到約八十公分左右。而且它們不編隊,一架一架飛行。當B-29被地面的探照燈捕捉到了,就現出原形。此時四面八方高射炮陣地的探照燈,最少有兩枝馬上加入,把B-29照得更清楚。而首先的探照燈就即刻熄滅,以免被炸。這個時候,日軍的信號彈、曳光彈、高射炮彈,及夜間戰鬥機的槍彈,加上五枚一列的火箭彈等,在空中飛舞。而從B-29投下的子母燒夷彈,在空中爆炸。一顆子母彈可裂成好幾顆,再裂成十幾顆,最後分裂成長筒狀的幾十顆,並在空中就開始燃燒,掉下後地面馬上陷入一片火海。被打中的B—29隨即變成大火球,慢慢往下掉,或爆炸消失在黑夜中。這些情景在空中交义,編織成身歷聲綜藝大銀幕,遠勝過現在的好萊塢電影不知多少倍。
這個場景雖然好看,但對躲在麥田裡的我,不免心裡駭怕。加上天氣又冷,全身顫抖不止,牙齒也磕個不停,越用力咬住,想不叫它響,卻反而響得越大聲。有次一架B-29忽然離開機群,並降下高度,朝我們飛來。當我正在不知所措的時候,它投下了燒夷彈。而一公里遠的一家鐵工廠,瞬間起火燃燒,其命中率之高實在令人折服。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空襲橫濱的B-29,由硫磺島起飛的P-51野馬式戰鬥機護航,共約有五百架之多。高空的敵機在白天持續肆虐數小時,市區二十五平方公里起火燃燒,可是他們也損失了十架左右。後來我再到橫濱一次,映入眼簾的是,日本最大商港已成廢墟。沒有一間屋子是完整的,只剩下兩三枝煙囱,矗立在燒焦的田野中,憑弔著數以萬計的可憐犧牲者。
戰後我才瞭解,之前三月九日晚上的東京大轟炸,也是由近三百五十架的B-29執行,其投下的燒夷彈,炸死八萬四千人,傷四萬,比廣島的原爆還慘。東京四十平方公里起火燃燒,連市區河川的水都接近沸騰。而較晚飛到的B-29也因底下火勢過於猛烈,氣流擾動,而像羽毛一樣的在空中翻滾。而其他大城,如:名古屋、大阪等,也都沒能逃過B-29與燒夷彈的恐怖攻擊。
戰後我一直懷疑,在美國李梅將軍指揮下的B-29轟炸機群,將散布在日本各地的飛機工廠摧毀殆盡,但高座廠與我們的宿舍為何沒有被空襲?我猜美軍情報可能已經探知,有八千多名的台灣青少年在此工作,而饒了我們。要不就是冥冥之中有神明保佑著我們。
日本戰敗、等待遣返
八月上旬,廣島與長崎,相繼被原子彈攻擊。死傷以萬計的消息,傳到我們耳裡。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我們被告知穿上乾淨的衣服集合,聆聽天皇的玉音放送。日皇殷殷告知:日本已經戰敗投降。大家聽了有如晴天霹靂,滿心不甘,淚流不止,萬念俱灰,不知如何是好。然而想到能回台灣,心裡又雀躍不已。
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二月,等待船隻遣送回台灣的半年時間,我們八千多人的伙食都由彰化縣出身的二期生王文林學長,與神奈川縣政府交涉、打理,對他真是感激萬分。
此間有一次,和同學到橫須賀工廠的倉庫,搬取車床用的車刀,想回來換取零用錢。但是在電車上,有個同學與日本人發生爭吵,把對方刺傷了。當我們背著車刀,從橫濱站下車時,有三個同學被美國憲兵抓住,兩手舉起,罰站在鐘塔邊。我們一看苗頭不對,便把背包丟下,火速離開。
台中隊在回台灣的當天清早,因為天氣冷,在宿舍取暖,臨走時,並未把火熄滅,以致火苗從靠北邊的第十寮竄起來。木造的兩層宿舍,加上強風助長,一舍十二寮,很快就陷入火海中。大火中,木片瓦滿天飛,我和幾個同學趕緊各拿一條毯子爬上屋頂,把飛下來的火苗撲熄。等到厚木航空基地(麥可阿瑟將軍從這裡進駐,並佔領日本)的美軍消防隊趕來時,已無濟於事,整棟宿舍都已燃燒殆盡了。
第二天,美軍憲兵和日本人的舍監(當翻譯官),把我們集合起來訓戒一番。因為日本投降後,台灣已成為戰勝國,中華民國國民已不受日本警察管束。一旦出了什麼事情,就由美國憲兵來處理。我們自己也有自治隊的組織,外出可以坐上聯合國的專用列車,暫時享受了戰勝國莫名的驕傲。美國兵看了覺得奇怪,常拿我們的證件,看了又看,然後點點頭,比手劃腳一番。
美國駐軍的軍營,每天三餐時間都看見日本人排隊領取剩飯。他們很有秩序地一個兵倒給一個人。日本人拿了就走,不會計較拿得少或多取一份。雖然戰敗了,仍保有那一份尊嚴。聽說各大城市的車站、地下道,都發現有凍死、餓死的人,聽了不免起了惻隱之心。
苦等了半年,終於輪到我們要回家了,但是心中仍覺得有些徬徨與感傷。日本已由內地變成異國,不知何時還能再到日本來?坐專用列車到橫須賀途中,由車窗眺望外面的山川草木,不禁勾起了依依不捨之情。在同意書上偷蓋了父親的印章,抱著無比的希望,忍辱負重,為它流血、流汗,努力奮鬥,生死與共的日本帝國,如今安在?
返抵台灣、家人團員
我們從橫須賀軍港旁的小港—浦賀,登上八千多噸的永祿號貨輪。因為船無法靠岸,必須由駁船接駁,再攀登三、四層樓高的小梯子上船。當時已近黃昏,有個同學,因視線不良,一不小心失足掉落海裡。等到撈起來時,已回天乏術了,看了令人鼻酸,唏噓不已。
回程的船比較大,不像二年前來時那樣暈船。有一天海上起霧,為了安全,船一路上鳴著汽笛。很靠近了,才發現左舷有一艘船擦身而過。當交會時,兩艘船都稍偏離了航道。直到通過後,才又恢復直線的航路。
當時有兩位學長,帶日本小姐同船回來。幾天過去了,情不自禁地在艙角擁抱接吻。不巧被同學們發現了,引來一陣騷動,成為船上的趣聞。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午后,隱約可看到台灣陸地了。啊!美麗之洋,婆娑之島,福爾摩莎!多麼懷念的故鄉!日夜盼望著、憧憬著、思念著,愛慕著的家園終於到了。算算時間,已經快兩年沒有吃過香蕉和砂糖了。台灣貨幣和日本內地只有五角錢的紙鈔可以通用。有些同學用一條毯子,以繩子綁著垂下去,和小艇上的船伕,交換一串香蕉吊上船。
由船上看到岸上的中國兵,他們的裝備與紀律和日本漫畫書所畫的一模一樣。這是祖國的軍人嗎?日軍雖然解除了武裝,但是還穿著英挺的軍服,排著整齊的隊伍,等著搭我們這艘船歸國去。中國兵和日本軍人一比,真是天壤之別。這樣的軍隊,能夠打敗日本,成為戰勝國,真是令人難以相信。大家議論紛紛,失望極了!
第二天,二月十六日早上,船慢慢駛入基隆內港靠岸。中午過後,我們一行一千多人,才陸續地踏上故鄉土地。
我也上岸了,第一件事就是去買糖果吃。忽然有一位同班同學跑來告訴我說,我母親來接我了。我以為他開玩笑,不敢相信,怎麼有可能呢?通訊已經中斷一年多了呀!同學硬拉著我去見母親。真的,不是作夢,我衝過去抱住她,叫了一聲「阿母」,就哭了出來。所謂「喜極而泣」大概就是這樣。我生平第一次感受這種激動又甜美的滋味。
母親說,我去日本不久,就舉家搬到桃園大溪找父親。因為惦念我這個長子,她每天清晨,都到風景秀麗,三面環水的觀音廟去燒香膜拜;求神保佑我平安,早日歸來。真是「天下父母心」,使我知道了母愛的偉大。本來母親是聽人家說:從日本回台灣的輪船上,因有人患了霍亂,被隔離在港內。她是抱著一絲希望,前來一探究竟的。沒想到佛祖賜奇蹟,憑著「母子連心」的感應,讓她來到港口,接到了心肝寶貝的兒子。我相信我們八千多位同學中,一定沒有像我這樣的第二個幸運兒,這一切真要感謝上蒼。
從日本帶回來的一千圓日幣,只換到七百元台幣。而在國民黨統治下,通貨膨脹,物質更為缺乏,一台斤的米已飛漲到十六元;戰前一碗麵五分錢,此時已經變成天方夜譚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家父調勤到新竹。我在台中師範畢業後娶了新竹北門望族吳家的小姐,新竹就成了我的第二故鄉。


※本文為廖受章(日名:吉川受富)回憶錄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起底謝宜容!傳身家背景雄厚「善做公關」 先生和綠營高層有交情
- 一元特典!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釋出「零星票券」,11/24 採實名制一般販售
- 【世界棒球12強賽】滿足「2條件」台灣確定晉級4強 今晚是關鍵
- 先搶先贏!Ado 五月林口體育館演唱會採實名制入場,11/19 輸入「指定代碼」可優先預購
- 【內幕】T112步槍裝彈器採購案疑專利侵權 以色列向軍備局寄存證信函
- 王一博金雞獎典禮被抓包視線離不開趙麗穎 網揭兩人4年戀情無法曝光背後真相
- 勞動部涉職場霸凌不只謝宜容? 何佩珊:與輕生者中間還有2個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