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陳椒華宣布退出時代力量 未獲家人同意不會再參加政黨 2025-05-10 20:41
- 最新消息 快訊/美方斡旋成功 印、巴同意立即全面停火 2025-05-10 20:39
- 最新消息 【立委網路聲量】黃國昌嗆辣發言負面聲量奪冠 這2人靠高仇恨值入榜 2025-05-10 19:12
- 最新消息 為停火設下新條件 克宮發言人:西方武器必須停止流向烏克蘭 2025-05-10 19:07
- 最新消息 俄烏戰爭、加薩衝突難解 WSJ:川普私下坦承很受挫 2025-05-10 19:03
- 最新消息 「新竹港南遊GO好動生活節」登場 運動MIX觀光全民動起來 2025-05-10 18:50
- 最新消息 【大罷免臉譜】罹癌化療仍義無反顧撂落去 苗栗罷團靈魂人物AMI真情告白 2025-05-10 18:40
- 最新消息 中國籍配偶上街遊行 要求政府放寬現行補件規定 2025-05-10 18:28
- 最新消息 成毅新劇《赴山海》再掀起爭議 女二李凱馨陷辱華風波戲份竟比女主古力娜扎多3倍 2025-05-10 18:03
- 最新消息 總統候選人整合失敗 南韓執政黨陣前「換洙」重啟提名表決 2025-05-10 17:40

屈原人格貫穿兩千餘年的中國史,成為君主專制制度重要的道德基礎。而今,我們要紀念的是一個以美勝過強權的屈原,我們要告別的是為君王分憂、至死忠誠的屈原人格,如此而已。(中國荊州屈原像/維基百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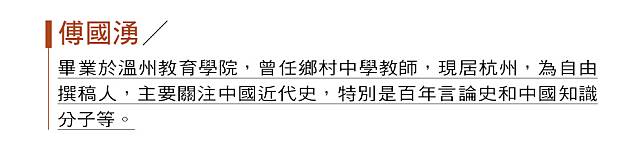
每年到端午節,總會有許多人想起屈原。屈原是誰?胡適甚至懷疑歷史上是否真有屈原其人,他在1922年寫的《讀<楚辭>》一文中提出這一疑問,他認為屈原是一種複合物,一種「箭垛式」的人物,與黃帝周公同類,與希臘的荷馬同類。
在胡適之前,廖平也提出過這樣的疑問,認為屈原並沒有這人,司馬遷的《屈原賈生列傳》中的事實前後矛盾,既不能拿來證明屈原出處的事蹟,也不能拿來證明屈原作《離騷》的時代。
郭沫若寫了一篇長文《屈原研究》,不同意他們的看法,認為還是要相信和屈原相去不遠的人們的著述,在司馬遷之前,就有長沙王的太傅賈誼,賈誼離屈原一百多年,又是在長沙,曾親眼見過屈原的故老都是有存在的可能,關於屈原的傳說也還十分新鮮。所以賈生的《吊屈原賦》中就說:
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
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
司馬遷把他倆合在一起做傳不是無緣無故的。
另外一位以楚國最後舊都壽縣為封地的淮南王劉安,寫過一篇現已失傳的《離騷傳》,但在司馬遷筆下有所引錄。
郭沫若相信屈原是真實存在的,並且推算出屈原出生在上距孔子卒(前479)139年,下距秦始皇兼併天下(前221年)57年,處在中國的文化最為燦爛的時代,是在情感方面發展的純粹詩人,與同時代的那些學者、策士很不一樣。這一論斷很值得注意,也正是《離騷》、《天問》這些詩篇,讓屈原戰勝了無情的時間。試問,今天還有誰關心楚懷王、上官大夫之流?權勢榮華不過一時,曇花一現,轉眼成空,而詩人在憂愁憂思中上天下地,所袒露的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心靈,兩千多年來一直引發人們的共鳴。
聞一多就是一個,雖然他不相信端午節起源於對屈原的紀念,據他考證相關傳說(粽子、端午和屈原)最早的記載是在《續齊諧記》,這是南朝梁時吳均的筆記體小說,同時代的《荊楚歲時記》也有類似的說法。端午這個節日遠在屈原出世前就已存在,變為屈原的紀念日又遠在屈原死去之後。但對於詩人屈原,他的推崇是由衷的,稱之為「人民的屈原」—「端午是一個人民的節日,屈原與端午的結合,便證明了過去屈原是與人民結合著的,也保證了未來屈原與人民還要永遠結合著。」
他甚至說,對於暴風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斃的楚國人民,《離騷》喚醒了他們的反抗情緒,楚亡於人民革命,非亡於秦,秦國大軍一到,那種潰退和叛變的方式,就是向萬惡的統治者報復。「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又是楚人對暴秦的反抗。
他說,陶淵明歌頌過農村,農民不要他;李白歌頌過酒肆,小市民不要他;杜甫是真心為著人民的,人民聽不懂他的話。只有屈原,沒有寫人民的生活,訴人民的痛苦,實質上等於領導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報了一次仇。
與其說聞一多在闡釋詩人屈原,不如說在自道心曲,他寫這篇《人民的詩人—屈原》是在1945年6月,他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已漸近沸點。僅僅一年多後,他即遭遇慘烈的暗殺。
魯迅不懷疑屈原的存在,完成於1926年的《漢文學史綱要》中即有專篇講《屈原與宋玉》,對於屈原的《離騷》有極高的評價—「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後人驚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產,故稱‘楚辭’。較之於《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然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對於屈原生平,魯迅相信《史記》所述,然對於屈原其人,他並不一概肯定,1932年,他在《言論自由的界限》一文中說:
「其實是,焦大的罵,並非要打倒賈府,倒是要賈府好,不過說主奴如此,賈府就要弄不下去了。然而得到的報酬是馬糞。所以這焦大,實在是賈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會有一篇《離騷》之類。三年前的新月社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似的境遇。(他們只不過批評)不料‘荃不察餘之中情兮’,來了一嘴的馬糞…」。(《魯迅全集》第五卷,115頁)
如果說,這只是魯迅慣用的雜文筆法,嬉笑怒駡皆成文章的需要罷了。那麼,1935年,他在《從幫忙到扯淡》一文說得很清楚:「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魯迅全集》第六卷,344頁)在他生前這篇雜文被官廳檢查封殺了,直到他死後1937年7月才收入《且介亭雜文二集》公開發表。
魯迅稱《離騷》「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讓我想起胡適的說法:「屈原的傳說不推翻,則《楚辭》只是一部忠臣教科書,但不是文學。」也讓我想起上世紀八零年代,我曾讀到過的論述:「屈原的那種對等級專制的絕對忠誠,對昏君、貪官、小人的刻骨仇恨和對人民的同情完美地結合在《離騷》之中」。15年前,我曾寫過一篇小文《告別屈原人格》,大致上是就是這些思路的繼續。
今天(端午節)早上起來,看到一位朋友發來的粽子畫,我在微信上轉發時寫了一段話:
粽子畫,竟可以如此之美!唯有美,可以勝過一切無情、無聊、無趣、無恥的時代,美,正是抵禦專橫權勢、守護人類乾淨心靈的最後一道防線。
我想到的是屈原,在他所在的時代,他不就是一個美的象徵嗎?連他的自沉也成了一種悲劇的美。秦、楚之爭誰勝誰敗,興耶亡耶,變得多麼次要,千載之下,這一切難道還看不分明嗎?《史記》所論定的—「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原人格貫穿兩千餘年的中國史,成為君主專制制度重要的道德基礎。如果說屈原為楚而死、為楚而憂,確不值得。個體生命的寶貴遠高過他所忠誠的物件,在文明史的譜系中,比起那些顯赫的成功,更有價值的還是個體的情感、想像和心靈的追求,最後能在時間中留下來的也是這樣美好的價值。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兮遲暮。
……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
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告別屈原人格,並不是告別在審美意義上的屈原,隱藏在他詩篇中的那種超越時間的美,又如何告別得了,那才是楚人楚地之魂。楚王的權杖早已被折斷,秦皇的霸業也不過是驪山腳下的土堆,兵馬俑的陣勢無論如何雄壯也只是死的文物。而屈原仍活在這些詩中,這些詩中隱藏著他活的心靈。就算沒有端午節,沒有粽子,有這些詩句,他就不會在文明的時間中消失。楚必亡,秦也必亡,亡秦必楚,又何必一定要等到秦亡的那一刻,即使楚秦未亡,那些寄託在這個個體身上的美好價值也照樣會長存世間。在這個意義上,糞土當年楚懷王,糞土當年秦始皇。在強大的權力遮天蔽日、窒息人間一切正義的長夜漫漫之中,個人如何找到自己得以留存的價值,古往今來,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曾在心中追問,答案早已不言自明。今天,我們要紀念的是一個以美勝過強權的屈原,我們要告別的是為君王分憂、至死忠誠的屈原人格,如此而已。

【延伸閱讀】
●羅世宏專欄:連胡舒立也不得不低頭的時候
●羅世宏專欄:書店無罪 獨立其罪
●廖偉棠專欄:殺死一間書店暴露一個城市的本質
【熱門影片推薦】
●臉書進軍影視界!
●川普旅遊禁令復活
●梅伊以10億英鎊換北愛小黨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