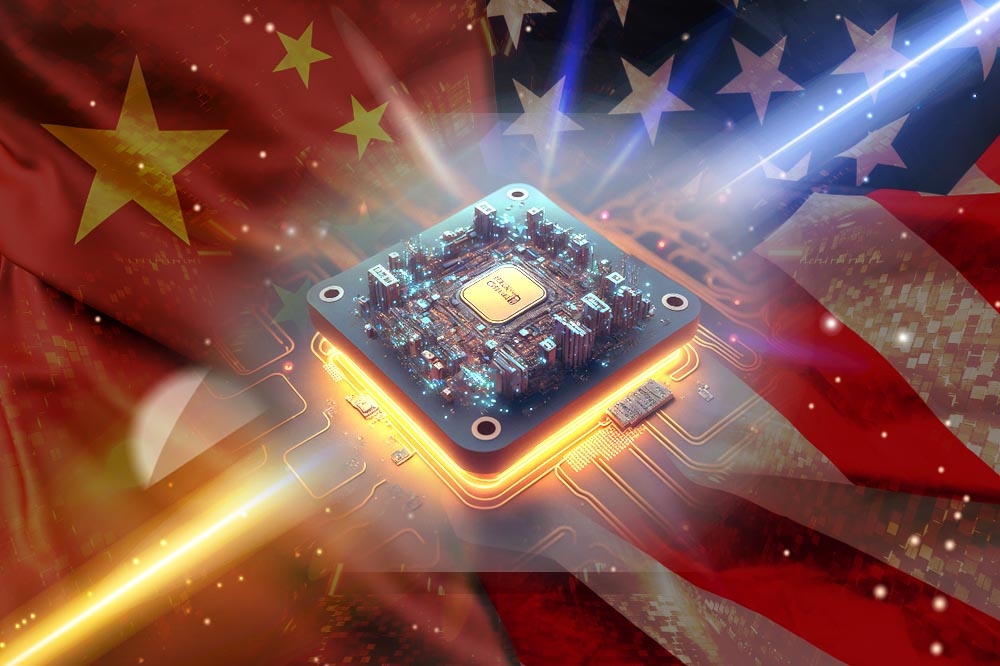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謝宜容起碼幹掉賴清德半壁江山 2024-11-22 00:02
- 最新消息 投書:立院惡鬥 只會讓更多科技人企業人不敢投身政壇 2024-11-22 00:00
- 最新消息 勞動部稱謝宜容失聯明天不出面 吳母淚控:霸凌太過分、太惡毒 2024-11-21 22:05
- 最新消息 俄烏戰況恐升級 烏克蘭是否有能力攔截ICBM 2024-11-21 21:50
- 最新消息 明後兩天各地氣溫回升 北部、東北部18到23度濕涼舒爽 2024-11-21 21:45
- 最新消息 劍橋詞典2024年度代表字出爐 「manifest」反映人們追求身心健康趨勢 2024-11-21 21:43
- 最新消息 為了9萬元勒斃馬國女大生 陳柏諺一審判賠父母逾638萬元 2024-11-21 21:32
- 最新消息 觸犯戰爭罪、違反人道法 ICC對納坦雅胡、哈瑪斯領導層發出逮捕令 2024-11-21 20:47
- 最新消息 【世棒四強賽】「CT AMAZE」自費飛東京應援 推掉台灣活動損失近10萬 2024-11-21 20:45
- 最新消息 蔡英文抵達加拿大 感謝台灣鄉親熱情接機 2024-11-21 20:37

共產黨對李登輝與李光耀倆人的評價截然不同。(美聯社)
如果都由一個大得遠非一般人所能測度或理解的組織去獨攬一切權力和作出大多數重要決定,我們將絲毫不能維護和培育民主。對此,如果我們能夠創造一個適合於小國生存的世界,那對我們大家都會更有好處。
海耶克
毛澤東說:「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善於鬥爭和善於統戰的中共,對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分辨得清清楚楚。
最近四十年來,中共政權以國家級媒體鋪天蓋地地批判乃至謾罵的「箭垛」式人物,主要有四位:達賴喇嘛、李登輝、彭定康、蓬佩奧。
中共宣傳機構給達賴喇嘛扣的帽子有:罪犯、叛徒、分裂份子、惡魔。西藏自治區共產黨頭子潑婦罵街式地攻擊說,達賴喇嘛是「披著袈裟的豺狼,人面獸心的怪物」。對此,達賴喇嘛一點也不生氣,反而笑稱:「如果使用此類語言來描寫我可以讓中國官員高興的話,他們應該繼續下去。我會很高興提供血液樣本,讓科學家決定我是人還是禽獸。」
中共宣傳機構形容末代港督彭定康為「千古罪人」。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表示:「香港回歸祖國已經二十三年了,末代港督彭定康作為賊心不死的老殖民主義者,仍不停對香港事務指手畫腳、妄加置喙,這種自不量力的倒行逆施可笑又可恥!……公然與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作對,已經並且必將繼續遭到世人的唾棄,留下歷史的罵名!千古罪人彭定康一定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彭定康則在演講中引用東德歷史指出,極權政府若果崩潰,往往只是一瞬間的事,而要事情有所改變,需要有勇敢的人站起來,捍衛美好、正確、良善的事。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還在任時,中國中央電視臺一連三天在新聞聯播中對其點名批評,指他「散播政治病毒,將自己變成人類公敵」、「背負四宗罪,喪失做人底線」、「硬是把在中情局期間撒謊、欺騙的那一套帶到美國外交場合,斷崖式拉低了美國的聲望」。蓬佩奧後來在回憶錄中點名中國三百八十次,在演講中稱,對自由世界,中國是比當年納粹德國更大的威脅。
中共對李登輝的仇恨,跟以上三人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九九四年六月十四日,中央電視台、新華社同時點名批判李登輝,七月與八月發動兩次「四評李登輝」系列文章,這八篇文章都以《人民日報》與新華社聯合評論員的名義發出,是中共最高等級的批判文章。毛時代批判蘇俄用了「九評」,如今單單批判李登輝一人就用了「八評」——「八評」之後,還意猶未盡,八月下旬,在李登輝宣布參選翌年首次民選總統時,新華社又發表題為<李登輝其人>的萬字長文,「把李登輝掃進歷史的垃圾堆,是海峽兩岸中國人民共同的歷史責任」。

與之相反,李光耀是極少數被中共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季辛吉亦有此「殊榮」)的外國元首。在北京舉行的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大會上,已故的李光耀獲習近平頒發「中國改革友誼獎章」。
但中共變臉比翻書還快。言猶在耳,二零二三年五月,在香港審計署建議圖書館加強檢視館藏、以維護國家安全後,香港公共圖書館下架若干書籍和紀錄片,僅關於「六四」的書籍和紀錄片就有四十多項下架,其中包括新加坡出版的、反映李光耀觀點的《李光耀看六四後的中國·香港》。連李光耀都上了禁書作者名單,可見在「今上」習近平眼中,新加坡模式早已雨打風吹去。
李光耀是現實主義者,他對「六四」被屠殺的學生沒有太多同情,卻也承認那是一場「悲劇」。他發現這是新加坡的機會:當時香港人心惶惶,出現新一波移民潮。他指出,當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後,中國政府將為所欲為;當涉及權力鬥爭時,中共根本不會在乎國際聲譽——他對中共本質的認知,比絕大多數香港人清醒和深刻。他曾向香港議員代表團建議,他們應該組織起來,集合全港最重要的二十萬人與中國談判,一旦中央過度干預香港,這批菁英就會離開,拖垮香港行政及經濟命脈(若這些人真的離開香港,李光耀敞開懷抱歡迎他們到新加坡定居)。李強調,這個「非衝突性」的方法可應付中國,屆時中國必須聆聽。但香港民主派領袖李柱銘樂觀地認為,香港可「民主回歸」乃至推動中國民主轉型,對此建議不加考慮。
李光耀有時情不自禁地火中取栗,但確實是最早從中國發現商機的外國人之一。從一九七零年代末鄧小平剛掌權開始,他就全力推動新中合作,不止於經濟層面,更涉及政治層面——更準確地說是行政層面。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無論「三個代表」,還是「和諧社會」,背後都隱然將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萬年執政模式作為學習的榜樣。
一九九零年代初,新加坡與中國達成中國高級官員到新加坡考察訪問、短期進修的合作計畫。最早招收中國官員的南洋理工大學,從一九九二年開始辦一週至三個月的短期培訓班,內容包括經濟管理、企業管理和公共管理,至今受訓者已超過一萬人。為因應中方不斷增長的需求,南大自一九九八年又開辦為期一年的管理經濟學碩士課程,二零零五年更與中共中央組織部及各省市組織部合作開辦公共管理碩士課程。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市長班」。後來,國立新加坡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也為中國官員開辦高級公共行政與管理碩士課程。二零一零年四月,到訪新加坡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李源潮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致辭說,中國把新加坡作為領導幹部海外培訓首選,是因為新加坡的發展經驗對中國有特殊的借鑒作用:「新加坡在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矛盾,和正在探求的解決辦法,正是我們現在遇到或將要遇到的矛盾,我們現在需要用或探索將要用的辦法。」李光耀對這類培訓寄予極高期待,但成果遠不如預期——中共官員學到的新加坡威權模式,不可能與中共極權模式無縫接軌。這種培訓無非是中共官員「洗學歷」的終南捷徑。
習近平剛被確立為接班人時,對新加坡模式饒有興趣。李光耀是習近平「立儲」後會面的第一個外國客人。見面時,李光耀故作謙虛地說:「再過十年、二十年,你們將不再需要我們。」習近平立即表示:「不,我們在未來的很多年都會需要你們。我去過新加坡,我知道你們有什麼,我們的人民想從中學習。我們希望向你們學習。我們從你們身上學到的要比從美國學到來的多。」李由此頗感寬慰:「這不是隨便說說的客套話。因為去美國,制度、環境對他們來說是陌生的,看到的東西是西方的處事方式。在這裡,他們來看我們是如何吸收西方的方式,並融入亞洲的環境。因此,他們發現我們很有用。」

習近平上台第二年的二零一三年,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表了一篇題為<建設服務型政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經驗與啟示>的文章,認為人民行動黨「有自覺為國為民服務的執政理念」。二零一五年,在中國引人矚目的微信號「學習(暗指習近平之習)小組」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習近平、李光耀與新加坡模式>的文章,文章指出:「新加坡模式不時受到一些西方學者的批評,認為是『假民主』、『櫥窗民主』……但新加坡的成功在於它充滿著深深的憂患意識,特別是人民行動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非常重視民意的習近平,已經嘗試對公眾的期待做出回應。他和他的團隊正在尋找一種有效的發展模式,對於中國來說,新加坡模式允許更多的自由經濟政策,同一黨執政並存,這一點很有吸引力。」
然而,實際上,早在胡溫末期,新加坡模式在中國的光環就已開始黯淡。習近平更是斷然丟開新加坡這個光鮮的榜樣,重新撿起「太祖」毛澤東的鏽跡斑斑的遺產——新加坡不再是中共黨內新星競相前往的鍍金之地,井岡山和延安才是,在「革命老區」興建起規模龐大的、作為中央黨校分校的幹部培訓機構。對習近平來說,中國未來只有一種模式,即毛澤東模式——他連新加坡幫助培養的技術官僚都不予信任。他要重建鐵桶般的極權制度,新加坡的威權制度他已然瞧不上眼。
李光耀與李登輝是同齡人,也都是客家人,他們對兩個以華裔族群為主體的國家——新加坡與台灣——都擁有類似國父的崇高地位。中共對他們的評價天壤之別,他們的政治遺產確實是南轅北轍。《李非李:李登輝與李光耀》是我繼《偽裝的改革者:鄧小平與蔣經國》之後第二部「比較政治學」專著。若再放寬視界,還可納入另外幾位同為一九二零年代出生的政治人物——美國總統老布殊、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德國總統魏茨澤克、日本首相村山富市、中共黨魁江澤民等——進行比較研究。
從某種意義上說,李登輝的道路就是台灣的道路,李光耀的道路就是新加坡的道路。對兩人的比較,也是對兩國道路和發展模式的比較。未來,新加坡與台灣何去何從,尚有頗多未知之數;而未來中國的轉型之路,是學新加坡,還是學台灣,對中國、亞洲乃至世界而言,更是影響深遠。
本書第一章「國族與價值認同的轉換及調適」,討論李登輝與李光耀兩位客家人,身負相似的客家文化,最後為何背道而馳。兩人在年輕時代都曾是左派,執政之後都成為某種程度的右派,倒應了愛因斯坦的名言:「三十歲之前不是左派,說明此人沒有良心;三十歲之後仍是左派,說明此人沒有理性。」兩人關於「亞洲價值」與「普世價值」的爭論,決定了兩人治國方略的重大差異。
本書第二章「日治時代的愛與恨」,李登輝與李光耀都曾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生活過,且都較為主動地參與殖民政權。但日本對台灣和新加坡採取不同的殖民模式,使得兩人對日本統治當局印象迥異,當然影響到兩人後來的對日外交政策及地緣政治觀念。李登輝的親日自不待言,李光耀的反日亦是淵源有自。
本書第三章「英風去矣,美雨猶在」,比較李登輝留美和李光耀留英的不同觀感與機遇。李光耀留英時,英國正處於二戰後的殘破狀況,左派思潮崛起,福利國家成形,殖民地的民族主義勃興。李光耀未能洞悉英國文化及制度的優長,反而產生強烈的反英意志。而李登輝兩度留美,均是在美國戰後成為超級強國的黃金時代,不僅深入學習美國的農業、經濟、技術,更受美國基督教文明的吸引,後來受洗成為基督徒,沐浴在美式清教文明的雨露之下,形成古典自由主義的世界觀
本書第四章「被強迫的獨立與被禁止的獨立」,探討新加坡與台灣陰差陽錯、擦肩而過的命運:李光耀力圖讓新加坡成為馬來西亞聯邦的一部分,卻遭馬來西亞驅逐,被迫走向獨立,卻鍛造出一個宛如「當代雅典」的亞太地區最富庶的城邦國家。而李登輝的願景是如摩西般帶領台灣人「出埃及」,卻受制於嚴酷的國際環境和台灣內部的認同分裂,只能走出形塑「中國民國在台灣」的小半步,台灣未來是繼續維持中華民國的法統,還是製憲正名,尚待未來的台灣主流民意來決定。
本書第五章「『他的黨』與『不是他的黨』」,呈現兩位黨魁與黨的不同關係:李光耀是人民行動黨名副其實的「黨父」,逐步排除黨內競爭者和不同派系,讓該黨成為他一個人的黨,黨內無派,唯有「李光耀派」;而且,新加坡是內閣制,李光耀先控制了黨,進而順理成章地控制議會、政府和國家。反之,李登輝加入國民黨這個「百年老店」,是半推半就的,他意外成為總統和黨主席之後,在激烈的政爭中擊敗所有挑戰者,鞏固了權力,推動了政治改革,改變了「中華民國」的特質,卻始終未能成功將國民黨改造成議會制下的競選型政黨,最終他與國民黨決裂。
本書第六章「威權教父與民主先生」,描述李光耀與李登輝不同的個性、思維方式及對政治的認識。如果說新加坡是幼稚園,李光耀就是幼稚園園長;如果說新加坡是幫派,李光耀就是幫派的教父。新加坡沒有言論自由,尤其是沒有批評李光耀的言論自由,所有批評他的人都被以「法制」或其他手段整得傾家蕩產乃至鋃鐺入獄。而李登輝雖善於奪取和運用權力,卻深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故而還權於民,實現總統直選,不惜讓自己成為被反對派攻擊和辱罵的對象。
本書第七章「從『二龍相會』到『李不見李』」,梳理「二李」奇特的互動方式——「因不了解而走近,因了解而分手」。李光耀與蔣經國是惺惺相惜的好友,他以為蔣經國的接班人李登輝必然是「蔣經國第二」,最初懷著這種心情與李登輝交往。但兩人的不同氣質,以及兩國國家利益的分歧,讓「二李」很快凶終隙末、分道揚鑣。
本書第八章「共產中國是友邦,還是敵國?」,分析李光耀與李登輝的重大分歧之一是對共產中國的不同看法。李光耀認為中國未來將取代美國成為亞洲乃至全球霸主,故而新加坡必須向中國示好,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分得一杯羹。而李登輝認為,中國這個龐然大物,其實是外強中乾的泥足巨人,台灣必須與之保持距離。新加坡以中國為友邦乃至盟主,而台灣以中國為惡鄰和敵國。兩人逝世後不到十年,世界對共產中國的看法已經丕變。兩人孰對孰錯,後人自能判斷。
本書第九章「新加坡奇跡與台灣奇跡,誰能持久?」,通過揭秘兩國經濟奇跡的來龍去脈,預測這兩個同為「亞洲四小龍」的國家未來的發展。李光耀和李登輝都已逝去,但他們生前的競技尚未結束,他們的政治遺產將面臨時間與民意的嚴峻考驗。
本書並不標榜所謂的客觀中立,對李登輝和李光耀做出明確的褒貶:褒揚李登輝而貶斥李光耀。不是作者對人物本身有強烈的偏見或成見,而是作者對民主、自由、人權等理念有堅定的認同和持守。在此意義上,本人是價值一元論者。
李光耀終身沒有走出威權主義的陰影。他對中共的專制統治表示理解:「一人一票制度從未在中國存在過,也絕不會帶來一個繁榮的中國,他們不會嘗試這種制度。」他為中共的極權體制背書,否定中國會成為自由民主國家(新加坡本身亦非自由民主國家),因為「中國若成為民主國家,則會崩潰。關於這一點,我很肯定,中國知識分子也了解。……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今天都跑到哪裡去了?他們完全不相干了嘛。」他還說:「我不認為你可以把和一個國家的過去毫無關聯、完全陌生的標準強加在他們身上。要求中國成為民主國家也是一樣。五千年來有記錄的歷史中從來沒有數過人頭;所有的統治者以皇帝之權力統治;如果你不同意,就砍人頭,不是數人頭。」李光耀被譽為哲學家和思想家,其實他的哲學和思想與鄧小平水準差不多,是「摸論」(摸桌石頭過河)和「貓論」(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耗子就是好貓)而已。他的文化、人種和地理決定論,根本不合邏輯。也違背事實——日本、南韓、印度、台灣包括新加坡在內的諸多亞洲國家,在其歷史上沒有存在過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但並不意味著他們現在或未來就不能擁有此種制度。制度可移植,制度也非永遠一成不變。
而李登輝對民主自由理念的信仰,不僅改變了台灣,更啟發中國及其他非民主國家的民主轉型之路。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三日,李登輝在美國阿拉斯加世界事務會議午餐會上發表題為<台灣與亞太的民主>的演講:「在個人執政、開啟台灣民主化的道路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讓台灣人民,走出白色恐怖的陰影,讓人民可以自由的表達他們的意見,表達他們對於政治,以及台灣自己未來前途的看法,甚至勇於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與制度。這也是為什麼,台灣在過去二十年來,在人民自主的思考下,逐步走出過去日本統治與中國帝國的陰影,釐清自己和中國的關係,找到自己的認同,以台灣作為主體,重新定位台灣自己,以及台灣與亞太、國際的關係。台灣也因為這種自由與思想上的解放,以及對自己理想的追求,展現台灣蓬勃的經濟與創意,邁向現代化的國家。」他特別梳理了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對於亞洲多數政府及領導人而言,如何走出專制與獨裁的迷思,在政治體制上,徹底民主化,讓政治權力回歸人民,而不在是由執政者或是少數統治階層獨斷,是重要的一步。在個人執政期間,如何讓台灣從過去的戒嚴體制,回歸正常的民主體制,將主權還給人民,正是個人推動台灣民主化的第二步。這也是為什麼個人在推動的過程中,廢除所謂的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讓憲法回到正常的運作;讓憲法的適用回歸到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讓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選出真正代表他們的民意代表;讓兩千三百萬人民,用選票直接選出他們自己的總統。這對父權文化下的亞洲領導人而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相信人民會作自己的判斷和抉擇,將權利還給人民,正是民主化的最大關鍵。」
通過對李登輝和李光耀的比較,以及台灣道路和新加坡道路的比較,再以此作為審視中國的鏡子,就能得出簡單而確鑿的結論:被中共視為朋友的,必定是壞人(中共現在連李光耀父子這樣的朋友也不要了,唯有普丁這樣更壞的人才配做中共的朋友);被中共視為敵人的,必定是好人(達賴喇嘛、李登輝、彭定康、蓬佩奧均是如此)。中共從來都是「擇惡固執」,它所選擇的道路,必定是歧途(中共現在連新加坡道路都不要了,只願意走毛澤東的道路);而中共堅決拒絕的那條道路,就是李登輝的民主化之路,就是正道與大道。

※本文為《小國巨人:李登輝與李光耀》(五南出版社)作者自序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起底謝宜容!傳身家背景雄厚「善做公關」 先生和綠營高層有交情
- 一元特典!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釋出「零星票券」,11/24 採實名制一般販售
- 【世界棒球12強賽】滿足「2條件」台灣確定晉級4強 今晚是關鍵
- 先搶先贏!Ado 五月林口體育館演唱會採實名制入場,11/19 輸入「指定代碼」可優先預購
- 【內幕】T112步槍裝彈器採購案疑專利侵權 以色列向軍備局寄存證信函
- 王一博金雞獎典禮被抓包視線離不開趙麗穎 網揭兩人4年戀情無法曝光背後真相
- 勞動部涉職場霸凌不只謝宜容? 何佩珊:與輕生者中間還有2個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