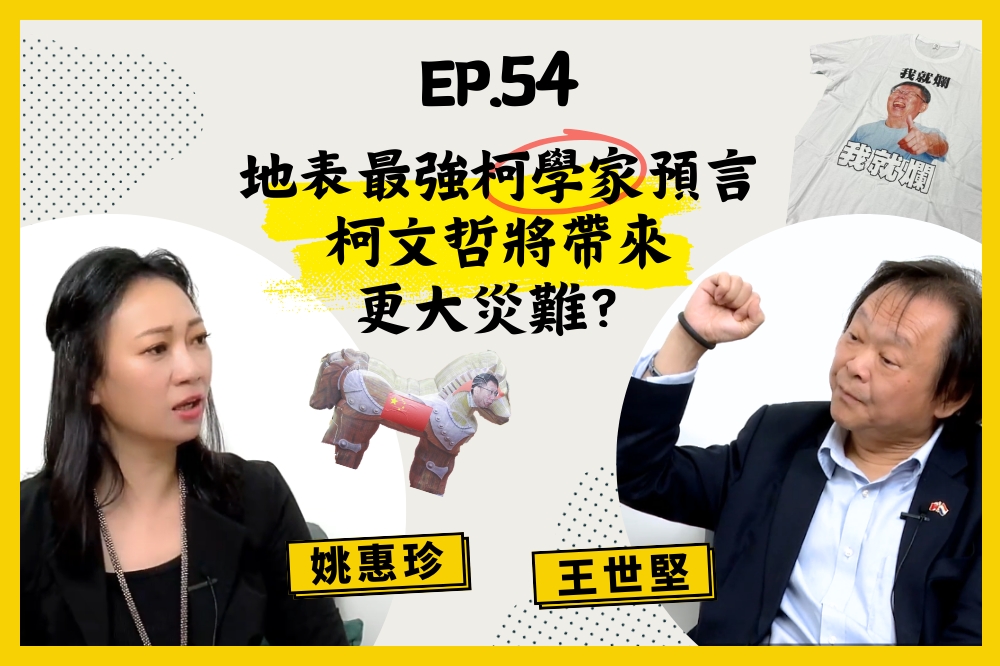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謝宜容起碼幹掉賴清德半壁江山 2024-11-22 00:02
- 最新消息 投書:立院惡鬥 只會讓更多科技人企業人不敢投身政壇 2024-11-22 00:00
- 最新消息 勞動部稱謝宜容失聯明天不出面 吳母淚控:霸凌太過分、太惡毒 2024-11-21 22:05
- 最新消息 俄烏戰況恐升級 烏克蘭是否有能力攔截ICBM 2024-11-21 21:50
- 最新消息 明後兩天各地氣溫回升 北部、東北部18到23度濕涼舒爽 2024-11-21 21:45
- 最新消息 劍橋詞典2024年度代表字出爐 「manifest」反映人們追求身心健康趨勢 2024-11-21 21:43
- 最新消息 為了9萬元勒斃馬國女大生 陳柏諺一審判賠父母逾638萬元 2024-11-21 21:32
- 最新消息 觸犯戰爭罪、違反人道法 ICC對納坦雅胡、哈瑪斯領導層發出逮捕令 2024-11-21 20:47
- 最新消息 【世棒四強賽】「CT AMAZE」自費飛東京應援 推掉台灣活動損失近10萬 2024-11-21 20:45
- 最新消息 蔡英文抵達加拿大 感謝台灣鄉親熱情接機 2024-11-21 20:37

台灣警察體系多年來「不合理的績效要求」,常使第一線員警疲於奔命,甚至鋌而走險,以違法方式執法。(資料照片)
面對他人所施加的暴力,我們尚可能有一絲還手或抵抗的力氣;然而,若今天施加暴力的是國家,我們該拿甚麼,與之抗衡?
6月26日是「國際反酷刑日」,今年,我們也迎來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通過的第四十周年。台灣自詡為人權立國的法治國家,我們理所當然地以為,刑求、虐囚早已走入歷史。然而,近期警察濫權、暴力執法等亂象頻生,不禁使我們反思,「酷刑」,是否只是藏得更深?
今年2月,屏東縣警局發生員警在執法過程中毆打嫌疑人,疑似導致嫌疑人死亡;沒過幾日,又發生武陵派出所的員警,在無具體事證的前提下,集體刑求一名路過派出所的17歲少年。巧合的是,這兩起案件,員警執法過程中,都「剛好」沒有開啟密錄器。
再回顧到近年廣為人知的員警執法過當事件:一位彰化少年只因長相被誤認為逃逸移工,被便衣警察突然抓捕導致受傷縫了17針(2023年7月);三重警察將民眾誤認通緝犯,毆打、噴灑辣椒水導致民眾多處受傷(2022年9月);中壢的警察非法盤查一名音樂老師,並對她大外割、上銬(2021年4月);高雄監獄管理員率雜役虐囚,將受刑人暴打致死(2019年10月)。事實上,警大2020年的研究報告便指出,2015年至2020年的五年間,便有56則關於警察不當執法的新聞,可能符合酷刑及其他不當對待案例。
這反映了兩大問題:
其一,是我國警察體系存有需通盤性檢討的問題,像是警察體系多年來「不合理的績效要求」,常使第一線員警疲於奔命,甚至鋌而走險,以違法方式執法。前述的不當盤查、警察誤認並毆打、當街壓制民眾等案件,都顯現警察績效制度及相關原則法制化問題,非常需要檢討改善。
其二,從早期江國慶、蘇建和、邱和順等冤案當事人被屈打成招、甚至枉死,到近期前述的多起警察執法過當、侵害人權案件,都在在顯示出國家應該正視「防範酷刑機制」的重要性與迫切性。
「酷刑」存在於人類社會幾千年之久,人們想出許多新奇巧妙卻無比殘忍的方法,施加痛苦於他人,並享受對他人施虐的過程。甚至在中世紀以及早期現代社會,「酷刑」是法律上的合法行為,並在道德上獲得容許。然而,「酷刑」是人類社會中殘忍、羞辱性極高、踐踏人性尊嚴的極端行為,往往造成酷刑受害者身心靈上難以回覆、治癒的創傷。
《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於1984年12月10日於聯合國大會通過,並於1987年6月26日正式生效,6月26日這天並被訂為「支持酷刑受害者國際日」。儘管現今社會,我們似乎對「酷刑」深惡痛絕,但世界各地,包括現今的台灣社會,仍有許多我們看不見的地方,正不斷在絕望的尖叫與哀號聲中上演著一次次慘無人道的「酷刑」。
行政院曾在2018年完成《禁止酷刑公約施行法》草案,把該公約及其議定書國內法化,落實相關規定跟國家義務;並送立法院審議,期許與國際人權標準接軌。遺憾的是,後續未能在立法院三讀通過,不了了之。
六年後的今天,上述的多起不當執法、國家暴力案件讓我們了解到,「酷刑」在台灣尚未遠離,為了避免未來更多受害人求助無聲、求償無門,《禁止酷刑公約施行法》仍有它的必要性及急迫性。台灣若能儘速通過《禁止酷刑公約施行法》,並在國家層級設置獨立防制酷刑機制,來確保各機關確實落實公約規定,或許才能完整國家人權保障所缺失的那一塊拼圖。
※作者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法案助理研究員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起底謝宜容!傳身家背景雄厚「善做公關」 先生和綠營高層有交情
- 一元特典!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釋出「零星票券」,11/24 採實名制一般販售
- 【世界棒球12強賽】滿足「2條件」台灣確定晉級4強 今晚是關鍵
- 先搶先贏!Ado 五月林口體育館演唱會採實名制入場,11/19 輸入「指定代碼」可優先預購
- 【內幕】T112步槍裝彈器採購案疑專利侵權 以色列向軍備局寄存證信函
- 王一博金雞獎典禮被抓包視線離不開趙麗穎 網揭兩人4年戀情無法曝光背後真相
- 勞動部涉職場霸凌不只謝宜容? 何佩珊:與輕生者中間還有2個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