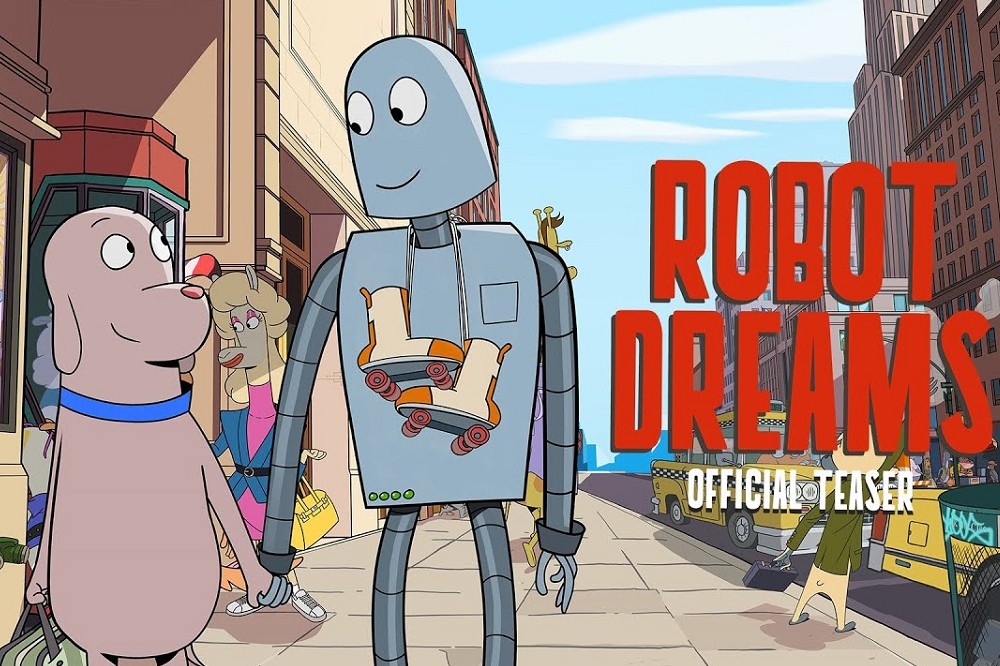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謝宜容起碼幹掉賴清德半壁江山 2024-11-22 00:02
- 最新消息 投書:立院惡鬥 只會讓更多科技人企業人不敢投身政壇 2024-11-22 00:00
- 最新消息 勞動部稱謝宜容失聯明天不出面 吳母淚控:霸凌太過分、太惡毒 2024-11-21 22:05
- 最新消息 俄烏戰況恐升級 烏克蘭是否有能力攔截ICBM 2024-11-21 21:50
- 最新消息 明後兩天各地氣溫回升 北部、東北部18到23度濕涼舒爽 2024-11-21 21:45
- 最新消息 劍橋詞典2024年度代表字出爐 「manifest」反映人們追求身心健康趨勢 2024-11-21 21:43
- 最新消息 為了9萬元勒斃馬國女大生 陳柏諺一審判賠父母逾638萬元 2024-11-21 21:32
- 最新消息 觸犯戰爭罪、違反人道法 ICC對納坦雅胡、哈瑪斯領導層發出逮捕令 2024-11-21 20:47
- 最新消息 【世棒四強賽】「CT AMAZE」自費飛東京應援 推掉台灣活動損失近10萬 2024-11-21 20:45
- 最新消息 蔡英文抵達加拿大 感謝台灣鄉親熱情接機 2024-11-21 20:37

《陽子之旅》裡,日本沒有接住陽子,就像沒有接住311震災後的東北。(《陽子之旅》宣傳照)
你是I(內向Introvert)人還是E(外向Extrovert)人?這是近幾年社交媒體常常出現的提問,附加一些帶廣告的測試題。其實何須測試,I人不會不知道自己I,E人不在乎E還是I,或者說E總是想I走出來,而不知道I走不出來。
我很老實,在一開始看熊切和嘉導演的《陽子之旅》的時候,代入的就是那個幽靈:小田切讓飾演的父親角色。我想像我死去的時候,我的兒子也許就是像主角菊地凜子那樣反應的,因為他是I人,他會讓周圍的人覺得他冷漠麻木,實際上他們內心波濤洶湧,但要他濺出來一星半點浪沫非常艱難,E人們會費盡努力而不得,因為他自有自己表達痛苦的方式。
互聯網時代幫助了他們的繭式生存,也好,因此《陽子之旅》裡菊地凜子飾演的42歲單身女子陽子可以在東京以從事網上客服工作謀生,她甚至可以不介意什麼差評,只有當她的手機摔壞,也需要網上求助客服,她才意識到自己的工作意味著什麼,她也只是停頓了片刻。很多I人幸運擁有藝術去表達自己,陽子沒有,她只有睡前看一些蒼白的喜劇消遣,而這些喜劇描繪的是E人的幸福生活。
因此當互聯網驟然終止的時候,才是陽子必須面對自己的時候。手機摔壞了,她沒有接到父親去世的消息,因此第二天只能跟著上門的表兄坐車回鄉。家鄉在青森,離東京720公里,對於陽子表兄來說不過是開車大半天的事,對於陽子無異於時空旅行一般艱難,她要穿越的除了空間距離,還有二十年的時間距離,以及,無法測量有多遠的與人之間的心理距離。
就在第一個服務區,陽子就跟表兄一家走失了,錢包和行李拉在表兄車上。幾近身無分文也沒有手機的陽子,開始了她一個人的奧德賽,一路向北,658公里,一路掙扎。電影院的宣傳說:「奧斯卡提名女星菊地凜子,聯同驚喜客串的小田切讓,帶來一齣中年女性的勇敢救贖之旅——沿路靠著坐順風車回家的陽子,一夜之間遇上形形色色的有緣人,在她與自己和解的路途上送她一程。」
這未免有點粉飾太平了,救贖?形形色色的有緣人?視乎如何看緣字,也許這說的是Karma。接載陽子的第一人,失業主婦,對社會有無從發洩的怒火,只能神秘地跟陽子說,而在取不得陽子認同之後,漠然把她拋在一個荒僻的臨時停車處;第二人是截車旅行的女大學生,她讓陽子想起那個和自己截然不同的妹妹,因此當她向陽子親暱撒嬌的時候,陽子本能地把她推開了,當下一輛願意接載的車來到,女大學生離開了陽子,留給她一條圍巾。
下一個出現的男人,戴著賑災報導作家的光環,但對陽子不奏效,於是圖窮匕現要脅陽子以肉體交換接下來的行程。此人的偽善與暴力,徹底擊垮了陽子,她奮力反抗逃出旅館,精疲力盡倒在海邊。在這時給予她額外一擊而不是幫助的,依舊是父親的幽靈,男人喚起對父親暴力的回憶——也許不是實在的暴力,而是父親那一代檢討受害人的態度。
這時我突然醒悟,那個由頭到尾不著一詞的父親小田切讓,甚至片中壓根沒有提及的母親,他們應該也是極端的I人,在他們那一代會自我壓抑自我改造的I人。他們的痛苦未嘗不比陽子大。
那兩個接下來在路上不由分說接上陽子的老農民夫婦,可以說是陽子心中期待的理想父母化身,這才是緣。他們不追問陽子、也不向陽子抱怨和情勒,默默為她準備好接下來的順風車與衣物。最關鍵的是,他們沒有想要陽子由I變成E。陽子握緊他們的手,在之後的旅程卻無法握上已經和她並排坐在汽車後座的父親幽靈的手。
隨著父親下葬的時刻接近,陽子咬牙打破隨身的牆壁,一再懇求冷漠的大多數路人帶她一程,坐上車之後還有長篇獨白反思自己⋯⋯這部分並沒有鼓舞我,反而是看得心如刀割——她不應被如此審判的。陽子其實自知無法打破,就在她深夜打通阿姨的電話又掛掉那時就很清楚。
陽子竭盡全力奔赴的,也許是自己的葬禮——當她打開家門,鏡頭裡並沒有父親之靈堂,導演很善良,也很殘酷,他甚至沒有安排陽子的妹妹出來迎接她。陽子告別的,只有一段歲月,陽子學會的是什麼呢?導演的答案是:日本沒有接住陽子,就像沒有接住311震災後的東北。我們也沒有接住陽子,因為我們都慢慢變成了J人(J,Judging),如此這般對別人的人生評頭論足。
※作者為詩人、作家、攝影師。1975年出生於廣東,1997年移居香港。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尋找倉央嘉措》、評論集《異托邦指南》等。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起底謝宜容!傳身家背景雄厚「善做公關」 先生和綠營高層有交情
- 一元特典!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釋出「零星票券」,11/24 採實名制一般販售
- 【世界棒球12強賽】滿足「2條件」台灣確定晉級4強 今晚是關鍵
- 先搶先贏!Ado 五月林口體育館演唱會採實名制入場,11/19 輸入「指定代碼」可優先預購
- 【內幕】T112步槍裝彈器採購案疑專利侵權 以色列向軍備局寄存證信函
- 王一博金雞獎典禮被抓包視線離不開趙麗穎 網揭兩人4年戀情無法曝光背後真相
- 勞動部涉職場霸凌不只謝宜容? 何佩珊:與輕生者中間還有2個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