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大巨蛋類地震】比照小巨蛋「禁跳令」? 北市議員:建管處可做周邊建物安全評估 2024-12-22 20:48
- 最新消息 【TPBL職藍】新北中信特攻邀海巡署長張忠龍開球 號召青年一起守護海洋 2024-12-22 18:56
- 最新消息 俄烏戰爭下是否該抵制〈胡桃鉗〉 立陶宛文化部長發言重掀激辯 2024-12-22 18:55
- 最新消息 柯建銘稱財劃法有折衷批韓朱卻硬幹 朱立倫:邊打邊談算哪種協商? 2024-12-22 18:52
- 最新消息 準颱風「帕布」水氣周一來會更濕冷 周五夜冷氣團再襲低溫下探13度 2024-12-22 18:25
- 最新消息 高捷列車車門「錯位」手動停靠引議 官方:安全無虞、深表歉意 2024-12-22 18:18
- 最新消息 【迎接2026】台北101跨年煙火搶先曝光 聚焦12強奪冠、融入台灣流行樂 2024-12-22 17:58
- 最新消息 《九重紫》大結局倒數最新預告曝光 李昀鋭中毒吐血孟子義用「這方法」餵藥又甜又虐 2024-12-22 17:45
- 最新消息 【大巨蛋類地震】「三天三夜」嗨唱掀共振效應專家解答 北市府暫不禁止跳動 2024-12-22 17:30
- 最新消息 《九重紫》李昀銳與孟子義戲份慘遭配角強壓收視暴跌 「他」演惡男頻頻搶戲全網唾棄 2024-12-22 17: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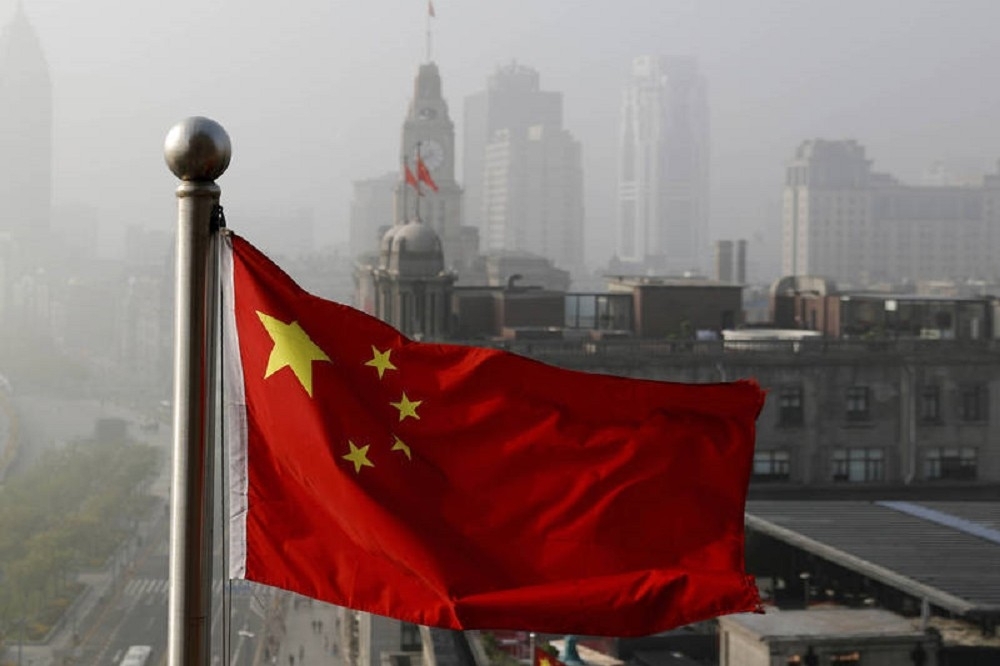
儘管近年來在資料蒐集上較為受限,但從長期、整體的觀點來看,中國研究仍是朝向正面發展的。(美聯社)
隨著近年來中國政經情勢的變遷,特別是習近平領導下政治控制的緊縮,與中國有關的研究面臨比過去更多挑戰。不論是外國學者欲赴中國進行田野調查,或是獲取境內的統計數據,都變得異常艱難,導致不少中國研究者的焦慮感乃至悲觀論升溫。然而,若借用「世界體系」(world-systems)觀點俯瞰近半世紀以來中國與世界關係的變化,筆者認為中國研究仍呈現出相當樂觀的圖像與想像。1979年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變得更緊密也更複雜,從邊陲國家(periphery)逐漸發展成半邊陲(semi-periphery),更在部分區域和領域邁入核心國家(core),甚至在全球範圍與美國展開地緣政治爭霸。上述發展使得中國研究在經驗上更寬廣、多元,在理論上更靈活、創新,相關知識的供給和需求也持續不斷擴大,因此儘管近年來在資料蒐集上較為受限,但從長期、整體的觀點來看,中國研究仍是朝向正面發展的。
更寬廣、多元的經驗現象
首先,中國作為一種經驗現象,明顯地更寬廣、更多元了。近半世紀以來,中國加入了全球化和世界經濟分工體系,其國際角色發生變化:起初作為外來資本與技術的接收國,扮演世界工廠的角色,出口「Made in China」商品,以賺取外匯;其後開始有能力轉為資本與技術的輸出國,向開發中國家用基礎建設換取自然資源,並向已開發國家攫取尖端技術,以追求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逐漸在部分科技領域取得全球領先的地位。隨著中國「走出去」,中國研究也跟著「走出去」了。中國研究的範圍變得更寬廣,主題也變得更多元,不僅限於中國本身的經驗,更擴及更多世界各地與中國有關的現象。比如,過去研究關注中國本身的農民工及血汗工廠,現在則關注中資公司在海外自然資源開採產業的勞動關係;以前研究關注中國內部的言論審查和網路監控,現今則開始關注中國的大外宣、假訊息操作,乃至數位威權輸出。
在此脈絡之下,中國研究在國內外學界都面臨是否需要重新界定範圍、甚至重新命名的議程。例如,在研究社群方面,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早從2004年就創設了以「China and the World」為名的研究項目,英國的艾希特大學則在2010年代提倡「Global China」的概念並成立以之為名的研究中心(Global China Research Centre),臺灣的中研院民族所亦在2021年組成「世界化中國」(Global China)研究群。在學術出版方面,澳洲墨爾本大學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已規劃在今(2024)年底以「Global China」為名舉辦年度論文研討會,而作為全球學術出版重鎮的劍橋大學出版社更自2022年起新增了「Global China」專書系列。在高等教育方面,上海紐約大學、香港科技大學、丹麥奧爾堡大學等皆設有「Global China Studies」相關學位學程。上述研究及教學項目的名稱演變,雖不表示中國研究的領域名稱必須有所調整,但已顯示隨著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深化,中國研究的經驗範圍已有擴大的趨勢。
更靈活、創新的理論變項
另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理論變項,不再像過去一樣較常扮演依賴變項(dependent variable)的角色,而是隨著與世界關係的演變,更有機會在更多情況下扮演獨立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的角色。如以世界體系的概念來做類比,中國以往作為邊陲國家,其狀態或變化較常處於依賴他國、受影響的地位,如今發展成半邊陲乃至核心國家,其內外作為皆更有對他國造成影響、甚至宰制的可能性。據統計,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在1980年排名全球第11位,到了2023年已躍升至第2位,僅次於美國;其人均GDP則從1980年的全球第149名提升至2023年的第71位;其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亦從1990年的全球第105位上升至2022年的第75位。上述指標反映中國數十年來在世界體系之中日益升級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

在此趨勢下,中國研究已然衍生出一些新興的研究方向和創新的理論概念。傳統的中國研究多是以中國為主體的轉型研究或比較研究,其宗旨在於探討「中國是如何被(內外因素)影響的」,而一個新興的研究方向則是關於「中國影響力」的研究,其目的在於釐清「中國是如何發揮影響的」。例如,中研院社會所早自2010年便開始倡議「中國效應研究」(China Impact Studies)並為之成立專題研究小組,國內外學界也陸續產出許多探討中國如何對世界各地不同層面發揮影響的研究成果。上述發展促進了中國研究新興領域的理論創新。例如,臺灣學者吳介民提出「中國因素」分析架構,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創造「銳實力」(sharp power)此一權力概念,跨國學者應用傳統的民主輸出(democracy promotion)理論建構出新興的「威權擴散」(authoritarian diffusion)理論。這些新興理論的普及化顯示中國被視為潛在的獨立變項有其需求及合理性。
資料局部受限,但整體更豐富
近年來,中國研究的資料蒐集面臨巨大挑戰,主因是中國政府在習近平治下加強了對公共空間和學術領域的言論控制,同時建立對境內數據的管制,導致外國研究者難以赴中國進行田野調查,亦不易蒐集和取得統計數據,此情況對質性及量化研究都構成一定阻礙。但如前所述,過去數十年來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深化,使得中國研究在經驗上更寬廣、多元,在理論上也更靈活、創新,這些都讓中國研究資料蒐集的空間和場域不再僅限於中國本身,而是擴及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與社會,此部分的訪調工作較不受中國政府的干預。除此之外,由於新科技的進步與輔助,資料來源和蒐集方法已不再局限於傳統的實體場域,而是得以擴展至網路媒體和社群平臺等虛擬空間,這有助於研究者突破以往的地理限制,延伸可資利用的數據及資料範圍,並提升蒐集效率。
更重要的是,中國在經濟和科技上的崛起,對於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造成威脅,導致更多研究機構和政策智庫願意針對中國研究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資源,這也讓相關資料的數量和品質有所提升。例如,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長期追蹤並評比世界各國的人權與民主狀態,近年卻特別針對「北京的全球媒體影響」(Beijing’s Global Media Influence)進行跨國調查並建立指標;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開發了中國科技公司海外合作網絡的資料庫;臺灣民主實驗室嘗試分析中國在世界各國多個領域的影響程度並建構「中國影響力指數」(China Index);臺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IORG)致力於觀測並記錄中國相關行為者的網路足跡及資訊操作動態;自由之家臺灣辦公室的異言網(China Dissent Monitor)計畫則為中國內部遭威權壓制的異議行動建立資料庫。這些研究資源的投入,與中國的言論緊縮相互加減之下,使得可資運用的中國研究資料來源不僅未減少,反而可能更豐富。
知識供給與需求的擴增
從知識的供給面來看,傳統的中國研究者固然仍是相關知識生產的主力,但隨著中國在不同地區、各領域及層面的影響力擴散,近年來出現越來越多「非典型」的中國研究者,他/她們原本並非專門做中國研究,但因為所關心的議題(可能是香港的城市農業,或是東南亞的族群政治)涉及中國的影響,故而開始涉足以中國為重要個案或變項的研究,成為相關知識生產的生力軍。以澳洲學者克萊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為例,他原先是一位關注氣候變遷、過度消費、永續發展等議題的發展經濟學者,過去幾年由於注意到中國政府對其他國家(特別是澳洲、北美及歐洲各國)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的滲透,因而投入中國影響力相關研究,已出版了《無聲的入侵》(Silent Invasion)和《黑手》(Hidden Hand)這兩本重要著作。除了學院研究者以外,如前所述,各國政策智庫也為了應對中國在全球及區域的霸權競爭,而提高了中國研究的投入和產出,這相應地增加了相關知識的供給。有鑑於此,現階段中國研究可望在傳統研究者的深厚基礎、非典型研究者的創新思維、以及智庫研究者的實務邏輯之間取得交流和整合,共同營造出更新鮮而豐富的知識成果。

另一方面,中國研究的知識需求也有所增長。在學術領域,中國研究的讀者很可能不再僅限於傳統的中國研究學者和學生,前述「非典型」的研究者和學生也需要多加參考、引用相關研究成果。以在中國研究領域具代表性的國際期刊《China Quarterly》與《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為例,其在2010年代的平均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均顯著高於2000年代的平均值。除了學界人士之外,中國研究的知識需求也擴及到其他公民社會、企業、政府當中的非學界人士。尤其自由世界的人們擔心中國崛起將對美國領導下的既有國際秩序、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帶來衝擊,因此亟需增進對中國的了解和掌握,以解除焦慮或找到因應之道。此一新興需求的有效滿足,有賴中國研究學界與各知識流通部門(包括出版社、各級學校、社區大學、公共及商業媒體、獨立書店、公民團體等)協力合作,方能將相關研究成果予以科普化與通識化,進而在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之中推廣並實踐「中國識讀」。
牆再高、浪更遠
綜合而言,儘管近年中國政治環境緊縮導致有人對中國研究的未來感到憂慮,但近半世紀以來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深化,及其國際影響力的強化,已然使得中國研究在經驗上、理論上、知識供給面及需求面的「質」與「量」均有所提升。雖然中國築起言論高牆,但中國研究已經「住到海邊」去了,短期且局部的限制終究抵擋不了長期而整體的趨勢。由此觀之,全球中國研究仍有著值得期待的樂觀前景,而臺灣的中國研究享有高度學術自由,也因地緣、歷史及語言因素而具備相對優勢,可望持續幫助世界了解中國,在當代重要知識的前沿占有一席之地。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執行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