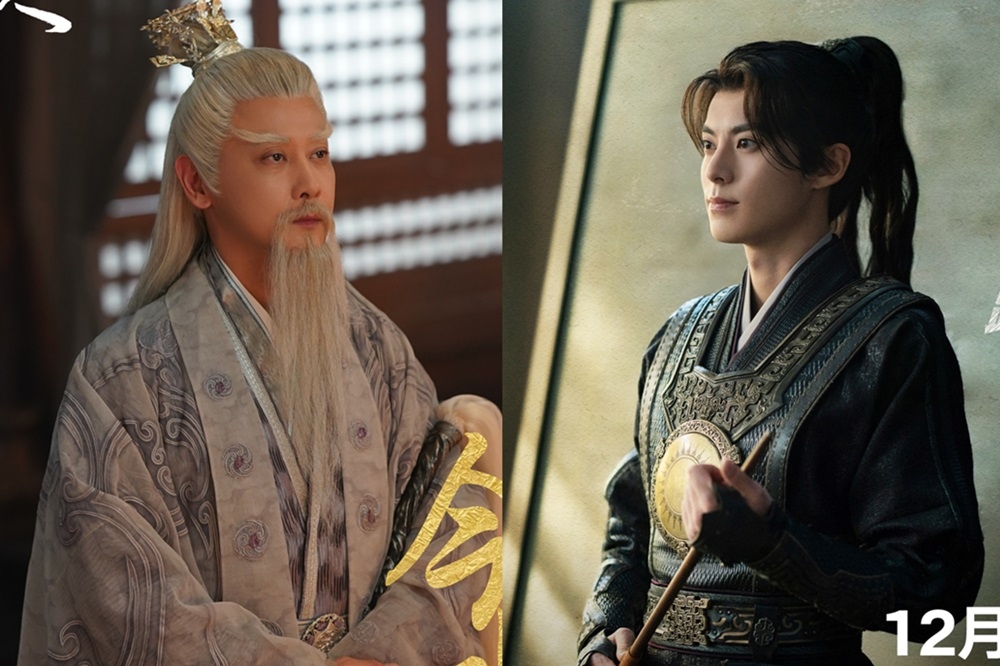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投書:台灣社會對柯文哲案應有的省思 2025-01-03 00:00
- 最新消息 柯文哲4人羈押理由曝光 柯曾說「要與妻孩出國躲紛擾」成關鍵主因 2025-01-02 23:53
- 最新消息 柯文哲再遭羈押 民眾黨籲賴清德「適可而止」 2025-01-02 23:22
- 最新消息 快訊/檢方三度聲押成功 柯文哲等4人裁定羈押禁見 2025-01-02 22:58
- 最新消息 內政部政黨審議會決議通過 聲請統促黨違憲解散 2025-01-02 22:28
- 最新消息 被緊咬是柯文哲分身 李文宗:大家都知道是蔡壁如 2025-01-02 22:12
- 最新消息 諷檢方下不了台「要關我就明講」 柯文哲:再加保就要賣房了 2025-01-02 22:00
- 最新消息 WSJ:中國已非美企「金礦」 難再幫北京說情 2025-01-02 21:50
- 最新消息 強烈冷氣團下周報到 低溫恐跌破10度、高山有望降雪 2025-01-02 21:34
- 最新消息 檢控他可能逃亡海外 沈慶京坐輪椅服藥:快80歲了怎麼跑 2025-01-02 21:08

公視微科幻趨勢劇〈貓的孩子〉雙重結局的安排,令觀眾深思表面和解的虛妄,真正的和解為何物。(圖片擷取自Youtube)
網路流傳一張錯視畫,照片中是日本小學空教室,窗前櫻花如雲、嫣紅盛開的美景。觀眾近看才發現,哪有什麼櫻花,是窗玻璃上滿滿血手印。寂靜空景中,頓時觀眾耳邊充滿了校園屠殺犧牲者設法推窗外逃的尖叫。
另一個例子,是高畑勳動畫片《螢火蟲之墓》海報,年幼兄妹背景是螢火蟲閃閃的夜空,適合兒童觀賞。今年高畑勳死後傳出新聞,把海報圖檔調亮100倍,背景夜空赫然出現了美軍轟炸機,螢火原來是滿天砲火。


公視劇集〈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新一集〈貓的孩子〉也是這樣的錯視畫。表面有一個歷經苦難和解的大團圓故事,底層有一個毛骨悚然的故事。像《螢火蟲之墓》戰後日本在美軍統治下不准說的故事,藏在背景裡30年,死了才能說出口。
平行世界
每個人對自己的人生,都有表、裡兩套版本。隱藏版的故事,自己意識不到,是痛苦的絕望。自己知道的表面故事,是虛假的希望。
〈貓的孩子〉開場,公公壽宴上,二伯炫耀四個兒女,一個進了醫學院,一個拿紐約大學獎學金,一個考上醫師資格,一個上北京大學法律系。小叔叔炫耀女兒讀北一。老三的兒子,應屆大學考生鍾國衍,考班上最後一名,自始早已坐立難安,想往外逃,都被母親擋下。
輪到他被迫交代時,他當眾失禁洩糞。讀北一的表姊,又把洩糞把柄告訴鍾的女同學羅志葳。羅志葳因為躲在垃圾場毒打弱小紓壓,被鍾撞破;所以就在班上罵鍾「大便男」欺負他。羅自恃考滿級分就是王,搶走鍾的便當,摘下壁報欄「滿級分」錦旗來回甩鍾的臉,鍾都不敢反抗,一心只想知道考滿級分的秘訣。
羅志葳由村上春樹小說《1Q84》獲得靈感。小說中,女主角在天上看到並排的黃、綠兩個月亮,意識到自己脫離了現實的「1984年」,踏入了平行世界「1Q84」。女主角得知新興宗教教主連續性侵多位少女,義憤暗殺教主;卻得知性侵其實是通靈儀式。少女是空氣蛹所製造的替身,不是真人。而且是少女硬上教主,教主當時是全身僵硬無法動彈。也就是說,雖然外表是性侵少女,實際是教主被性侵。這種荒謬的合理化,是外人無法想像、也無法理解的。但只要創造出那個平行世界,教主的故事就能成立。
〈貓的孩子〉劇中,羅志葳由此得到啟發,也說垃圾場是平行世界、不是真的,所以打人沒關係:「在現實世界中,我是個乖女孩。在平行世界,我可以為所欲為。」她考滿級分的秘訣,是在平行世界狂揍班上最後一名,就能在現實世界考第一名。《1Q84》的平行世界,是心靈面對無法承受的痛苦時開啟的潛意識空間,血肉活生生撕裂開來、吞沒痛苦。《1Q84》主角天吾這麼定義現實:「一用針刺就會流出鮮血的地方就是現實世界。」其實對被壓迫者來說,現實是挨揍不准痛,刺傷不准流血,只能在幻想中沒有傷口的完好之處偷偷疼痛流血。
表面故事
二伯、小叔的表面故事是「只要兒女高學歷,我就有價值」,隱藏故事是在公公習慣性騷擾家人、毫無感情的家族中,飽受價值感低落之苦。鍾父的表面故事是「我會失敗都是因為學歷不如人,所以兒子學歷要好。兒子考不好,都是因為老婆管不好。我不回家吃飯,都是因為老婆沒把屋頂漏水修好。」無論是漏水或兒子學習障礙,鍾父都透過把持發言權,使解決雙方共同問題的責任,永遠只落在鍾母的頭上。
鍾母面對丈夫外遇,姑嫂踐踏她,公公對她性騷擾,她則向所有人連連道歉。她的表面故事是鍾父表面故事的下集:這全都怪兒子考不好,要是兒子考好了,就不用請家教,錢省下來就可以請好一點的師傅抓漏,這樣鍾父就會回家吃飯了。鍾母拜託家教老師,學鍾父狠狠打兒子,兒子成績就會進步;一停止,成績就會往下掉。
鍾被家教揍到見人顫抖、畏縮,挨罵嘔吐,或當眾失禁,鍾母都視而不見,置身事外。鍾父痛揍兒子時,鍾母則在喧聲中拼命扒飯,假裝不在場。劇情在此揭露了犧牲的體系,不平等體制的穩定性,繫於不斷將風險外包。而外包的技術就是編織統治神話,有話語權的人虛構故事,將個人困境歸罪受害者,代罪羔羊只能是在親密關係中他自認有權踐踏的對象。兄嫂輾壓鍾父,鍾父輾壓鍾母,鍾母虛構故事轉移對自身痛苦的注意力,施行權力,虐待兒子。壓迫的食物鏈,一連串的風險外包,滾雪球相乘相加,落在鍾雙肩上,把他壓垮了。
於是,鍾也創造了表面故事:他有辦法考第一名。只要在平行世界殺一隻貓就可以。
2016年,思覺失調症患者、失業男子王景玉,當街砍殺女童「小燈泡」。王景玉認為自己必須傳宗接代,而要完成必須殺死一個人。
王景玉的父親不讓王就醫,只叫他去買春。女童母親王婉諭表示「我覺得他爸爸沒有好好對待這個孩子……他的朋友曾經要去家裡關心或是打電話,他父親都會斷然拒絕、掛電話,覺得你不需要朋友,所以他跟任何人沒有情感連結」。王婉諭希望理解這一切,「理解才能夠真正修復」,但因王景玉父親一直否認兒子生病而告終。
王景玉的表面故事「我必須傳宗接代,而要完成必須殺死一個人」,和王父的表面故事「我兒子沒病,只要花錢打個砲就會好」,也就是平行世界,具有重要的功能:幫助當事人解決重大生存壓力,透過否認現實,允許他們活下來。因為當他們需要別人允許他們活著、否則無法活下來時,周圍沒有人為他們做這件事。
鍾的雙重人格
回顧〈貓的孩子〉劇中安排的幾個問題,首先,鍾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殺了貓?
表面上,殺貓對鍾純屬實用,理性客觀中立,對貓沒有個人恩怨,只是鍾考滿級分的巫術道具。法國人類學者李維史陀研究原始思維的巫術行為,譬如聽見鳥鳴而獵到野豬,雖是意外,原始部落居民卻會建構因果關係,循此在狩獵前製造鳥鳴、以祈求第二次獵到野豬。
換到劇中,鳥鳴就是殺貓,獵到野豬就是考滿級分。初看,第一次毒死貓,原本只是鍾忘了頂樓曾投放滅鼠藥、過失致死。但因為鍾母啼哭之餘,遷怒鍾故意毒死貓,又說「算了只要你考高分就無所謂」,反而令鍾創造出殺貓和考好的因果關係,進而第二次主動毒殺野貓。責任可歸於鍾母。
然而,該劇不是如此。劇情強調鍾燈下苦讀,嫌貓太吵,要鍾母把貓移到頂樓;隨後鍾又立刻遺忘自己有此一舉,被問起仍渾不知情。殺貓的結果,也是鍾母這麼說了,鍾才恍然大悟毒藥和貓死的關連。鬼影幢幢,就像是小說《化身博士》,一人身上有雙重角色:平日是善良的傑基爾紳士,有時會喚出邪惡的海德博士。劇情暗示,鍾潛意識中早已有個海德博士在暗中操盤,布置了種種意外因素匯聚到位,還加上不在場證明。責任應歸於鍾。
多數時候,觀眾從鍾身上看到的,都是善良的傑基爾紳士。殺貓只為考好、滿足媽媽的期望。那麼海德博士想要什麼?
海德博士想要貓。只要遇到貓,他就會住手消失。貓是母子人格切換的重要按鈕,牠到底象徵什麼?
大家都有雙重人格
為了回答這問題,必須探討另一條線索:鍾的自殺和殺人,都因遇貓而中止。這有什麼用意呢?
先是自殺:起初鍾絕望到在家跳樓自殺,被抓漏師傅拉住阻止。此時鍾身受情緒衝擊,應該久久難以平復。但劇情卻安排鍾明察秋毫,聽見師傅沒聽見的貓叫,循聲撲過去找到棄貓,抱貓露出燦笑。觀眾困惑了:不是剛才還在自殺,想死是開玩笑的嗎?
再是殺人:結尾鍾向鍾母討抱,鍾母卻冷漠拒絕。屢次受挫的鍾,憤而死命勒住鍾母頸子,不顧鍾母掙扎,但卻因幼貓誕生的叫聲打斷而鬆手。兩人不但一起正能量關注家貓生產,鍾還乖乖聽鍾母命令去拿毛巾幫忙。原本冷漠的鍾母,差點被殺,卻毫不驚訝,不動氣也不害怕。反而變得滿臉慈悲,一切她都寬諒。憤怒的鍾,則轉為內疚求和。母子相擁而泣。
自殺和殺人的情節,一遇貓就在輔導級界線前緊急煞車,這貓簡直就是NCC。情緒轉換乍看突兀,但這是因為劇中每個要角都有表裡兩種狀態,突兀,是為了強調前後斷裂不連續的反差,凸顯出貓這個轉捩點的意義重大。
鍾母有兩個。每當面對鍾,鍾母就是啼哭勒索的巨嬰,哭叫著怪他不考好,答錯要打。而每當面對家中貓咪,鍾母則溫柔善良、悉心疼愛。
羅有兩個。羅原本嬉笑黏人;但鍾邀請羅「一起讀書吧」,像催眠暗示一扣扳機,猝然喚醒羅在平行世界的狂戰士狀態,凶性大發,揮拳追打鍾。
鍾有兩個。原本鍾受虐畏縮、向來任人欺負不還手。但羅指點鍾:「只要看到藍色月亮,就能看到另一個自己。」鍾的另一人格,表現於藍色月光下,鍾赤膊站在壁癌天花板下床角、困惑迷惘的鏡頭;和黑暗中鍾扭曲狂笑的臉部特寫。由此成為一個殺貓凶手。
表面的和解
最後,由殺貓而實際動手弒母,鍾由爆發衝突得到宣洩。接著母子相擁而泣雨過天青,一切回歸正軌,寧靜幸福。
這是真的嗎?
當然不是。第二個結局,翻案戳破了第一個結局。第二個結局,從市區店面工地宣布一小時午休,突然跳接到山區湖畔吃便當,觀眾無法分辨這幕戲是幻想或真實。鍾國衍躺在湖畔讀聖經,沒頭沒腦地問猛嗑便當的羅志葳:「如果你是耶穌,我殺了你,那你要怎樣才能原諒我?」羅問:「我是神?」「不是神,是神的兒子。」於是羅回答:「我要你懺悔自己的愚蠢,然後乞求我的原諒。」
他繼續問:「如果你是貓呢?」
這問答乍看很謎,點出劇名「貓的孩子」:兒子壓抑對母親的恨意,表面上殺貓是想考滿級分,其實是弒母。對母親的恨,轉移到貓身上宣洩。
改編的原作〈人子與貓的孩子〉中,家教慨嘆,家貓不需要考試,所以鍾母能放心溫柔疼愛貓,反而無法疼愛她懷胎十月生下的兒子。原文「人子」並沒有宗教意涵。但因為聖經中「人子」專指耶穌,因此劇情突然搬出聖經,鋪墊鍾這一問。那麼鍾問耶穌時,要問的到底是什麼?
前頭鍾為弒母而道歉後,鍾母回答:「我們可不可以先學會一件事,不要一直說對不起。」這句貌似原諒的膺品,再度把自己做不到的理想,丟到兒子身上。鍾道歉了,但鍾母沒有道歉也沒有認錯,日後繼續替兒子做便當就是道歉了。這就是向田邦子散文〈父親的道歉信〉描述的間接道歉。父母道歉之所以間接,是因為在他們所處的社會規範中,上層階級不需要向下層道歉;上層無論對下層做什麼,都是對的。對加害者而言,道歉?道什麼歉呀多此一舉,是受害者該放下吧,過去的事讓它過去吧。但轉型正義要求,屠殺之後,單單補償受害者是不夠的;必須揪出加害者,揭明其傷害,宣告這種事不能再發生。
劇情苦於無法讓鍾明說,只能拿出聖經虛晃一招,假裝問耶穌。觀眾領悟,實際鍾要問的是自殺:「媽媽,你殺了我,我要怎樣才能原諒你?」這個問題是指認凶手。
羅回答:「我要你懺悔自己的愚蠢,然後乞求我的原諒。」這是要凶手鍾母承認其傷害,宣告這種事不能再發生。
真正的和解
為什麼該劇無法明說之餘,要把控訴質問藏得這麼深?似乎該劇也成為劇中受困的角色之一,需要一個表面故事撐腰,才能見容於世。
劇中著重刻劃鍾內心渴望和解的部分,也就是兒女再怎麼受虐、仍然期待父母能愛他們。這在劇中,以「擁抱」來表現。鍾對擁抱有兩種反應。
一是對羅的害怕:
起初在學校,鍾要羅說出滿級分秘訣,羅提出以「你抱我」作為交易。但鍾不情不願、虛應故事,羅索性自己狠狠抱緊了鍾。鍾顯得驚慌、厭惡,抵抗掙脫。
一是對鍾母的渴望:
劇情中段,在家中,鍾一直渴望母親的擁抱而不得,趁鍾母睡著後,摸黑上床偷偷抱著她睡覺。
然後,結尾的和解,表現於鍾為弒母而道歉後,鍾母伸手一抹鍾臉頰的淚痕,表示原諒之意。
其後,鍾、羅湖畔問答後,情景跳回鍾、羅先前在學校互毆成傷,在此透過一系列精彩的動作,回應了前三段情節。夕暮金光中,鍾含笑主動攬過羅的肩膀,親密同行。比較鍾先前掙脫羅的擁抱、上床偷抱鍾母,此時,原本鍾「害怕」擁抱的羅,在意義上轉變成鍾「渴望」擁抱的鍾母。
而羅的反應,則是從原本擺臭臉,逐漸放鬆舒緩,然後伸手一抹鍾臉頰的傷痕,重現了先前鍾母替鍾抹淚的動作。說明這是一段幻想性的描寫,透過鍾的擁抱、羅的抹臉,互相確認羅已不是羅,而成為鍾母,用來說明鍾理想中的真正和解。
鍾母無法放下身段道歉,透過羅主張鍾的權利,這才產生了隱藏版、真正的母子和解。若鍾母不認錯,就沒有鍾的原諒。所以和解存在於渺茫的期待之中,虛空之中,從未發生。只要鍾還心存期待一天,就一天無法脫離鍾母的掌控。
轉移
這個結局同時說明了,鍾母在鍾心目中已經一分為二,分裂為溫柔疼愛的好媽媽、和瘋狂體罰的壞媽媽,並把這標籤貼到其他人身上。貓象徵好媽媽,羅象徵壞媽媽。鍾看不見鍾母的壞,也無法逃跑或反抗鍾母;但換成羅向鍾施暴,鍾就瞬間逃跑、反抗,甚至海德博士上身,拎磚砸頭、把羅往死裡打。鍾對鍾母的憤怒,經過潛伏壓抑後、不自覺加倍傾瀉在羅身上。而另一方面,鍾母的暴怒令鍾無法親近;但鍾母只要有貓就能解除焦慮,變得溫柔可親。此時在鍾母眼中,鍾也就不再那麼一無是處,而暫時變成好兒子。甚至在貓發揮安撫鍾母的作用之前,劇情就已經安排貓的出現打斷了鍾的自殺衝動。此時貓就是愛,是允許鍾可以去愛的鍾母。這就是轉移。
回答先前的提問:「貓代表什麼?」像同系列〈媽媽的遙控器〉中,遙控器作為故事中控制主角的裝置;貓是母愛「on/off」的按鈕。羅是打開鍾暴力的按鈕,羅從出場以來的每句話,都在替鍾的殺貓鋪梗做球。貓是打開鍾的愛的按鈕,只要遇到貓叫求助,鍾的自殺、殺人就會中止。劇情就在按鈕之間迅速切換。
和解,則意謂著取消按鈕。無論好媽媽、壞媽媽,都重新融為一體,重新被認知和接納。所以劇集也好,現實也好,保守派若想靠強調「好媽媽」「有愛」的一面來為鍾母說情,試圖和解;這就低估了事態的嚴重,不但無法和解,還只會越陷越深。
劇中,鍾母撞破鍾國衍因為殺貓被捕,鍾因此崩潰,當街質問鍾母「你愛不愛我」。但我認為,這句疑問,可能是經治療多年,甚至中年以後,當事人才有辦法面對的。孩子當時問不出口,再怎麼受虐也想不到「媽媽不愛我」,表面故事就是為了遮蔽不被愛的痛苦而產生。如果環境能支持孩子自主發言對抗權威,那也不至於演變成大病了。鍾殺貓對自己的意義是什麼,鍾當時也不可能知道。劇情對兒女的韌性過於樂觀,和對父母「教化可能」的悲觀,可說互為表裡。
第一個結局「由爆發衝突得到宣洩」進而和解的傳統家庭劇公式,顯然不適用於比「歡喜冤家床頭吵床尾和」更嚴重的問題。第二個結局攻擊了第一個結局的傳統弊端:在過短的篇幅內、作出缺乏說服力的和解,等於被迫過早和解,揠苗助長。和解是眾人想要的,但加害者沒反省,就要求受害者原諒,這種和解只是壓迫當事人否認問題。強迫轉念,強迫和解,對探索病情毫無幫助。若要依靠這種和解,那麼我以為,結尾弒母只是母子無數次大小衝突中的一次,這次不成,還有下次。
〈貓的孩子〉雙重結局的安排,令觀眾深思表面和解的虛妄,真正的和解為何物。以及,如果一談到親子衝突,我們就非談和解不可,那為什麼我們非談和解不可?顯然是因為,在現實中,強迫和解的壓力極其普遍。我們身處的環境早已設定議題,逼受虐孩子必須原諒父母,並且還須求父母原諒。強迫和解,就是壓迫的幫凶。
更有甚者,有些保守派無法分辨「普通的親子爭執」和「嚴重的殘害兒女」有何差別。面對外界的親子衝突,一概劃歸為普通爭執,或視為必要的施壓、導正,盲目捍衛,指責這些受虐兒女「什麼事都要怪父母」。有些人由於看不見自己的受虐經驗,所以他們不知道親密和虐待的界線何在。要求快速即時的和解,正是把普通者與嚴重者混為一談。這種混淆,動機或許並非有意,但就結果則是大罪,因為它成功否認了問題存在。轉型正義,正是為了對抗混淆而生。
該劇既須想像有說服力的和解,但現實沉痾之深,又無法滿足和解的要件,所以該劇作出了前衛的嘗試。即使虛構的作品,也無從在經驗上撒謊而不被觀眾識破。如果我們未曾用身體去經驗過真正的和解是怎樣來的,是什麼狀況,那我們就無從想像原諒與和解。此時不該去憑空捏造,〈貓的孩子〉放棄正面描述未知的和解,而僅僅提出暫定的親子談判框架。只給予最初的少數骨架,而不假裝知道它完成時的全貌為何。那麼,觀眾就必須繼續哲學性地探索自己。
必須推翻孝道
像〈貓的孩子〉這樣「母親犧牲兒子來滿足父親」的故事,東西方都有。歐洲的鵝媽媽童謠中有一則,敘述樵夫喪妻再娶,後母偷偷砍了亡妻女兒的頭,把肉熬湯給丈夫喝。弟妹把骨頭埋在樹下,就有一隻金鳥飛來樹上,每天唱三遍「我的媽媽殺了我,我的爸爸在吃我,兄弟姊妹坐在餐桌底撿起我的骨頭,埋了在冰冷的石頭下」。於是樵夫派後母搬梯子去抓金鳥,結果樹倒了把後母壓死。
順帶一提,童話中的邪惡後母,通常在原始版本中,就是生母本人。
張愛玲的小說《半生緣》,描述姐姐曼璐做娼妓養活全家,婚後她認為留住丈夫祝鴻才的唯一方法,就是犧牲妹妹曼楨,把妹妹騙來,讓祝打暈了性侵,囚禁,逼嫁。原因是曼璐自己已經不能生育,而外面找的女人一定沒有曼楨好掌控,因為畢竟是自己的妹妹,所以要利用妹妹來吊住丈夫的心。等於〈貓的孩子〉妻子利用兒子吊住丈夫的心。
張愛玲〈沉香屑第一爐香〉講姑母梁太太犧牲讀中學的姪女葛薇龍來吊住恩客,〈連環套〉則是母親霓喜犧牲女兒來吊住飯票。這些都是舊時代犧牲者按在教室窗上的滿滿血手印。如果讀者習以為常,視為特殊個案看待,表示我們並沒有脫離那個拿孝順吃人的時代,仍然視兒女為父母的私人財產。在那個時代,多數人認可賣女兒養家,多數人認可〈金鎖記〉曹七巧對兒女婚姻極端的控制,也認可溺女嬰、販奴。這種孝順,狹義是奉養義務,廣義是一張空白支票,隨便父母填上任何莫名其妙的要求,諸如「我媽說女生可以生孩子的時候不生就是不孝」、「不拼生男就是不孝」、「兒女搬出去住就是不孝」,總之「不聽我的話就是不孝」,父母成為不受限制的最高道德制定和仲裁者,不問是非、無限上綱,要兒女犧牲自主來埋單。孝順吃人的時代,和人權的時代,勢不兩立,其間轉換需要社會價值上的劇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系列,為啟蒙工程作出了輝煌偉烈的貢獻,〈貓的孩子〉更是如此。
結語
《1Q84》中,天吾說:「很多事物已經開始在同步變化了。這是我所感覺到的。有幾種已經變形了。可能沒那麼簡單變回原來的樣子。」
編輯小松問:「如果那牽涉到我們無可替代的生命也一樣嗎?」
在原作〈人子與貓的孩子〉中,動手痛毆鍾的不是鍾父,而是鍾母本人,她也沒有內疚跡象。劇集改為陳述鍾母的苦衷,並把她虐打兒子的情節,改成由鍾父動手,把鍾母演成像兒童般天真可憐、無助啼哭,可說盡力柔焦美化,一心向善創造了沒有壞人的世界。原著中的兒子,則是個被輾碎的犧牲者,無法反抗,沒想過殺貓。一般精神官能症或心理病患,都像原著主角,苦惱,不知適從,表現笨拙,自殘、自殺為多,離暴力傷人很遙遠。〈貓的孩子〉毅然挑戰了主角走向暴力的少數可能,勇闖禁區令人佩服。然而正因為貓/愛作為按鈕,兒女無論如何受虐,總還期待得到父母的愛,總是對父母暴力視而不見,而把施暴對象轉到其他人身上。或許鍾國衍成為王景玉,才是旁人自掃門前雪順其自然的正常結果吧。現實中,像虐貓、像小燈泡這樣的殘酷犧牲,很多時候,可能只是父母施虐槓桿,間接產生的代罪羔羊。
我們無可替代的生命。
《1Q84》接著寫道:
天吾曖昧地搖搖頭。他感覺到自己不知什麼時候已經開始被捲進一股強大而一貫的洪流中了。那流水正要把他沖向一個陌生的地方。但卻無法對小松具體說明。
※作者為作家
延伸閱讀
●捷運老鼠之亂:假警報 真驗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