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不斷更新/【世棒四強賽】「中華隊 vs 美國」陳傑憲再發威 中華隊1局上攻佔1、3壘 2024-11-22 11:03
- 最新消息 西方國家官員表示 北韓高階將領首度在俄國庫斯克地區遭攻擊受傷 2024-11-22 11:00
- 最新消息 全聯隔日達改名「全電商」!每周六日一最高回饋 12.5% 黑五同步登場、爆殺品下殺 26 折 2024-11-22 11:00
- 最新消息 《珠簾玉幕》劉宇寧、唐曉天為趙露思爭風吃醋 兩人鬥嘴不斷「這場面」超爆笑 2024-11-22 10:42
- 最新消息 快訊/賴清德再為「勞動部霸凌案」道歉 承諾嚴查嚴辦、檢討法令 2024-11-22 10:41
- 最新消息 黃牛1帶3?Ado 五月林口體育館演唱會今全面啟售,一進「只剩輪椅區」引粉絲不滿 2024-11-22 10:21
- 最新消息 勞動部輕生員工有「2份遺書」 曝工作壓力很大、未點名謝宜容 2024-11-22 10:17
- 最新消息 賴清德就任總統後首度出訪 將訪南太平洋3友邦 2024-11-22 10:10
- 最新消息 衛星畫面顯示 北韓以軍火、作戰人員換取大量俄國原油 2024-11-22 10:03
- 最新消息 直播/賴清德就任後首度出訪 總統府10:00記者會 2024-11-22 10:02
張思之就是民國少年的典範,一個永遠的民國少年,新的民國在哪裡?在他九十年的生命中。(維基百科)
我生也晚,當我少年時,思之先生享盛名已久矣, 1980年他為林彪、「四人幫」政治集團案出庭辯護,在央視新聞節目出現時,真是光彩照人,那時他才年過半百,自五七之災以來,浪擲了二十餘年寶貴歲月,一旦重登律壇,即不同凡響,可惜其時14英寸的黑白電視都還是奢侈品,我家鄉的山村中一台也沒有,我在雁蕩中學求學,也未見過哪個老師家有電視,直到多年後才在紀錄片鏡頭和老照片中見到。
第一次記住了先生的姓名要等到1991年初春,我那時囚禁在溫州黃龍山,在被窩中偷聽短波收音機,外電連續報導八九「黑手」王軍濤、陳子明案開審情況,他和孫雅臣是王軍濤的辯護律師,好像還有對他的介紹,他們對王軍濤做了無罪辯護。特別是當年冬天,從收音機中聽到王在獄中寫給他們的信,信中請他們諒解自己在法庭上為八九大潮中不該由他負責的事情和觀點辯護,給他們的辯護所造成的不利。並請兩位律師安慰他的妻子。這封信我曾無數次感動過我的心靈,我視之為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文獻。思之先生作為第一收信人,我從此便牢牢記住了他。以後,我留意他的消息,他為鮑彤、為魏京生、為高瑜、為楊子立等當局眼中的異端辯護,每一次都以敗訴告終,他卻屹立在法庭上,以白髮滿頭的形象贏得了舉世尊敬。
2001年,《脊樑:三代自由知識份子評傳》在香港問世,其中有一篇寫到自1999年以來,思之先生和戴煌先生等一起關注河南被冤殺的農民曹海鑫案,出版人金鐘先生大概給他們都寄了樣書。2003年初春,在北京的一個飯店,《中學人文讀本》座談會上才第一次遇見他,他的《我的辯詞與夢想》序言被我們選入了這套讀物,當天邀請與會的老先生除了他,還有戴煌先生、何家棟先生、梁從誡先生、藍英年先生、邵燕祥先生等,中年的有徐友漁先生、雷頤先生、丁東先生、謝泳先生等,如今何、梁、戴諸先生都已離開我們了。
中餐時,我和張先生、戴先生在一張飯桌上,他們對我的友好與熱情,讓我心存感念。我不好意思地向思之先生提問,臺灣出版的《我的辯詞與夢想》還能找到否?他當即答應,給我一本。書在海峽對岸出版,帶進來太不容易了,我其實並沒有抱太大的希望。時間長了,也就淡忘了。先生卻放在了心上,我估計當時他手頭沒有書,是托人想辦法帶來的,當年11月17日我收到沉甸甸927頁的大書《我的辯詞與夢想》,先生在扉頁寫著:「資料一冊,國湧雅正 張思之 2003、初冬,北京」。這是我手中最珍貴的簽名本之一。先生之謙和、幽默,不是一種表演,而是其生命的自然流露,是一位飽經時代風雨剝蝕的民國少年,向這個世代呈現的精神底色。
「十萬青年十萬軍」
是的,他是一位典型民國少年,1927年他生時正是北洋政府向國民政府更替之際,他的小學、中學、大學,在不安和動盪的亂世中度過,他之所以成為左翼青年,加入中共地下黨的週邊組織,是那個時代造成的。遙想當年,他在四川三台國立十八中,傅庚生老師的國文課曾經那樣深深地吸引過他,半個多世紀後,他都還能複述老師在講臺上的神情、動作、講述的細節。更早,他在綿陽國立六中的初中部,遇見了啟蒙老師王資愚先生,李煜、東坡、辛棄疾的詞,白居易的詩,漢魏六朝到清代袁枚的名篇都深深地植入了他少年的記憶。
「十萬青年十萬軍」,即使投筆從軍,踏上前往印緬戰區的行旅,少年思之的行囊中還帶著《宋詞選》、《魯迅雜感集》、《英漢辭典》。十六歲的娃娃兵,一生喜歡宋詞元曲的民國少年,在他身上我看到的不是左右意識形態紛爭帶來的創傷,而是古典中國、綿延不絕的中國文化在他生命中種下的基因,1949年的時代劇變逆轉了一切,卻改變不了一個民國少年的底色,他如此,1920年出生的許良英、1921年出生的李慎之如此,1928年出生的戴煌、1931年出生的資中筠、1933年出生的藍英年,以及1936年出生的方勵之都是如此,這些民國少年,一生的大半時光都處在清一色的紅色時代,但多姿多彩的民國已奠定了他們的人生根基,民國的講臺呈現給他們的不僅是知識的天寬地闊,更重要的是心靈的自由翱遊,他們有幸在中西文明偉大相遇的時代,被建造成人,以平常心做平常人,卻成就了非常事。
他們是學者、律師、作家、翻譯家、物理學家,更是人子。要真正理解思之先生,只有將他放置在他經歷的這個波濤起伏、風雲詭譎的苦難時代中,1927到2016年的中國,以及共產主義運動興衰變易的大背景中,同時將他放在同時代人的行列中,也放在百年中國律師的傳統中。
他是一位律師,上承民國律師之余緒,下啟掙扎、糾結、千回百轉的轉型時代律師何為的追問,在當下中國二十萬職業律師中,他是一個異數,也未必能得到多數人的認同,但他的影響早已溢出律師界,在律師圈外凡知他者幾乎對他一致心存敬意。他身上隨意釋放出的生命能量,與他接近者感受到的他身上的那種精神氣質,其實不是律師職業生涯所賦予他的,而是民國的教育賦予他的,這位民國少年終其一生都保持著閱讀的習慣,對古典文學心存溫情的敬意。他的辯詞之典雅和莊重即包含了少年時的文學陶冶,同時又有一生滄桑陶鑄出的那種厚重和銳利,當然還有對法的精神之尊重和追求。
看見「將來的現在」
他的辯詞是從「過去的現在」淘洗出來的,是洗盡鉛華之後的凝練與壯美,雖然他總是說自己無能、軟弱,為王軍濤做無罪辯護的辯詞洋洋近七千言是撇腳的,因為此案卷宗21冊,2900多頁,只給了律師三天閱卷時代,經請示也只延長了兩天,五天下來,最後還是沒有看完。他為此而深感遺憾和慚愧。
他的辯詞文本毫無疑問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也許放眼整個人類文明史,他的辯詞還不足以成為傳世之楷模,但作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一名律師,他做到了極致。他真實地呈現了自己的職業水準、道義良心,同時顯示了漢語在此一時代的尊嚴。他的文本由此可以列在《古文觀止》之後的漢語文本序列中,與王軍濤的那封信一起,選入未來中國的母語教科書中。
站在「現在的現在」,我看見的是「將來的現在」,思之先生的夢想指向的就是將來一個每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得到尊重的時代,是漢語重新找回尊嚴的時代。一位民國少年,不喜歡說大話、空話,但不意味著他沒有夢想。在古老帝國夢的盡頭,民國曾經破土而出,不幸被黨國替代。他的夢想也可以視為回到一個真正民國的夢想,那是所有國民自己當自己的主人的民國。如果這是先生的夢想,那也是我的夢想。
遠遠的東方 太陽正在升起
十三年來我有幸蒙先生厚愛,給予我極大的幫助和鼓勵,2011年,在中國引入律師制度百年之時,他為我編的小冊子《追尋律師的傳統》寫下了美好的序言,更早在2005年他毫不猶豫應允為我的《過去的中學》執筆回憶他的中學生涯,寫下了令人感動的《綿綿師恩誰寄?》。幾年後,他獲得德國伯爾基金會授予的佩特拉•凱利2008年度獎章,在他的書面受獎演說詞最後,我驚喜地讀到了這樣的表述:
我不敢低估前路的障礙阻力,但即使艱險環生,也絕不因此而萌生絕望。絕望與希望之間有時也只是一步之遙;…展望前程,無由悲觀。關鍵在於恒守信念,學習不輟。我誓以夕陽西垂之軀,迎晶瑩晨露輝映人間明媚春綠。…「遠遠的,東方,太陽正在升起。」
他從夕陽想到了日出,精美的演講詞背後,我讀出的卻是別一番風光。最後的一句引文,旁人也許不會留意,唯有我看到了才明白,那是我編的《過去的中學》中講述了重慶南開中學,有位學生在作文開頭寫了一句話:「遠遠的東方,太陽正在升起。」在清華大學國文系師從俞平伯的陶光在「遠遠的」後面加了一個逗號,成了:「遠遠的,東方,太陽正在升起。」由此贏得了「一點師」的美譽。
《過去的中學》初版於2006年問世,沒想到,年近八旬的思之先生收到樣書,竟然認真讀了,幾年以後還活學活用,寫在了演講詞的最後。我恍然體悟,「恒守信念,學習不輟」對於他不是大言大詞,而是身體力行,終身踐行的座右銘。即使九十歲了,他還是在川中聽王老師、傅老師講課,在駝峰航線上帶著《宋詞選》的那位民國少年啊。我想起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中國強,…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在我心目中,思之先生就是民國少年的典範,一個永遠的民國少年,新的民國在哪裡?在他九十年的生命中。
2016年9月15日中秋節,颱風襲擊臺灣、廈門,江南正在風雨之中,匆匆完稿於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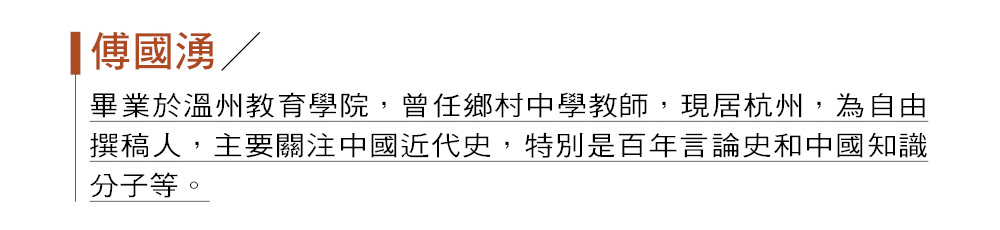
【上報徵稿】
上報歡迎各界投書,來稿請寄至editor@upmedia.mg,並請附上真實姓名、聯絡方式與職業身份簡介。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起底謝宜容!傳身家背景雄厚「善做公關」 先生和綠營高層有交情
- 一元特典!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釋出「零星票券」,11/24 採實名制一般販售
- 【世界棒球12強賽】滿足「2條件」台灣確定晉級4強 今晚是關鍵
- 先搶先贏!Ado 五月林口體育館演唱會採實名制入場,11/19 輸入「指定代碼」可優先預購
- 【內幕】T112步槍裝彈器採購案疑專利侵權 以色列向軍備局寄存證信函
- 王一博金雞獎典禮被抓包視線離不開趙麗穎 網揭兩人4年戀情無法曝光背後真相
- 勞動部涉職場霸凌不只謝宜容? 何佩珊:與輕生者中間還有2個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