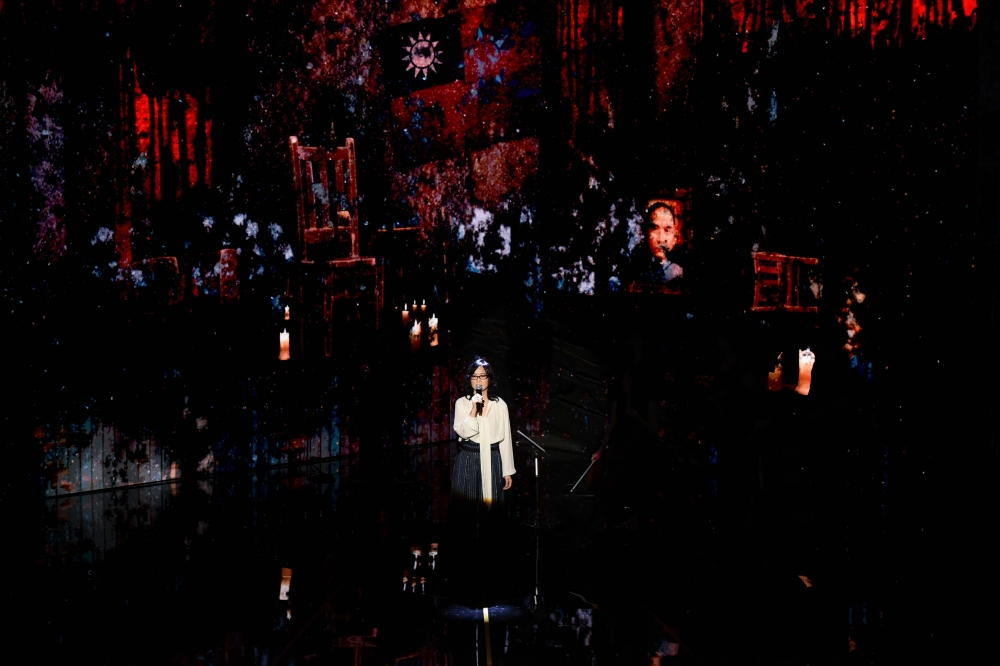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出訪期間逢韓半島變局 賴清德深夜召集國安幕僚關注情勢 2024-12-04 22:59
- 最新消息 瓊瑤發文時間藏「愛的暗語」 張曼娟曝:「22」是平鑫濤最喜歡的數字 2024-12-04 22:00
- 最新消息 美國駐日太空軍正式成軍 強化美日聯盟對太空活動監控與因應能力 2024-12-04 21:56
- 最新消息 南韓市場價值長期遭國際投資人壓低 路透:戒嚴事件成為有力實證 2024-12-04 21:06
- 最新消息 【子宮大戰】朝野明審《人工生殖法》 綠委炸鍋讓衛福部孕母政策急轉彎 2024-12-04 21:00
- 最新消息 瓊瑤、劉家昌相繼辭世 韓國瑜愴然與不捨如潮水般湧來 2024-12-04 20:53
- 最新消息 反外送平台併購案 外送員集結公平會鳴汽笛1分鐘抗議 2024-12-04 20:51
- 最新消息 台北聖誕、跨年餐廳推薦!韓式燒肉店「Meat Love」推 2 款期間限定套餐 每人最低 970 元起、鮮蝦櫛瓜煎餅必吃 2024-12-04 20:30
- 最新消息 賴清德出訪友邦 台灣助吐瓦魯學校「班班有冷氣」 2024-12-04 20:15
- 最新消息 瓊瑤離世!檢方相驗「無他殺嫌疑」 遺體發還家屬 2024-12-04 20:03

多數人對核廢料這種「己之不欲、施加予人」心裡有數,只是選擇不看不聽不談,希望能減少這種身為加害者的罪惡。(本報資料照片)
1980年,時任蘭嶼鄉代會主席的董森永在當時的《中央日報》上看到一則報導,核廢料將貯存在蘭嶼。他看不懂什麼是「核廢料」,還以為這是「肥料」可以拿來用在自己的農作物,認為這樣很好。一直到當時的台灣省議會到蘭嶼參訪,同行的黨外省議員蘇洪月嬌告訴他:「那是有污染的,有放射性的,不太好。」他其實根本聽不懂什麼叫「放射性」,就只好開始一路問、一路追………
蘭嶼的達悟族人後來收到原子能委員會的答覆公文,大致陳述了四個讓核廢料放在蘭嶼的理由。一是交通,運輸方便,不影響環境衛生;二是蘭嶼貯存場距離部落五公里以上,不會影響居民的安全;三是核廢料將來要投海,只是暫時貯存在這個地方;四是達悟族只有二千多人而已,可以稍微犧牲,不然的話就把他們遷移到台灣,這很好辦的事情。就這樣,這批低階核廢料在蘭嶼放了快40年了。
日前,所謂「以核養綠」的公投提案人黃士修在公投辯論場上提到這批蘭嶼核廢,他說,核廢對蘭嶼最大的影響是讓蘭嶼人有免費充足的電力以及醫療與教育資源補助;他並且以「鋼彈模型」來類比「低階核廢料」,說蘭嶼人可以抗議「鋼彈模型」是外來文化而讓它遷出,但不能說是鋼彈模型讓蘭嶼人得癌症。黃士修說,不少反核人士把回饋金視為政府用威權逼迫蘭嶼人接受核廢料,但事實上是「放了一批無害不會影響生活的核廢料」,主人合理收取租金並補助當地的建設、醫療及教育,「難道蘭嶼人沒有資格好好過現代人的生活嗎?」
對照董森永等達悟人在40年前連「核廢料」與「肥料」都分不清,導致核廢得以長驅直入蘭嶼,黃士修的說法正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他把蘭嶼核廢比喻做「鋼彈模型」,意思在它無害;在他眼裡,台電到蘭嶼「租地」,蘭嶼因此「收租」改善生活,這是銀貨兩訖的「雙贏」。
但蘭嶼的低階核廢料無害嗎?那為什麼要千里迢迢地從台灣跨海運到蘭嶼,還特別向達悟人強調貯存場離部落五公里不會有事?核廢讓蘭嶼人有免費的電力與與公共醫療可以使用是一大恩賜?那這位黃先生願不願認領兩桶核廢回家珍藏,讓政府可免他家全年電費與健保費?就算他肯,黃先生家周圍五公里半徑外的鄰居肯嗎?
國民政府在40年前擇定蘭嶼作為核廢貯存場的理由其實不難理解,因為它孤懸於台灣本島之外,可以降低台灣人對使用核電的疑慮;其次,蘭嶼達悟族人少,無論就實際的反抗或選票的考量,兩者都不足為慮。在台灣的用電需求下,蘭嶼作為核廢貯存場就成為一種「必要之惡」、一個「被犧牲的存在」。
日本福島核災後,出生日本福島的東京大學教授高橋哲哉不斷反思核災為何會發生?他反問:「為何讓自己故鄉福島人們去背負如此重大的風險,自己卻在東京悠哉享受福島核電廠所供給之電力?」甚而在核災發生了之後,許多人對被迫移居的福島人,以及來自福島的食物充滿疑慮甚至嫌惡。高橋因此寫下《犧牲的體系》一書,認為核電本身就是一個沒有犧牲就無法運作的體系。福島電廠既為了供應東京都的電力而存在,在發展東京的視角上,福島就成為一個犧牲的體系。
為了發展,台灣又何嘗不是拿蘭嶼、金山、石門、貢寮作為一個犧牲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下,核災的可能性被貶抑到「小到可以忽略」(別忘了當初東京電力公司就是用一模一樣的說詞洗腦福島人),但經濟發展與核廢彼此相生相映,所以成為許多人的「必要之惡」,並以此說法來遮掩政府的無能猥瑣以及自己的良心不安。
其實,多數人對這種「己之不欲、施加予人」心裡有數,只是選擇不看不聽不談,希望能減少這種身為加害者的罪惡。只是令人想不到,居然還有人指鹿為馬暗諷蘭嶼人就只是要回饋金;而已經把核廢塞到人家裡40年了,還能臉不紅氣不喘地宣稱「難道蘭嶼人沒有資格好好過現代人的生活嗎?」
「以核養綠」把別人的犠牲視作理所當然,這種掩不住的歧視,才是核電支持者永遠跨不過去的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