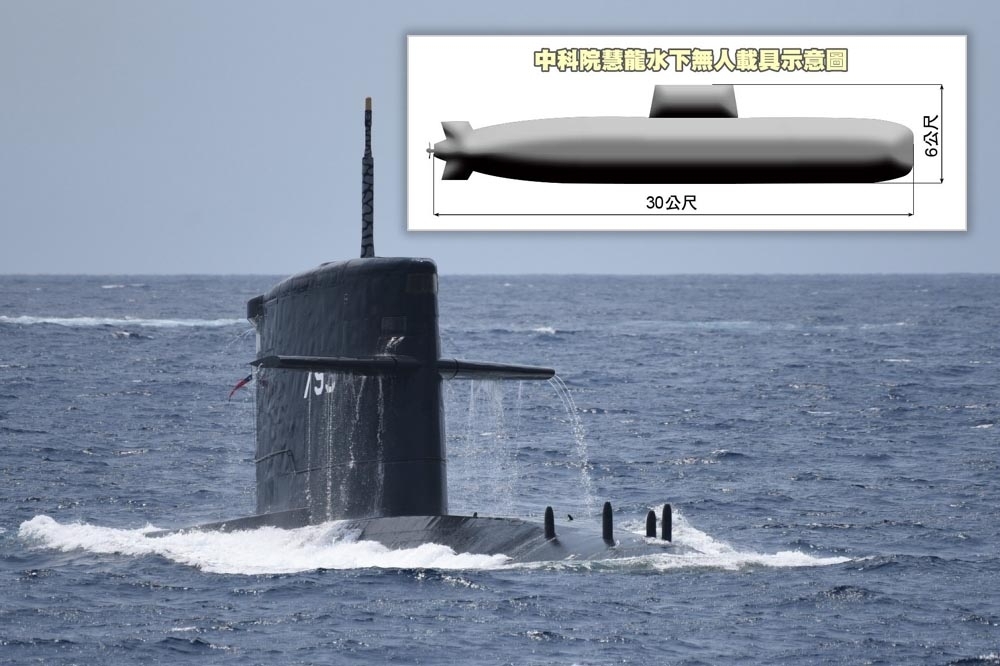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柯文哲續領政黨補助還有正當性嗎 2024-10-31 07:00
- 最新消息 江雅綺:外送平台監管 倒洗澡水別把嬰兒也倒掉了 2024-10-31 07:00
- 最新消息 全台唯一一場!全球甜點傳奇大師「和泉光一」攜手台南遠東香格里拉推出「大師面對面」限量午茶見面會 2024-10-31 07:00
- 最新消息 【康芮襲台】宜蘭山區累積雨量近300毫米 「4個地區」恐吹14級以上強風 2024-10-30 23:26
- 最新消息 不斷更新/康芮颱風假「美麗華影城」暫停營業一天!全台「電影院營業時間」懶人包 2024-10-30 23:00
- 最新消息 張顥瀚涉詐助理費、陳啟昱捲弊案 民進黨廉政會立案調查 2024-10-30 22:38
- 最新消息 不斷更新/康芮暴風圈觸陸!10/31颱風假一次看 全台22縣市停班停課 2024-10-30 22:30
- 最新消息 從366公尺高空墜落負重傷! 美國陸軍「玩真的」為台海戰爭做準備 2024-10-30 22:11
- 最新消息 【康芮襲台】晚間9點暴風圈觸陸 台東、蘭嶼發布颱風強風告警 2024-10-30 22:10
- 最新消息 【康芮襲台】颱風看病大台北12家醫院急診照常 門診異動一次看 2024-10-30 22:01

罷工,就是希望讓整個社會都真實感受到切身之痛,更迫使最直接受到產值損失的資本家認真思考(或者說計算),要不要答應罷工方的提案。(美國洛杉磯教師大罷工/美聯社)
年假結束前夕,華航機師工會決議發起罷工。
罷工開始後,社會上有一派輿論砲火猛烈的抨擊發起罷工者影響旅客權益…。
影響旅客權益論的諸多說詞就不逐一贅述,反正沒有好聽的,最多就是起手式來一個「我知道你有權利罷工…」,但說到最後就是「你不可以影響到我」。
罷工,如果誰都沒被影響,只是溫良恭儉讓的安靜坐在一旁舉標語和口號抗議,如果你是雇主,你會理睬嗎?
應該會暗地裡記下發起者,等事件過後再默默處理掉吧?
罷工,本質上就是要癱瘓既有的社會秩序,就是刻意破壞掉原本運轉有序的社會秩序,讓社會或企業付出額外的成本,逼得資本家或主政者答應坐下來談判的一種抗議手段。
為什麼馬克思當初在資本論中宣稱的無產階級革命最終沒有發生在歐美社會?有社會學者認為,是戰後工會崛起,工會能夠罷工以爭取勞動權益的關係,民主社會將推動秩序變革與進展的破壞性能量(熊彼得曾經說過的破壞式創新)納入了社會運作的遊戲規則中,讓勞動階級的聲音可以有管道發出,甚至某種程度的容許(通常是不傷害人命)破壞社會秩序。
今天勞動階級的勞權之所以大幅躍進,幾乎都是靠勞工團結罷工所爭取來的,極少數是由資本家自己主動宣布修改法律的,見諸歷史,可見罷工有其必要性。
黑天鵝的作者塔雷伯曾說過,那些沒有切身之痛的人說的話,可以不用理。好比說,不拿自己錢出來投資的分析師,不要相信,因為不是賠自己的錢,不會痛,所以即便犯錯也學不會教訓,更可能任意揮霍客戶的錢。所以投資界有句嘲諷話說:你客戶的遊艇在哪裡?
罷工,就是希望讓整個社會都真實感受到切身之痛,讓某個存在時所有人都覺得理所當然的東西刻意缺席,透過缺席凸顯出其存在的必要性以及社會必須支付的額外成本,迫使所有人認真思考,這場罷工的必要性與訴求的合理性,更迫使最直接受到產值損失的資本家認真思考(或者說計算),要不要答應罷工方的提案。
 許多跳下來罵罷工的人,多半是沒有實際受影響的旁觀者,卻罵得比受影響但能體諒的旅客還兇。(攝影:張哲偉)
許多跳下來罵罷工的人,多半是沒有實際受影響的旁觀者,卻罵得比受影響但能體諒的旅客還兇。(攝影:張哲偉)
上述是理想的罷工情況,遺憾的是,在台灣,每次罷工發生,總有人以道德或專業倫理進行情緒勒索,控訴發起罷工方沒良心沒擔當沒責任感沒有職業倫理…,卻很少去思考為何社會輿論如此不友善還是要發起罷工?甚至直接幫雇主方迴避掉其應該承擔的責任?
勞工發動罷工,是最需要付出切身之痛的代價的,因為就算罷工成功,也可能被組織內部高層點名作記號,未來可能失去更上一層樓的機會,甚至被藉故弄走,但即便如此都仍然願意罷工,顯見有我等外人所無法理解的深刻問題必須解決,就算以我們的常識或法規判讀之下覺得並無不合理,箇中細節可能只有當事人才知道隱藏其中的關鍵?
關於罷工,可以談的面向有很多也已經很多人談了,本文只是想談談切身之痛這個角度所看見的一些現象。
好比說,還有一點很有趣,如果是人在現場真的被影響到的旅客跳腳罵人,也還情有可原,因為那是「切身之痛」,且可能真的有人生的緊急大事因此被耽擱。不過,網路上更多跳下來罵罷工的人,多半是根本沒有實際受影響的旁觀者,卻罵得甚至比受影響但能體諒的旅客還兇。
為什麼明明自己不會受影響卻氣得跳腳?
有人說這是奴性,主動幫主子想卻不幫同為勞動階級想。
在我看來,很可能有不少人骨子裡覺得自己其實是統治階級(只是因故還沒能上位或不能剝削人),不覺得自己其實和這些罷工者是同一陣線,甚至會去站在其實會剝削我們的另外一個陣線那邊來指責非難罷工者,這毋寧才是最值得深思的問題?
非要舉個例子的話,大概就是台灣社會對外籍移工的態度了。眼下台灣有五萬逃逸外勞,占總外勞人數的十分之一,比例不可謂不高。
之所以逃逸,規範外勞的法規本身不合理是其一,仲介抽傭太重讓外勞不逃賺不到足夠繳交當初出國的貸款是其二,然而還有一點我們經常忽視,那就是台灣雇主的虐待與剝削,這並不是罕見個案。
如果再考慮聘僱外籍移工的雇主大多不是經濟狀況特別好而是有迫切需求的群體,剝削外籍移工的本質,根本弱弱相殘。
有時候我在想,會否就是台灣輕易的就有容易剝削與傷害的沉默多數(大量外籍移工可剝削是其一;有個房子可隔成鳥籠出租,以扮起房東跟房客收租是其二),助長了俗民社會這種明明自己也是弱勢,卻覺得自己是雇主方,是(準)資本家的想法,造成了勞權伸張困難,人們普遍習慣以資方心態看事情,趨向保守右派而非社會公平之實踐的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