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幼兒園狼師」毛畯珅性侵6童重判28年 二審坦承「摸過所有女童」再押2月 2024-11-28 12:33
- 最新消息 一邊斡旋停火一邊賣武器 拜登政府再度推動對以色列221億軍售 2024-11-28 12:20
- 最新消息 白鹿新劇四搭《墨雨雲間》王星越抖音話題量衝破億 她被直擊穿睡衣進組萌翻全網 2024-11-28 12:15
- 最新消息 黃紹庭涉詐助理費遭起訴 認罪並繳回1455萬元盼從輕量刑 2024-11-28 12:10
- 最新消息 中選會公告王義川遞補不分區立委 預計最快下周一就職 2024-11-28 12:06
- 最新消息 《永夜星河》丁禹兮與虞書欣CP感爆棚 兩人3年前「這互動」畫面曝光超鹹濕全網暴動 2024-11-28 12:00
- 最新消息 《膽大黨》快閃咖啡廳首度登台!角色餐點、特典一次看 台灣限定日本立繪亮相 2024-11-28 12:00
- 最新消息 以色列上訴要求ICC延遲全球通緝納坦雅胡 法國暗示不會抓他 2024-11-28 11:55
- 最新消息 【黃巾之亂】采盟遭曝與桃機簽約25年 王鴻薇要求檢討霸王條約 2024-11-28 11:54
- 最新消息 台中公捷處長熊抱、摳手性騷6女 遭「歷年最重處分」、百萬退休金也飛了 2024-11-28 11:50

無法不歸寂,又無法不從死寂中再生波瀾,再起萬念,於是,就有了今天的香港。(圖片取自The Culturist 文化者臉書)
牛仔衣褲,中分頭,扔在地上的《破壞王》漫畫書,空曠的地鐵裡相擁的情侶,這是我們熟悉的九十年代,和今天的香港諸多不同,但最大的不同是沒有人低頭看手機,他們看拍攝他們的鏡頭。
這顆28mm鏡頭持在青年謝至德手中——三十年後他成為香港最重要的中堅攝影師之一,但那時候他和他常常拍攝的「夜青」一樣,是一個尚未預料到香港會走向何方、只求在每一刻留下生命印記的孤獨個體,他喀嚓喀嚓的快門聲是木刻刀一般的試探。
和大多數那個年代的城市紀錄者不同,謝至德習慣於繞過那些在那個年代熠熠發光的東西。他的照片後景總有精彩,配角總是搶戲,布置櫥窗模特的人比模特更像假人⋯⋯這也是謝至德審視香港的方式,這本書裡的九十年代貌似避開了時代風起雲湧——實際上是避開了西方傳媒的新聞視角,去觀看小波瀾是怎樣在平凡人身上漾開,波動同樣平凡的我們。
 三十年後謝至德成為香港最重要的中堅攝影師之一。(圖片取自The Culturist 文化者臉書)
三十年後謝至德成為香港最重要的中堅攝影師之一。(圖片取自The Culturist 文化者臉書)
關鍵是謝至德身在其中,作為當時尚算寂寂無名的一個攝影工作者,他每天出門帶兩部相機,一部拍報社要求他拍的新聞照片,屬於「公的」,另一部拍自己想拍的情景,屬於「私的」——那個年代的香港攝影師不可能拍攝日本的「私攝影」,除了因為謀生的要求,還有因為這個城市的公共性遠遠壓到私隱性,每一個人都必須與公共發生關係,無論是創作者還是被攝者。至今依然。
《九十年代香港面孔》裡的照片大部分曾經以《近照香港:定格路人甲乙丙丁》為名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出版,當年撰寫評論的文化研究學者陳嘉玲提到「對峙」,作為那個時代謝至德街頭攝影的關鍵詞,我非常同意。
但她強調的是攝影者與被攝對象的緊張關係,我的觀感不一樣,謝至德作為攝影者是極其不挑釁的,他無限靠近但是散發著親和的氣場,就像他本人一樣,反而能從容留存下來攝影內部的「對峙」,這是香港無處不在的階級「對峙」、文化「對峙」、情感「對峙」,表現在攝影中就是意象「對峙」。
這種「對峙」不一定是衝突的,也可以是互為犄角的,躊躇滿志的廚師與侍應生,配得上他們背後的尖沙咀鐘樓。循道公會的建築前面是配戴玉刀的裸身青年,誰也改變不了誰。街童與坐在嬰兒車裡的“巨嬰”同在,在森然豪宅前面是抽著假菸的小學生。
低下階層多「不羈放縱愛自由」,無論是公共電話下面一無所有只有褲袋裡一團紙巾的「老泥妹」(當時對年輕露宿女性的蔑稱),還是地鐵車廂裡骨牌傾倒一般的牛仔服姊妹,有的是聽Beyond與Nirvana的一代青年的真摯;赤柱擺攤賣墨鏡的夫婦,眉目間能見過去的風塵。
他們是遺民,也是逸民。和那些被大時代綑綁的弄潮兒不一樣。
這一切之中,九七似乎隱形,然而九七之人凸顯,這屬於謝至德式的反高潮。正如在西環後巷的一張照片裡,背景有移民賣樓的招貼,前景的人卻依然安居樂業,剔牙理髮,波瀾不驚。
更有被選為封面的最精彩也最曖昧的一張:煙霧遮蔽了面孔的賦閒男子,頗像宮崎駿的無面人,從都市的齒輪中逸出,無所謂於自己的名字與身份。角落另一隻夾著香菸的手與他的手呼應,暗示了無面人不是孤島一個,而是無數孤島。他們無人在意,而他們並不在意的,是地上的那張英文報紙,刊載了什麼大新聞——這些牽動城市中產去向的字眼。
「萬念.叢生」,是這批照片在去年重展的名字,之後是「萬念.歸寂」。雖然是中年謝至德的覺悟,我旁觀著卻很是欷歔。聯想到九七之際,鏡頭前後那些人們多少都有過對未來的想像——我也曾經是那個坐在文化中心外噴水池談人生談未來的青年,不過他們是在1995年,我在1997年——最終,形勢比人強,無法不歸寂,又無法不從死寂中再生波瀾,再起萬念,於是,就有了今天的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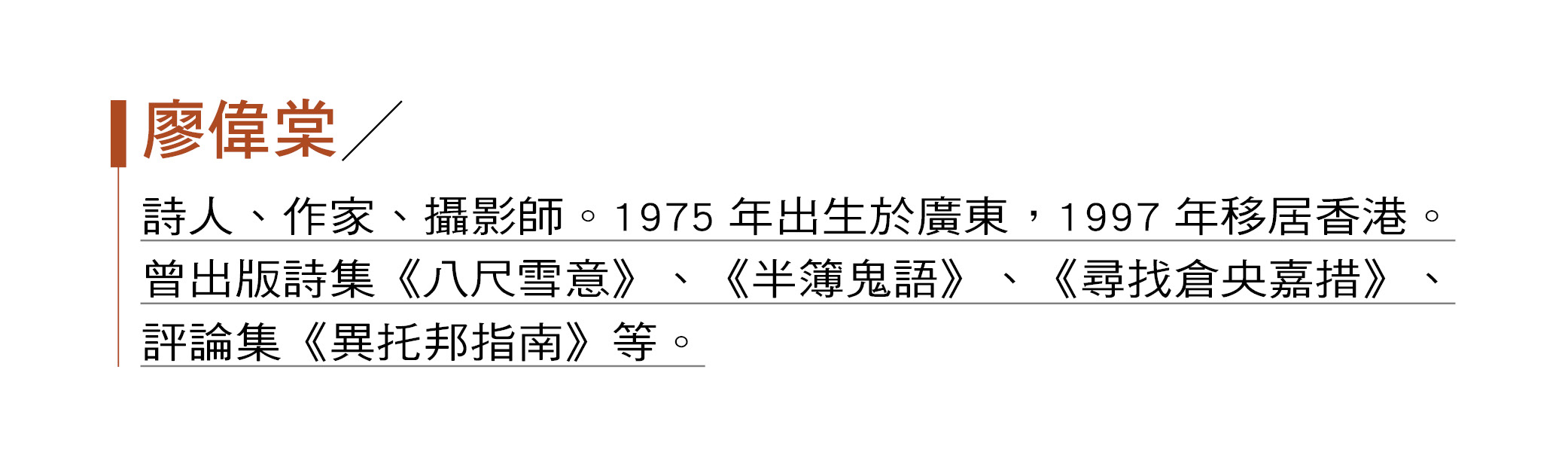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珠簾玉幕》大結局趙露思、劉宇寧擁吻訣別 她含淚哀求他「這句話」全網哭翻求番外篇
- 傳賴清德想把500元鈔票改印「中華隊奪冠照」 央行確定發行12強紀念幣
- 《深潛》成毅新劇搭檔《大夢歸離》古力娜扎 台灣女星演武林高手劇照曝光全網認不出
- 大風吹時間!《英雄聯盟》LCK 賽區各大戰隊轉會期 11/23 人事異動整理
- 【中華隊奪冠】麥當勞大薯買一送一!拿坡里、漢堡王、必勝客等 7 家速食優惠懶人包
- 《春花焰》吳謹言與老公洪堯牽手逛街孕肚藏不住 他因「這理由」挨轟沒擔當
- 《珠簾玉幕》大結局趙露思、劉宇寧生死訣別掀淚海 她與「崔十九」從宿敵變知己全網感動
- 【世棒爭冠戰】台日先發投手年薪差31.5倍 中華隊若奪冠每人獎金可望破千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