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不斷更新/【世棒四強賽】「中華隊 vs 美國」吉力吉撈安打助中華隊攻佔1、2壘 6局下3:2領先 2024-11-22 13:19
- 最新消息 「巴西川普」波索納洛涉嫌政變 與4將軍企圖毒死或炸死正副總統 2024-11-22 12:50
- 最新消息 賴清德總統任內首次出訪選擇南太 黨政人士曝戰略考量 2024-11-22 12:40
- 最新消息 《大夢歸離》侯明昊錄真人秀在非洲草原拉屎 全程被外國遊客拍下秒登熱搜糗爆 2024-11-22 12:34
- 最新消息 【有片】露面了!謝宜容鞠躬道歉 落淚稱對不起家屬:孩子成冷冰冰遺體 2024-11-22 12:20
- 最新消息 美特使還在以色列進行調停 以軍持續對黎巴嫩空襲釀47死 2024-11-22 12:03
- 最新消息 徐千晴重提高虹安「北一女案」 批大官對「良善」解讀與大眾脫節 2024-11-22 11:59
- 最新消息 《永夜星河》丁禹兮霸氣砸48萬買虞書欣封面雜誌 他這舉動暗藏「超甜細節」全網嗑翻 2024-11-22 11:44
- 最新消息 【擴大健保財源】健保署改革補充保費 擬增售屋、賣股票項目 2024-11-22 11:40
- 最新消息 對俄天然氣工業銀行祭出制裁 美財長葉倫:使俄軍更難取得資金 2024-11-22 11:23

國內市場太小,正是影音產業走向國際化的動力,有此認知,韓國娛樂公司因此更加堅定讓藝人往海外發展的決心,以便在國際市場獲取規模經濟並學習新技術與新知識,值得台灣借鏡。(湯森路透)
在台灣如此分歧的社會,「台灣市場太小」是少數能夠跨越統獨、階級與職業而能夠獲得廣泛認同的概念,無論藍綠政治人物、政府高官、企業領袖、知識份子到社會各界人士,幾乎都將市場太小掛在嘴邊,作為論述的起點,認為台灣市場的規模限制了發展的可能,不僅吳宗憲以此作為依賴中國市場的理由,國民黨也據之闡述兩岸經濟統合之必要,民進黨則以之申論新南向政策的重要性。市場太小在台灣就如同公理一樣的存在,是不證自明的真理,是所有產業政策的起點,但是我以為正是這種說法阻礙了台灣社會認識台灣市場的真正意義。
音樂的世道不好,舉世皆然,根據IFPI的統計,世界的音樂總產值從2004年的219億美元降到2015年的150億美元,減少了32%;其中數位音樂比重從2004的2%逐年遞增,到2014年首度超越實體音樂而大勢底定。
曾打擊韓國音樂市場的四個因素
比較2000年時的台韓音樂市場,韓國不僅和台灣一樣有市場規模太小的問題,人均音樂支出也低於台灣,而且剛經歷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國家元氣大傷,更由於盜版等因素,從2000年到2007年,音樂實體CD的銷量下跌了70.7%,而且還有四個因素令韓國音樂市場雪上加霜:
- 從歷史銷售資料來看,韓國音樂CD銷量的高低起伏很大,而且幾乎毫無規律,代表對音樂公司而言,經營的風險極高。
- 韓國的線上音樂收費極為低廉,令很多藝人與音樂公司幾乎無利可圖。2012年自韓國iTunes下載一首歌曲只要0.05美元(約1.5元台幣),美國價格最低的州也是韓國的10倍,日本更高達27倍。更有甚者,相較歐美日藝人可以收到下載費用55%的收入,韓國藝人只能拿到40%,因此下載一首歌的收入,歐美日藝人可以達到韓國藝人的13~37倍之多。
- 儘管90年代是音樂公司的黃金時代,但事實上在K-pop興起前,不僅音樂從未外銷,而且由於藝術與休閒的多樣化,1990年時的音樂市場比重比1960年時更小。
- 雖然全世界講韓文者有8,000萬人,但是扣掉北韓的2,500萬人後,與說中文者相差甚遠。
正是如此艱難的情況,反而成為韓國音樂國際化的動力,事實上韓國的例子並不特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發展經驗都表明,國內市場的狹小正是廠商國際化的動力,以便在國際市場獲取規模經濟、範疇經濟與學習新技術與新知識。相較當時更具國際化潛力的日本音樂,遠在K-pop這個詞還未為世人認識之前、遠在韓國音樂外銷收入仍為零的時候,日本的J-pop就已經傳頌東亞,日本在國際上有比台韓更為卓越的軟實力,但是正因為日本本國市場的規模已經足夠,反而使得日本音樂公司對國際化躊躇不前,畢竟進入外國市場的障礙高、失敗風險也大(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導致今日J-pop在國際上的發展不如後起的K-pop。

本國市場的困境反強化了國際化的誘因
不僅市場規模,本國市場的困境也會強化國際化的誘因,正因為韓國音樂CD的收入極不穩定,所以3大娛樂公司要進入國外市場以降低本國市場的風險,而且由於國外線上音樂的收入遠較本國市場為高,所以更堅定娛樂公司與藝人往海外發展的決心,而K-pop海外發展的軌跡,從日本開始再進入美國,不僅與音樂文化與地理親近性有關,也與收入的多寡吻合。
台灣對本國市場的理解需要超越簡單的市場規模,芬蘭人口不過5百萬人,卻能夠產生一度稱霸世界手機產業的諾基亞(Nokia),也與其市場特色有關。芬蘭素有千湖之國之稱,早期人口更加稀少而且彼此因湖泊區隔,而在各城市地區間產生互有差異的通信設備與規格,諾基亞為了服務這個從任何一個角度看都是廠商夢魘的微小市場,耗費心力逐步整合全國通訊與規格介面後,累積了卓越的規格技術能力,助其進入國際市場後所向披靡,一舉成為世界手機霸主,這個號稱全球最惡劣的通訊市場反而成為諾基亞累積技術能力的關鍵。
相反的,巴西龐大的內需市場使得其軟體公司毫無國際化的企圖,因為國內龐大的市場幾乎占滿軟體公司全部的產能,因此沒有進軍國際市場發展的動機,雖然當時的軟體公司CEO曾經表示某些國外市場相當具有潛力,但是因為國內市場仍存在許多尚未開發的空間,所以他們寧願留在國內市場,也不願冒風險走出去,卻因此逐漸拉大與國際一流軟體公司的技術差距,造成日後必須苦苦追趕,後來當巴西的部分軟體業者國際化之後,這些國際化企業的技術也明顯領先死守國內市場的競爭對手。
「台灣市場太小」是過時的論述
「台灣市場太小」是一個過時且陳舊的論述,既不符合世界發展經驗,也蒙蔽了許多人認識世界的視角,許多國際企業的常識,在台灣言論市場中竟顯得無比陌生。關鍵不在台灣市場太小,而是如何將市場理解為多面向的制度,廠商如何在其中建立獨特的優勢;國際化的關鍵也不在走出去就好,而是如何走出去,和為何走出去,為了市場(規模經濟)還是知識(技術)將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對此韓國娛樂公司國際化的過程,相當值得同為後進者的台灣音樂公司注意。
如同我在前一篇文章所述,韓國娛樂公司成功地結合東西方的音樂與舞蹈,找到未被滿足的市場,並勇於面對音樂數位化所造成的威脅與機會,採用差異化策略重組價值鏈,改變自己在世界音樂產業分工的位置,促成了K-pop在國際的興起。
事實上從實體CD到線上音樂的數位化過程中,韓國娛樂公司得以重新檢討資源配置,進而有助於國際化。傳統上一張22美元的CD,有將近40%用於廣告以及銷售,真正用於製作的成本有限,因此那些批評FB(臉書)與iTunes賺取過多暴利的人,實則未能從音樂公司的角度理解。
線上音樂改變娛樂公司經營模式
對三大娛樂公司而言,走向線上音樂不僅得以分配更多的資源用於生產內容,而且也改變了他們的經營模式:
- 就韓國本國市場生態而言,由於韓國下載音樂的價格極低,一張CD的價錢,在歐美日約等於下載10~15首歌曲的費用,但是在韓國可以下載約250首歌曲,導致韓國的音樂下載市場極為發達與高度競爭,足以產生各種多樣性的音樂,也有助於娛樂公司的差異化策略。
- 因此韓國娛樂公司將下載市場視為一個試煉場所,所有的新想法都可以先期測試,而實體CD則是經營粉絲的產品,死忠鐵粉會以蒐集CD的齊全代表在粉絲圈的地位,娛樂公司也因此開發出不同的粉絲經營之道。
- 線上音樂的收入主要來自廣告,因此娛樂公司也積極多角化,令旗下的藝人接觸廣告、戲劇等多樣化的收入來源。
- 線上音樂也使得製作歌曲的成本較為低廉,因為可以透過各種軟體製作以測試市場為目的的歌曲。
雖然經營藝人永遠是娛樂事業的核心,不過因為長期專屬性的投資,娛樂公司進一步利用多人團體降低對公司投資的威脅,因為在多人團體中個別成員受傷或是退出,並不影響該團體繼續運作,也因此使得公司對藝人有極大的議價力量。Patrick Messerlin和Shin Wonkyu的統計也證實了這一點,在他們計算的各種CD、下載、串流、YouTube等各種市場對供給者的集中度(Herfindahl和C4),發現集中度都偏高,代表娛樂公司對於包括藝人與詞曲創作者等各種供給者的議價能力都很大,因此他們的收入偏低。
但是從消費者的角度,則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對消費者而言,除了YouTube之外,其他市場的集中度都非常的低,而YouTube的高集中度完全是Psy的〈Gananam Style〉所造成的,除去之後,所有市場的集中度都偏低,代表韓國娛樂公司在消費者端存在激烈的競爭,因此每家公司必須時時創新求生。
這導致每家娛樂公司的特色都略有差異,例如龍頭SM向來被視為偶像製造機,以機械化大量生產偶像團體聞名,而YG則更鼓勵藝人團體的獨特性格,至於JYP創辦人朴軫永熱愛表演,不僅積極活躍於線上,更經常參與旗下藝人團體的活動,例如在Wonder Girls的〈Nobody〉和〈Tell me〉MV中,都可以看見他的身影,他也不同於SM和YG一開始只尋求與歐美音樂公司合作,最早就直攻美國音樂市場,頗有當初諾基亞以芬蘭無名小卒的國際化首攻美國的味道。
台灣應為國際化鋪路
由於缺乏台灣類似的音樂統計資料,我無法直接比較兩國的音樂市場的集中度,不過如果以電視節目來看,台灣市場在上游由於政府的管制政策,呈現由高度垂直整合的系統頻道商壟斷,而缺乏競爭,在下游則由眾多頻道導致的市場零碎化,相較日韓知名節目的收視率可達當地的30%,台灣的節目往往必須在3%上下掙扎,無論這是否反映台灣觀眾品味的多元,其效果是使得台灣市場在廠商心目中比實際上的規模更小些,如果沒有國外市場的支持,本國市場通常難以符合規模經濟的要求。
不過這種零碎的市場結構也可能意味著台灣對某些類型的訊息更為敏銳,例如台灣觀眾乃是世界上最早接受K-pop的群體之一,韓流(hallyu)正是源自1999年韓國剛開始試探文化輸出時,由台灣觀眾注意並加以命名。因此如果音樂公司能夠活絡台灣音樂市場的話,實可以如韓國的音樂下載市場一樣,將之打造為多樣化音樂的早期試煉所,為國際化鋪路。
K-pop的國際化,除了JYP由於創辦人朴軫永背景之故,最早直取美國,在2010年時,當時仍屬JYP的朴載範(Park Jay)的歌曲及專輯,已經在美國、加拿大及丹麥的iTunes R&B排行榜上高居第一。但是國際化最成功者還是SM,其中2010-2011年在韓、中、美、日、法的世界巡演(SM Town Live World Tour),具有指標意義。例如在巴黎時,原來6月10日演唱會的票在15分鐘內售罄,導致將數百名法國青少年粉絲在羅浮宮前跳舞及示威抗議,SM只得宣布在6月11日加開1場,結果票仍然在10分鐘內售完。演唱會當天,來自歐洲各國的7,000名粉絲齊聚巴黎,沈醉於東方神起、少女時代、Super Junior、SHINee和f(x) 的表演,巡演的成功正式對世人宣告K-pop國際化時代的來臨,隔年Psy點播率世界第一的〈Gananam Style〉只是早已滿天K-pop星辰中最閃亮的一顆流星。

細究K-pop國際化之道,文化學者所津津樂道的由SM娛樂創辦人李秀滿所提出的文化技術(culture technology),其實只是國際企業理論ABC,於其他產業行之有年,所謂文化技術,是李秀滿根據韓國資訊產業所提出的音樂國際化三階段:
- 先令旗下藝人在韓國市場廣受歡迎,以此為根基拓展至海外。
- 與海外公司或藝人合作,擴大當地市場。
- 與當地公司合作成立分公司,傳授並複製文化技術的國際化模式。
以結構洞做解釋
其目的在於子公司可以藉由當地股東的資源擴展當地市場,而母公司仍保有核心的控制權,SM母公司的外資有日資Digital Adventure (19%)、中資阿里巴巴(4%)。YG的外資包括中資如Shanghai Fengying (8.9%)、騰訊(4.9%)、法資如Shinhan BNP Paribas(4.4%)等,韓國人仍掌有絕對的控制權。
真正植根於K-pop國際化背後隱而不顯的乃是佔據結構洞(structural holes)位置,結構洞是我讀博士班時的老師Ron Burt教授創造來描繪社會結構如何給個體帶來機會與優勢的社會資本理論,關鍵在於連結兩個原先彼此缺乏連結的異質性群體,例如李登輝時期的亞太營運中心試圖將台灣打造成為連結亞太各國的節點,馬英九時期則試圖讓台灣成為中國與西方的中介,也就是佔據中西之間的結構洞位置,但是結構洞要能發揮功用,必須要所中介的兩個群體之間缺乏連結或難以溝通,當中美之間可以獨自聯繫共同完成生產鏈時,台灣的優勢也就隨之消失,因此結構洞的優勢有其半衰期,如果僅僅想依靠所謂的戰略位置而不尋求創新者,要不就逐漸滑落到價值鏈中附加價值最低的地方,要不就坐等優勢逐漸消失而遭受取代。
K-pop的國際化在佔據音樂內容與生產上的結構洞,在內容上,K-pop結合西方音樂、B-Boys的舞蹈、以及韓國的繩索舞傳統,在文化上銜接西方的音樂與東方的秩序與乾淨的語言,滿足了過去未被滿足的市場;在生產上,韓國利用技術變遷之際重組價值鏈,以差異化策略整合進全球分工較高附加價值的活動。
事實上韓國娛樂公司並不是一開始就如此清楚的定位,例如早期SM將寶兒等藝人引進日本市場時,仍採用的是傳統類似J-pop的高音樂密度與較低舞蹈密度的類型,經過幾次嘗試才找到K-pop的定位。這種學習型組織是追求知識的國際企業的特色,因為佔據結構洞者通常得以快速地接觸不同文化,因此不僅在決策時的限制較低,結合異質知識創新的機會也比較高。
同樣佔據結構洞位置,台韓的分別不僅在於雙方策略的差異(台灣成本領導,韓國差異化),而且在於台灣企業將結構視為靜態,僅想依賴結構位置獲利,韓國企業則以動態看待結構,而能夠真正結合不同文化與資源而加以創新,造成兩國差異者,不僅是結構,更重要的是人是否能實現結構的優勢。
韓國練習生制度
K-pop的國際化在國外與國內帶來的反應也不盡相同。儘管K-pop的產值從2005年的世界第29名飛速進步到2014年的第8名,但是其文化在國際流行樂壇上仍處於半邊陲地位,例如SM早期將寶兒與東方神起引進日本時,必須以J-pop的形式唱日文歌曲,這不僅是為了在日本打天下,更因為日本的文化軟實力優於韓國之故。
韓國與具有流行音樂霸權的美國相比更為明顯,韓美兩國是在世界音樂產值下跌趨勢中,少數逆流而上的例外,美國產值佔世界1/3,將近韓國的18倍。市場規模大不僅使得美國競爭激烈,有更多實現規模經濟的機會,以及更多創意的空間,更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強調的:市場的大小限制產業的分工程度,越大的市場越能夠養得起各種專業的廠商,導致分工更為精細,因此美國娛樂產業的優勢在高度專業分工與市場創新,藉以掌握附加價值最高的部分,而韓國娛樂公司則僅會在牽涉到關於K-pop的專屬性投資的地方,進行垂直整合,例如主導美國音樂的3大公司Universal、Sony與Warner,不若韓國有練習生制度,而多由星探或是音樂公司發掘有潛力的歌手,同時美國3大各自掌有全球的通路,而韓國3大連在本國都必須合資建立銷售通路,在海外更只能完全依賴海外的通路商。
美國因為具有文化霸權,所以詞曲音樂內包,很多甚至由歌手自行創作,還有大量的舞蹈、編曲、錄音、舞台、特效等專業公司提供各種服務。相較之下,韓國必須借助歐美音樂家的歌曲創作與編舞,獨立的專業工作室在韓國力量甚微。不過為了迎合亞洲觀眾的需求,K-pop強調純愛而非性愛的歌詞,不僅得以與歐美歌曲稍作區別,也更容易在中東、印度等文化上較保守的地方獲得接受。
由於與西方音樂的高度合作,令有些韓國音樂工作者懷疑究竟K-pop還能不能算是「韓國」音樂,而且在3大娛樂公司勢力壯大之後,他們甚至無法想像韓國還能夠有機會產生像周杰倫那樣一個人開創一個時代的獨特華人音樂,台灣音樂豐沛的創作能量曾經是某些韓國創作者欣羨的對象。也有人認為像SM這樣以流水線生產偶像團體的作業方式,正是斲傷創造力與「韓國」音樂的元凶,如同獨立音樂研究者Song Myoung-Sun所說,有些韓國地下音樂工作者視主流音樂為具有高度服從性與商業主義的符號,因而拒絕加入主流,以便維持藝術的創造力與自由。
對OECD智財權的批評
但是西方則視K-pop為一成功的故事,相較傳統西方影視中將亞洲人視之為神秘、冷酷、狡猾、缺乏男子氣概等負面形象,K-pop挑戰了這些刻板印象,並帶來難以放入傳統分類的新亞洲人形象。但是這種挑戰不該被過份高估,整體而言,韓國在文化上仍處半邊陲地位,娛樂公司所打造的全球價值鏈的成長性與持續性仍有待考驗,韓國政府統計音樂產業在2015年共出口3.54億美元,其娛樂公司所經營的海外粉絲共3,500萬人,雖然粉絲持續成長,但是在近年來樂團大增的情形下,部分粉絲開始對娛樂公司的策略不再言聽計從,新樂團能否接棒也成疑問。
除了國際化策略之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韓國對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態度,當台灣的音樂公司怪罪政府保護智財權不周為頭號戰犯時,韓國藝人對此則有相當不同的態度。由於韓國是OECD的一員,因此受到嚴格的OECD智慧財產權法的約束,不僅約束詞曲創作人,唱跳歌手與娛樂公司也包括在內,事實上韓國下載音樂費用如此低廉,智財權本就不太成問題,因此OECD的做法也引發不少批評,有人甚至諷刺地說道如果近代歐洲已經開始實行OECD的智財權,我們今天也許永遠見不到《唐吉軻德》的全貌(因為Cervantes在1605年出版了《唐吉軻德》第一部之後,就遲遲不肯動工,後來因為Alonso Fernandez de Avellaneda偽作了第二部,逼得Cervantes只得親自動手,直到1615年才出版了第二部,如果當時有嚴格的智財權保障,或許《唐吉軻德》全貌就永不見天日),過去10年在歐洲更是對智慧財產權有嚴厲的批評,也獲得相當多的支持,冰島的海盜黨甚至即將贏得大選。
因此或許和有些人的臆想相反,韓國藝人並非普遍歡迎嚴格的OECD智財權規定,反倒想出種種辦法企圖奪回主導權,例如本身也詞曲創作的唱跳歌手Rain認為藝人表演的動機並非完全出自金錢,所以Rain後來用自己的公司垂直整合詞曲、編曲、編舞等活動,以便完全控制智財權,另一種方式則像寶兒成為其經紀公司SM娛樂的股東。
嚴格說來,自2008年開始大興的K-pop至今不過8年,卻已經展現驚人的成就,與台灣的比較顯示,「台灣市場太小」實為一束縛人心的教條,不僅妨礙了產官學研認清現實,更導致視野偏狹,阻礙了創意的發揮。如果要嚴肅思考台灣的出路,必須丟棄這些充斥台灣言論市場上不假思索、似是而非的假設,正確地理解台灣市場所蘊含複雜的意義,將視野拓展到世界,或許是擬定政府政策與企業策略的第一步,特別是2015年乃是全球音樂市場自1998年之後首度出現成長,也為世界上的音樂公司帶來一絲曙光。
「加拉巴哥症候群」
文創學者也不能將焦點過度置於政府的文化政策,歷史經驗表明,無論政府如何有錢以及能力超群,鮮有能在國際上建立任何具有競爭力的產業者,何況我們的政府並不以特別富有或無與倫比的能力聞名;關鍵仍在企業本身的策略及努力,尤其是企業主其事者的視野與策略,戰術上的勤奮無法彌補戰略上的錯誤,將帥無能不僅累死三軍,更重要的是可能錯失國際上轉眼即逝的機會,導致人人回過頭再盯著自己的肚臍,繼續在內需市場打得頭破血流,更加仰賴裙帶資本主義的特權與政府關愛的眼神過活,無從發展自主的事業與人格。
在文化傳播上沒有比只盯著自己的肚臍更糟的事了,達爾文在加拉巴哥群島(Galapagos)觀察到島嶼遺世而獨立時會演化出特有的物種,Chi-Ling Tor據之稱日本患有「加拉巴哥症候群」,用以描述日本因為過度重視本地市場而與世脫節的現象,當時仍屬日本的夏普在2010年推出以加拉巴哥命名的平板電腦,名符其實的除了日本之外,不對世界任何國家販售!日本卓越的手機工藝與創新也僅用來關注日本人的生活型態,導致日本高超的技術似乎越來越顯得與世界無關,而漸漸為其他國家趕上,6年後的今天,「加拉巴哥症候群」終於導致夏普幾乎破產而為台灣鴻海所購併。
當世界多數國家都已經走向數位音樂時,台灣也在2015年時數位銷售超過實體,但是身為全球第二大音樂市場的日本仍有75%屬於實體CD銷售,而且由於日本的智財權保障文化商品最低價格,使得其CD價格為其他國家的2倍,依舊不減日本人對實體CD的喜好,單曲CD仍動輒破百萬,CD租賃也仍然廣泛存在。Mun Keat Looi在《Quartz》認為日本老化的人口結構加劇這種現象,嵐已經成軍17年,廣受歡迎的福山雅治也已經47歲了,中年粉絲的購買力加深了偶像老化的現象,也拖緩了日本音樂數位化的進程,不利其國際化。
Euny Hong也注意到K-pop團體如少女時代所展現的女人味為日本所罕見,J-pop的超人氣團體AKB48仍經常會穿著中學制服,唱著〈制服が邪魔をする〉這樣的歌曲,對日本萌文化不熟的外國人構成相當程度的障礙,背後同樣存在加拉巴哥症候群的因素。
對音樂發展來說,不僅政府只是輔助角色,連結構也不足為恃。世間的事經常福禍相倚,如果不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令三星、現代、LG等舊有勢力退出音樂圈,K-pop的興起不會如此順利,當一個國家或社會的體制逐漸僵固時,需要制度創業家從中促成變革,K-pop的制度創業家像是SM的創辦人李秀滿出身歌手,YG的創辦人楊鉉錫是早期著名唱跳團體Seo Taeji and Boys的一員,身兼歌手、舞者與編舞老師的身份,JYP的朴軫永同樣出身歌手及舞者,即使成為集團創辦人,依舊活躍於線上。他們對音樂舞蹈的專業能力,有助於發展K-pop唱跳的類型,其中多人畢業自韓國一流大學,有助於在韓國如此階層嚴明的社會中佔有一定的文化資本,而且多數有留美經驗,也能夠找到具有國際經驗的CEO制定企業策略與國際化策略,如果沒有這些人的創新,即使佔有結構洞的位置或是獲得政府大量補助,也無能創立K-pop蔚為風潮。
延伸閱讀:沈榮欽專欄:吳宗憲所不了解的事-韓國音樂產業為何贏過台灣(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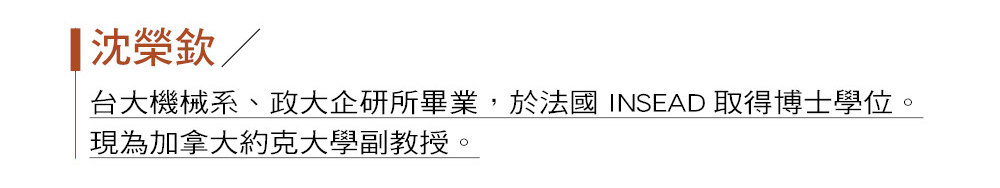
【上報徵稿】
上報歡迎各界投書,來稿請寄editor@upmedia.mg,並請附上真實姓名、聯絡方式與職業身份簡介。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起底謝宜容!傳身家背景雄厚「善做公關」 先生和綠營高層有交情
- 一元特典!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釋出「零星票券」,11/24 採實名制一般販售
- 【世界棒球12強賽】滿足「2條件」台灣確定晉級4強 今晚是關鍵
- 先搶先贏!Ado 五月林口體育館演唱會採實名制入場,11/19 輸入「指定代碼」可優先預購
- 【內幕】T112步槍裝彈器採購案疑專利侵權 以色列向軍備局寄存證信函
- 楊冪人氣暴跌與《慶餘年》張若昀演新片淪鑲邊女主 造型曝光全網夢回《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 王一博金雞獎典禮被抓包視線離不開趙麗穎 網揭兩人4年戀情無法曝光背後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