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大夢歸離》侯明昊錄真人秀在非洲草原拉屎 全程被外國遊客拍下秒登熱搜糗爆 2024-11-22 12:34
- 最新消息 不斷更新/【世棒四強賽】撐住!「中華隊 vs 美國」美國隊深遠安打得分 中華隊4局下2:1領先 2024-11-22 12:33
- 最新消息 【有片】露面了!謝宜容鞠躬道歉 落淚稱對不起家屬:孩子成冷冰冰遺體 2024-11-22 12:20
- 最新消息 美特使還在以色列進行調停 以軍持續對黎巴嫩空襲釀47死 2024-11-22 12:03
- 最新消息 徐千晴重提高虹安「北一女案」 批大官對「良善」解讀與大眾脫節 2024-11-22 11:59
- 最新消息 《永夜星河》丁禹兮霸氣砸48萬買虞書欣封面雜誌 他這舉動暗藏「超甜細節」全網嗑翻 2024-11-22 11:44
- 最新消息 【擴大健保財源】健保署改革補充保費 擬增售屋、賣股票項目 2024-11-22 11:40
- 最新消息 對俄天然氣工業銀行祭出制裁 美財長葉倫:使俄軍更難取得資金 2024-11-22 11:23
- 最新消息 西方國家官員表示 北韓高階將領首度在俄國庫斯克地區遭攻擊受傷 2024-11-22 11:00
- 最新消息 全聯隔日達改名「全電商」!每周六日一最高回饋 12.5% 黑五同步登場、爆殺品下殺 26 折 2024-11-22 11:00

目前分崩離析的香港,誰和誰能互相依靠呢?也許只有在抗爭中崛起的一代能在催淚彈的硝煙中體會互相依靠、相濡以沫。(近日香港群眾走上街頭,抗議北京政府干預法治/湯森路透)
「年代沒有關係,地點不必提及。/卻說有一回在大路上,七個良善的農人相遇。/他們來自粉碎省,來自悲苦縣,來自窮迫教區,來自附近的鄉村/—補丁鄉、赤腳村、襤褸鎮,荒涼、焚劫、和飢餓,還有沒有收成莊。/他們遇見了就爭論,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這一段精彩的詩不是鮑伯狄倫的歌詞,雖然很像他的風格。這是俄羅斯19世紀詩人涅克拉索夫的名作《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的開端。
好一句「年代沒有關係,地點不必提及」,因此我們可以把「俄羅斯」置換成「香港」、「中國」或「台灣」。這首詩一直縈繞我心間,直到最近看了一部溫情電影《幸運是我》,便更覺得有一寫的必要。
《幸運是我》是今年難得的一部算得上真正「港產」商業片—它真誠、在地、舉重若輕,在今天一片浮誇造作的合拍片浪潮中實屬難得。而且它的溫情又有別於大陸同類片的煽情和台灣電影的所謂小確幸式多情,而是繼承了香港電影黑白片時代的五味雜陳的幽默,很熨貼人心,雖然是導演羅耀輝的處女作,有不少遺憾的畫蛇添足,但已經足以讓久渴的香港影評人一片叫好。
不過反過來說,這部並非傑作的電影被香港人肯定,又顯示出香港電影、香港現實已經多麼窘迫。作為最大眾化的藝術形式,電影總是在一個極端時刻起到一個麻醉品的功用。這裡把《幸運是我》比做麻醉品並無否定導演誠意的意思,只是對香港人這樣說有點殘酷,因為大多數香港人並不幸運。
《幸運是我》裡的兩個角色,女主角是獨居老人芬姨,男主角是內地來港青年阿旭,這兩個本應不幸的設定相遇之後,彼此成為對方的「幸運」,這在今天香港幾乎是做夢。首先,大多數的獨居老人不會像芬姨那樣中年時無端獲老闆贈送一間房屋養老,同時,大多數內地來港的青年也未必能像阿旭那樣遇到許多善意對待。
最關鍵的是,現實中這兩種人是彼此敵對的包租婆與租客的關係。這種關係可謂當今香港民生議題裡最惹火的,在香港完全畸形的地產經濟中,擁有收租物業的業主絕大多數都是要賺盡一分一毫的勢利眼,動輒加租,完全不考慮租客的承擔能力和多少年的人情;而且滋生出香港特有的「劏房」間隔,一間本來只能住一家三口的老房子,往往被劏成六、七間甚至更多的鴿子籠出租⋯
無須多描述,台灣的電視傳媒今年已經帶著獵奇眼光介紹過不少香港人的悲慘住家。租貸霸權不過是香港最恐怖的地產霸權的末枝,卻以其赤裸裸的貪婪折射了香港霸權社會的全豹。當然,這是小電影《幸運是我》無法觸及的。
芬姨和阿旭,本來還應該象徵了香港未來的兩大問題:人口老齡化問題和新移民問題,恰巧有不少香港的建制派政客故作天真地認為,新移民的不斷放寬是對人口老齡化的有效補充。貌似這很像某些歐洲功利主義政客的接納移民理由,實際上前者背後隱含的對北方大陸的政治獻媚才是他們唯一考量,而不是具體的人的狀況。
電影讓芬姨和阿旭組成新家庭,當然不是政客說夢的圖解。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是芬姨的老派價值觀改變了帶著仇恨生活的阿旭,芬姨的一句香港俗語出現了兩次:「做人嘛,總是我幫你一點你幫我一點的」—這讓人想起五O年代香港左翼電影《危樓春曉》和後來的《七十二家房客》,乃至八O年代被廣為推崇的香港人同舟共濟精神。但這一切,在今日各種矛盾空前激烈的香港,顯得如此天真不可信,幫,是可以的,但首先要看看你的站隊。
說到底,今日沒有多少人在香港能過好日子。芬姨和旭仔這樣的基層市民,任由官商勾結所榨取殆盡。電影中旭仔任職的福利機構,在得不到足夠政府支援的壓力下艱難求存,有的甚至走向扭曲。中產階級成為政府大花筒支出的提款機,教育者成為洗腦與良知的磨心,小商家永遠敵不過租價的癌細胞式增長⋯
《幸運是我》強調幸運是找到互相依靠的人,而在目前分崩離析的香港,誰和誰能互相依靠呢?也許只有在抗爭中崛起的一代能在催淚彈的硝煙中體會互相依靠、相濡以沫何謂,雖然電影完全沒有涉及這一段新香港的歷史,但他們卻是最值得祝福的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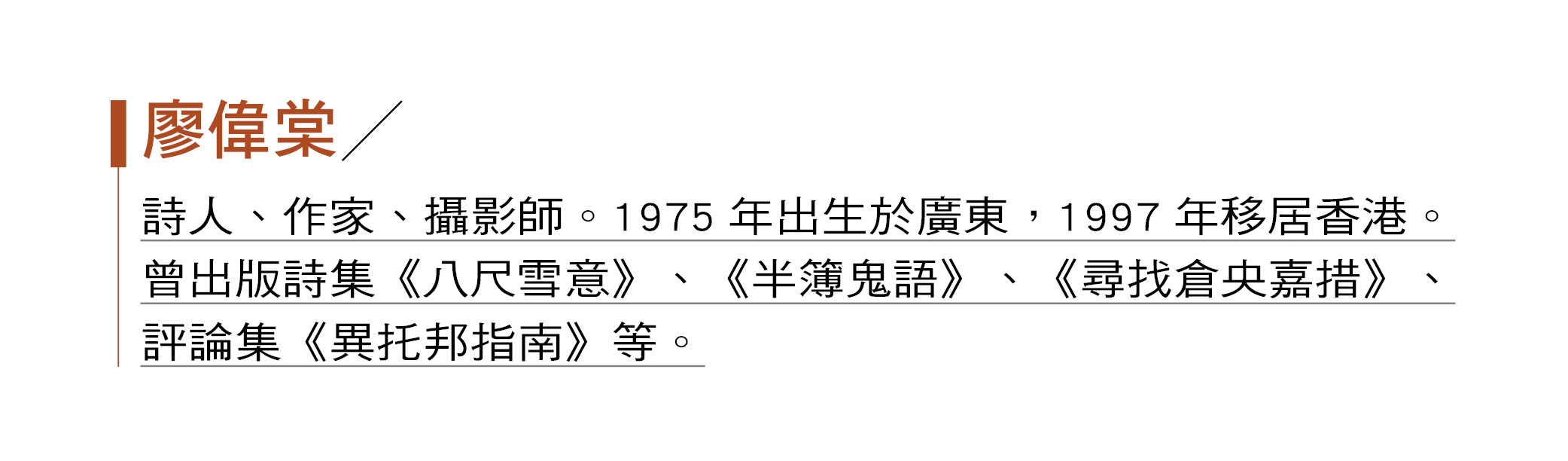
【上報徵稿】
上報歡迎各界投書,來稿請寄editor@upmedia.mg,並請附上真實姓名、聯絡方式與職業身份簡介。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起底謝宜容!傳身家背景雄厚「善做公關」 先生和綠營高層有交情
- 一元特典!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釋出「零星票券」,11/24 採實名制一般販售
- 【世界棒球12強賽】滿足「2條件」台灣確定晉級4強 今晚是關鍵
- 先搶先贏!Ado 五月林口體育館演唱會採實名制入場,11/19 輸入「指定代碼」可優先預購
- 【內幕】T112步槍裝彈器採購案疑專利侵權 以色列向軍備局寄存證信函
- 王一博金雞獎典禮被抓包視線離不開趙麗穎 網揭兩人4年戀情無法曝光背後真相
- 楊冪人氣暴跌與《慶餘年》張若昀演新片淪鑲邊女主 造型曝光全網夢回《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