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藍點名NCC外傳新委員翁柏宗、羅慧雯「意識形態強」 怒轟:絕不接受 2024-04-25 15:43
- 最新消息 《春色寄情人》李現360度甜吻周雨彤畫面超酥麻 她主動獻身名場面恐因「這關鍵」遭刪除 2024-04-25 15:10
- 最新消息 快訊/大雷雨強襲4縣市! 11縣市大雨特報雨彈狂炸 2024-04-25 15:05
- 最新消息 買便當送飲料 80 元有找!全聯美味堂熱便當推「世大運鹹酥雞」新口味超值開賣 2024-04-25 15:00
- 最新消息 全球首例!威尼斯今起開徵入城費 一日遊不繳175恐被罰1萬元 2024-04-25 15:00
- 最新消息 台北市林森北路「六條通」詭異命案 女雙手反綁、頭套塑膠袋套亡 2024-04-25 14:49
- 最新消息 才與媽媽通話!北市中正一分局男警自戕 「頭部中彈」送醫不治 2024-04-25 14:22
- 最新消息 前立委助理張書維涉襲胸、性侵女記者 更一審逆轉判3年2月 2024-04-25 14:19
- 最新消息 【有片】挺巴勒斯坦示威蔓延全美大學 眾院議長威脅出動國民兵鎮壓 2024-04-25 14:18
- 最新消息 輔大偷拍狼出沒?女大生如廁抬頭赫見手機 男大生辯:只是伸手穿衣服 2024-04-25 14:12

在奉俊昊的電影版《末日列車》裡,一列階級極端化的列車直接否定了改良的可能,乘客只剩下非此即彼的選項:革命,還是不革命?(維基百科)
這樣一個題目,難免讓人想到魯迅的《娜拉走後怎樣》。「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魯迅先生這句話,從晚清到未來,從北平到一列末日列車,依然有效。
此前,我寫過一篇《不作死就不會死嗎?》——點出《末日列車》的問題是一個革命問題,那就是人類要到達哪一條底線才會選擇革命?在奉俊昊的電影版《末日列車》裡,一列階級極端化的列車直接否定了改良的可能,乘客只剩下非此即彼的選項:革命,還是不革命? ——最終這些絕望的「後列乘客」不是因為物質貧乏而絕望,而是因為目睹階級懸殊及伴隨的不公不義而絕望,而終於選擇了革命。
但是革命以後呢?電影裡的列車到一個稍微不那麼嚴寒的地方剎停,車上剩下的也似乎都是正面人物,善良、堅毅而抱有希望,並且在雪地上發現了新生命的萌芽。電影畢竟有商業考慮,漫畫呢,可以更接近殘酷現實。這本《末日列車》的漫畫續篇《末日列車:終點站》(今年竟然在中國出版了簡體譯本)更拋出一個更嚴苛的問題:假如離開絕望但仍能苟存的列車,遇見一個活得較好但同樣有階級、極權和欺騙的「烏托邦」,你還選擇繼續革命嗎?
也許,如果不是因為女革命者瓦爾懷孕了,如果不是她和革命同伴普格是經歷過列車最殘酷的黑暗的人,這一切會「好辦」得多。列車的好處在於:它並沒有讓人做夢,它只是讓你苟存性命而沒有許諾升級、自由等等,因而瓦爾與普格等不存在「夢醒了無路可走」的情況。瓦爾唯一的夢是她腹中胎兒,與之相比,其他皆為虛妄。
《末日列車:終點站》裡的應許之地/迦南樂土卻是建立在兩個瘋狂科學家(美其名為「調度員」,不禁讓人想起文革時的「舵手」)的烏托邦夢上面,他們做夢做久了就自欺欺人,就算明知該夢虛假他們也得必須用暴力去維繫之,因為這個謊言是他們的權力和生命延續的保障。而被它們「拯救」和奴役的「白老鼠」們,符合「信徒」的一切條件,甚至可以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孩子被壓榨生命而忍受,就為了烏托邦營造者口中那個虛無縹緲的「未來」。而「調度員」的口頭禪是「我們別無選擇」。
這觸及了一切宗教或假革命名義的宗教都必須面對的問題:能否為了彼岸犧牲此岸?早期宗教幾乎都會以一個光明彼岸的許諾來教人民忍受此岸的種種苦痛和不公義,這也是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原因。後來極端的宗教組織還會鼓勵信徒為了彼岸的享受而在此岸做出罔顧自己與他人生命的行為,包括天堂之門(Heaven's Gate)丶太陽聖殿教(Order of the Solar Temple)丶人民聖殿教(瓊斯鎮)(Peoples Temple - Jonestown)、奧姆真理教等——然而,馬克思之後的主義者,也擅於這種許諾。
反而,宗教自身也有「正能量」,比如說耶穌的革命行為,根據《馬太福音》記載,耶穌這個名字是天使啟示下來的,天使向馬利亞宣告她要懷孕生子的時候,對她說:「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這決定了耶穌不只是一個自我修行者,更是一個要解放眾生的革命者,他的驅趕法利賽人以及在十字架上殉道,都是證據。
瓦爾與她腹中的胎兒,既是瑪麗亞與耶穌的隱喻,又讓二者合而為一,成為宗教自身的覺醒者、反叛者。更何況瓦爾本身就存在贖罪的潛意識——年輕的她本來是議員的女兒、既得利益者,並從事著為「破冰號」乘客編造「視覺旅行」這一精神鴉片的工作,後者其實就是本集的「樂園」的虛擬版本,具有一樣的以夢代替現實的功效。所以瓦爾並不容易像其他列車乘客一樣被樂園蒙蔽,她早已熟悉這一套騙人的手藝。
從繪畫風格來說,這一集《終點站》,羅切特的筆觸更狂放、調子更沉鬱。尤其讓人難忘的是他塑造的人鼠合一的形象,除了視覺上觸目驚心的不安感,還具有多重隱喻:對於「調度員」,這些戴老鼠面具的舊倖存者不過就是他們偉大實驗所需的小白鼠;而且,把敵對者物化、醜化,比如說盧旺達胡圖族人對圖西族人的大屠殺,前者就把後者反复描繪成蟑螂,使前者相信自己不是在殺人,是在消滅害蟲——這一點,最近我們在香港竟也耳熟能詳了,警察及其擁戴者,不就一直用「曱甴」(粵語的蟑螂)稱呼示威者甚至一般市民嗎?
 香港警察及其擁戴者,一直用「曱甴」稱呼示威者甚至一般市民,不也是相信自己不是在殺人,是在消滅害蟲?(湯森路透)
香港警察及其擁戴者,一直用「曱甴」稱呼示威者甚至一般市民,不也是相信自己不是在殺人,是在消滅害蟲?(湯森路透)
對於倖存者自己,這些面具是自欺欺人的防毒保障,他們不知道真正的污染來自核廢料;對於新一批接受他們奴役的列車倖存者,他們就是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不由得讓人想起古老的詩經,多麼諷刺的中國夢。
故事尾段,數頁鮮血的洗禮之後,一個莽莽蒼蒼的新世界才終於向我們展開了,瓦爾的孩子和其他孩子、甚至是孩子的孩子是新世界的繼承者,老去的蒂姆對他們說:「所有人都能在牆上畫畫。所有故事都很重要。」岩畫成為了《末日列車》的畫中畫,起的依然是記下、絕不忘記這樣的作用,讓人想起奉俊昊的電影版《末日列車》那個列車尾部黑暗中堅持畫下發生的一切恐怖歷史的畫家。蒼老的瓦爾和普格經歷了屬於她們自己的啟示錄,「重新選擇生存的峰頂」(北島《回答》)。
列車裡無夢的人是幸福的,因為他們可以選擇做屬於自己的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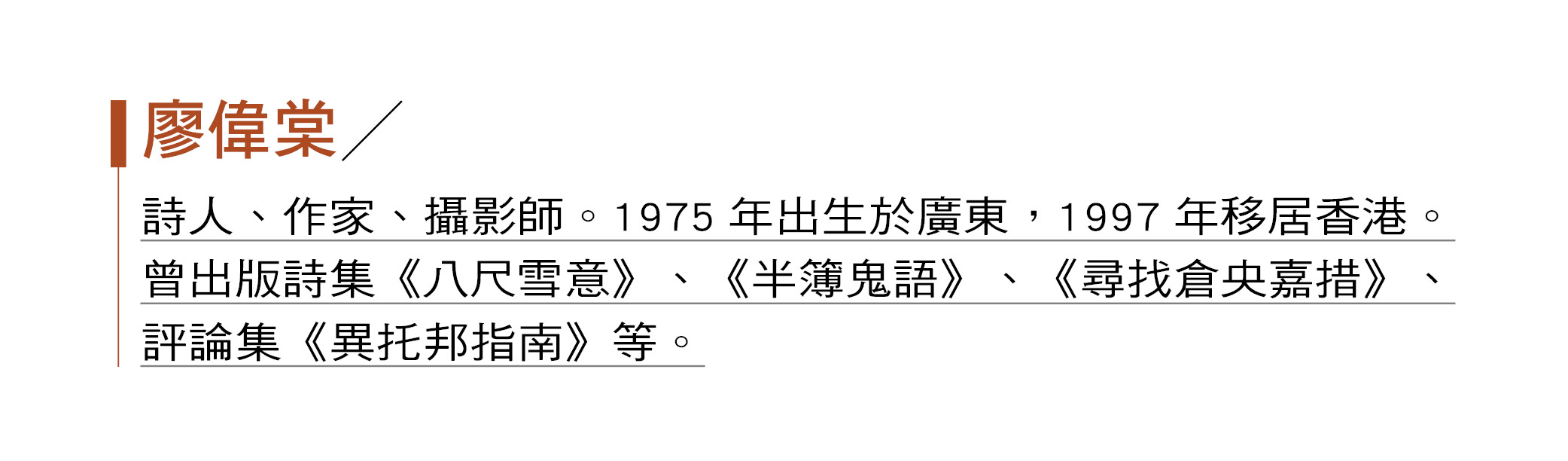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淚之女王》金秀賢逼哭觀眾迎來出道第3次爆紅 寵溺金智媛超甜蜜收視超越《愛的迫降》
- 投書:如果F15EX能加入台灣空軍
- 《不夠善良的我們》林依晨不忍賀軍翔婚姻冷暴力 「簡慶芬出軌」演技大噴發掀淚海
- 最多現省 486 元!拿坡里披薩、炸雞「買一送一優惠」只到月底 12 塊雞腿、腿排只要 399 元
- 《慶餘年》肖戰大學受封校草青澀帥照曝光 他因「這理由」不敢發自拍全網笑翻
- 《長月燼明》白鹿新劇搭檔《蓮花樓》曾舜晞爆不和 他「妝造醜翻」疑遭打壓粉絲氣炸
- 麥當勞買一送一!10 塊麥克雞塊、薯餅、焦糖奶茶通通有 歡樂送買一送一、深夜食堂享 79 折
- 《寧安如夢》張凌赫擠走緋聞女友白鹿成GUCCI大使 新劇與徐若晗花瓣雨下熱吻甜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