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謝宜容起碼幹掉賴清德半壁江山 2024-11-22 00:02
- 最新消息 投書:立院惡鬥 只會讓更多科技人企業人不敢投身政壇 2024-11-22 00:00
- 最新消息 勞動部稱謝宜容失聯明天不出面 吳母淚控:霸凌太過分、太惡毒 2024-11-21 22:05
- 最新消息 俄烏戰況恐升級 烏克蘭是否有能力攔截ICBM 2024-11-21 21:50
- 最新消息 明後兩天各地氣溫回升 北部、東北部18到23度濕涼舒爽 2024-11-21 21:45
- 最新消息 劍橋詞典2024年度代表字出爐 「manifest」反映人們追求身心健康趨勢 2024-11-21 21:43
- 最新消息 為了9萬元勒斃馬國女大生 陳柏諺一審判賠父母逾638萬元 2024-11-21 21:32
- 最新消息 觸犯戰爭罪、違反人道法 ICC對納坦雅胡、哈瑪斯領導層發出逮捕令 2024-11-21 20:47
- 最新消息 【世棒四強賽】「CT AMAZE」自費飛東京應援 推掉台灣活動損失近10萬 2024-11-21 20:45
- 最新消息 蔡英文抵達加拿大 感謝台灣鄉親熱情接機 2024-11-21 20:37

每個天朝主義的「民粹主義批判」話語背後,其實可能都躲藏著一個「川普式的幽靈」。(美聯社)
川普在美國總統選舉壓倒希拉蕊,不僅顯現了美國政治的劇烈變化,同時,也被許多人看作是世界秩序的分水嶺。這「許多人」當中,台灣最容易忽略掉的,或許是一位美國的政治學者,以出版《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而成名的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1月11日,福山在《金融時報》發表了專文—「對抗世界的美國:川普治下的美國與新全球秩序」(US against the world? Trump’s America and the new global order)。福山在文章中明確提出:整個人類世界,已經進入了「民粹式民族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為主導的動盪時代。
福山的論斷,在川普當選後近乎歇斯底里的歐美主流媒體話語中,並不特別讓人意外,也因此並未引起多少注意。但或許該提醒一些不知情的讀者:這位福山教授,並非等閒之輩。他在1989年,在天安門下的血跡尚且重擊人類靈魂的時刻,就立即以一篇以《歷史的終結?》為名的政治哲學論文,去論述「自由民主秩序乃是人類政治發展的終極形態」。
這篇有著醒目標題的論文,由於恰好發表在蘇聯與東歐共產政權瓦解的特殊歷史時刻,讓福山頓時成為全球知名人物,預言「自由民主的最終勝利」的當代先知。不但媒體爭相採訪他,就連法國哲學家柯傑夫(Alexandre Kojève)原本僅為少數哲學愛好者知曉的「歷史終結論」,也透過福山的大眾化手法,而成為西方媒體上的通行術語。
26年後,同樣是這位福山教授,但在他的筆下,從1950年代以來以自由民主體制為本的世界秩序,卻已在美國「民粹式多數」的衝擊下,陷入了自由原理與民主原理相互衝突的構造性危機。(圖為福山/維基百科)
自由民主體制:精巧而脆弱的現代政治秩序

那麼,福山是改變了他對「歷史終結論」的看法了嗎?
恐怕未必。福山其實從未改變過他的基本觀點。
在晚近例如《政治秩序的起源》這樣的專著中,他依然重申柯傑夫追隨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而做出的哲學命題:「世界歷史」,已經終結於1806年,終結於拿破崙擊敗了普魯士王國,從而將現代的自由民主理念和共和體制向整個歐洲進行「革命輸出」的耶拿戰役。
人類為脫離各種奴隸狀態,為追求普遍而平等的「承認」(recognition),因此啟動了漫長的「世界歷史」進程,但這個驚心動魄的人類文明演變,在18世紀末的歐洲,就進入了「最後階段」。就政治發展的邏輯而言,此後的人類歷史,實質的核心內容不過是這種現代自由民主秩序向全世界不斷地複製與延伸。用晚近福山自己的話來說:「固然我們會質疑,要多久之後全人類才能抵達那個終點,但我們不應該懷疑,某種社會形態確實挺立在歷史的終結處。」
因此,從政治哲學的角度說,人類為爭取「平等承認」而鬥爭的「世界歷史」,是確實結束了。「後歷史」的人類,將如黑格爾與馬克思所見,在相互承認彼此平等的自由主體地位的「自由王國」中滿足於實現自我的「確幸」;不但戰爭與流血的革命將會消失,人類在「世界歷史」階段中反思自己對自由的追求而產生的「哲學」,也將同步消失。
然而,哲學家所論斷的「世界歷史的終結」,對政治學者福山來說,事實上不等於人類歷史動力的真正終結。
現代自由民主秩序,是結構微妙而脆弱的人類造物,依賴著經由各種現代社會設施和治理裝置而建構起來的強大「國家能力」,依賴著穩固且獨立的法治運作,更依賴著迫使政府向人民負責的各種民主問責制度,三者缺一不可。甚至於,在自由民主體制已經建立的地方,如果政治制度僵化而無法適切而及時地反映社會發展的趨勢與需求,加上「家族化官僚」勢力的「復辟」,結果就可能形成既得利益群體構成的「尋租聯盟」,而在「制度化的腐敗」中,將自由民主體制帶向「政治衰退」的絕境或險境。
「政治衰退」與美國版的「金權政治」
對今日的福山,美國無疑地已經步入自己獨有的「政治衰退」路徑。
福山有時主張,儘管美國在法治與政治問責上並未出現基本的問題,但卻在「國家能力」的發展上呈現不足,國家本身的力量過於薄弱,似乎還特別缺乏了應對全球化下經濟和社會不平等持續擴大趨勢的「國家能力」。就此而言,以限制國家能力為前提考量,卻從不去思考「國家能力」問題的「否定性政治」,或許就已構成了美國在政治制度發展上獨特的僵化慣性。
不過,在某些時候,他也不忌諱地點出,美國例如布希家族或柯林頓家族所代表的「建制」勢力,已經滋長出了腐蝕美國民主運作的「尋租聯盟」。特別是例如「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這樣的司法裁決,居然以「言論自由」的名義,為企業無限制和無制約的政治獻金打開了直通捷徑,在不可阻遏的「利益團體政治」下,造成了美國版的「金權政治」。
那麼,我們不免要問:川普的「民粹式崛起」,難道不是正代表著反對這種「尋租聯盟」的「民主化」趨向嗎?
福山顯然不以為如此。川普對美式的「金權政治」提出的解決方案,實際上非常「個人化」:我是如此有錢的人,所以我不會藉由參政來謀取私利。這種奇妙的「賢能政治論」,台灣人並不陌生。每當連戰家族的人參選,不論選的是總統或台北市長,國民黨的宣傳機器就會在市民階層散佈功能等值的耳語:連家有錢啊,有事業啊,不會像那個暴發戶,只會撈錢,不會做事。
此外,川普例如禁止旋轉門現象等的主張,也是本末倒置、隔靴搔癢。如果說希拉蕊對企業政治獻金的問題保持了沉默,其實川普也是一樣。杜絕卸任官員和退休公務員進入相關企業部門的管道,可是卻對企業的政治獻金問題不聞不問,其中的政治奧妙,不言可喻。福山的這些論點,對天朝那些直達「天人合一」的「大一統」祕境,倡言「貴賤有別、階序有分的儒家政治哲學」的政治神學家,應該會不入法眼,不屑討論;可是,台灣的各路「平民政論家」,大概都會同意福山的論點。
天朝學人眼中的「歷史終結」
揪心在「超克(西方)現代」問題的天朝學人,不論是台灣的抑或是中國的,對福山版本的「歷史終結論」,始終是冷嘲熱諷。
典型的理由之一是:福山未曾真正搞懂柯傑夫的「政治哲學」。
按照天朝學人的詮釋,福山以為「後歷史」的人,就是生活在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無階級社會」的人;在這樣的社會中,高度的社會流動將使得人們普遍具有中產階級的自我認同,認為自己即使現在不是中產階級,未來也必然會是;乃至,即使自己不可能是中產階級,但自己的兒女,卻必然會是。
只不過,對柯傑夫,這種「歷史終結」之後的「後歷史人類」,將再也沒有為自我的存在、主張和地位而鬥爭的「高貴的自由理念」,而只能生活在「永恆的現在」,一種沉浸於「小確幸」的詭異「動物狀態」。人的生活將不再表現為對某種現狀的超越,將不再具備對某種未來可能性的慾念或規範性期待。「歷史的終結」,因此在哲學上就不可能不是「貴族心性」的終結,就不可能不是「人的動物化狀態」的開始。
於是,天朝學人們做出了「政治成熟」的「哲學結論」:福山筆下「歷史終結」後的人類,自以為獲得了「幸福」,但實際上獲得的卻僅是「滿足」,或者,更準確地說,動物式的「滿足」。福山沾沾自喜自由民主體制是人類歷史的「終點」,而卻不曾意識到:自由民主體制只會豢養出動物化的「末人」—故而,與其說自由民主體制是「世界歷史的終結」,不如說自由民主體制表徵著「西方文明的終結」。
對這些天朝學人,西方哲學為西方現代性的「自我滅絕」而寫下的「時代診斷書」,正是東方的「天下帝國」政治神學可以「超克」西方民族國家模式的最佳佐證。
天朝話語下的「民粹主義」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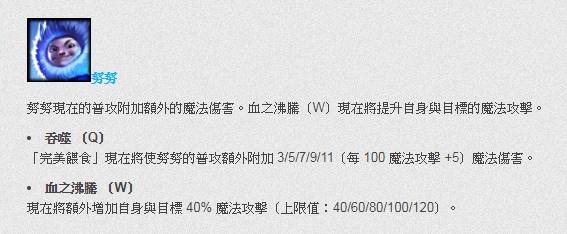
循著這種天朝主義話語的邏輯,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可說並不讓人意外,不過是體現了自由民主體制的極致荒謬:如果自由民主體制意味著對人的普遍而平等的「承認」,那麼,相對於儒家經典所登錄的聖王禮樂教化建制,自由民主體制也就必然意味著追求卓越身位的「貴族優越意識」(君子)的消失。換言之,自由民主體制,不過是不識「貴族優越意識」的「歷史末人」的政治統治形態。
對「以中國為原理」,崇尚「三代之治」,嚴格「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從大廳到臥房都處處講究「天人合一的修養功夫」的天朝學人,啟蒙主義下的「現代民主」,不啻「最可蔑視的小人為統治者的時代」,無非即為最遠離「君父的國度」的時代。是可忍,孰不可忍?
依據這種華夏的帝國政治神學,福山誤解了「民粹主義」問題的真正本質:自由民主體制不是因為「民粹主義」而陷入危機,而是強調大眾啟蒙,以普世人權與人民主權為核心原則的自由民主理念,原本自身即為「知性上的民粹主義」的產物。
因此,習近平的「七不講」是對的,「習近平核心」的成立也是對的。因為華夏帝國要化解自己的制度危機,第一步該做的就是對西方啟蒙主義思維內蘊的「知性上的民粹主義」給予政治神學形式的否定和「超克」,以「王有所成」的王權主義話語來取代「人民主權」的民主主義話語,重新回歸到「天下帝國與普世王權」兩相結合的古典儒教帝國神學。
總結地說:西方民主必然會造成「民粹主義」問題,這是西方啟蒙主義要以「民智」取代「王制」必然要付出的代價。川普現象,不是西方民主下的「病態」或「例外」,而恰為西方民主最真實的本來面目。
當福山嘆息著美國對世界不再是民主的象徵,天朝學人或許會竊笑:福山,你錯了!癥結不是美國不再是民主的象徵,而是民主不再是人類文明的象徵。川普的勝利,說明了「中國特色道路」在政治神學上的「優越性」,說明了世俗化的「大眾民粹主義」最終依然不是神顯的帝國權威的對手。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沒落,正昭告著世人:「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已經來臨!
從「民粹主義批判」到帝國神學
有論者已經指出:習近平的政治地位的變化,象徵著中國「由共和變成帝國」的演變歷程。有趣的是,習近平式的「王權主義的復權」,華夏版本的「共和變帝國」,恰好與川普等保守勢力取得美國政權,在時間上貼合。借用天朝主義文人的話語邏輯,或許可以這麼說:正好在華夏再度「帝國化」的歷史時刻,卻也見證了美國的「去帝國化」趨勢的抬頭。
而且,就在川普當選後沒多久,香港高等法院就在11月15日對「青年新政」梁頌恆及游蕙禎的「立法會議員宣誓司法覆核案」頒布判詞,指出梁游二人不願依照《基本法》第104條和《宣誓及聲明條例》宣誓,裁定宣誓無效,同時取消其議員資格。
在普世人權與民主理念退潮的當下,習近平式的「王權主義」,要以香港為芻狗,用實際的政治決斷,來確立中國對香港的「帝國式主權」是不可挑戰的。
這種前所未有的政治局勢,似乎一時之間讓一些台灣的本土派和民主派覺得受到了雙重夾擊。有人急切地反擊重新流行起來的「民粹主義批判」話語產業,為著將台灣民族主義,將台灣的民族國家建設與「民粹主義」問題切開,乃至衍生出對川普言行的辯護性言辭。
可是,這種對「民粹主義批判」的「再批判」,極有可能會徒勞無功。
這是因為,就如同前面的段落暗示的,台灣與中國流行的「民粹主義批判」話語產業,背後真實的意識形態原點,經常並不是對現代自由民主體制在原理上的堅持,反而是對現代自由民主體制在原理上的否定。
眾所周知,在全球化的情境下,古典的的民族國家方案的確是遭遇到了難題:全球性的跨界流動導致了對「他者」的親身體驗,同時也導致了突出認同差異的「承認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但有個附帶的現象,可能就尚未得到充分的注意:從這種全球化情境下的倫理難題,居然衍生出了對「帝國話語」的支持性立場。
按照這種「帝國轉向」的新話語,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終究是無從消解這種全球化情境下關於「承認政治」的衝突的;而唯一可能的解決之道,乃是從根本上棄絕過去一個世紀多居於文化霸權地位的民族國家方案與民族主義話語,而徹底回歸人類歷史中源遠流長的「帝國傳統」,以「世界大同」的「包容性的帝國原理」,來作為構建新世界秩序的基礎法則。
對天朝學人,他們或許也會同意福山的論斷:我們確實進入了一個「美國對抗世界」的新時代,但關於這個「世界」,它確切的內容乃是以華夏「天下帝國」為核心的權威資本主義國際聯盟。
一言以蔽之,天朝主義下的「民粹主義批判」,是與「復興帝國」的「帝國心性」和「帝國神學」有關的事情。如果不徹底領悟這點,是難以真正去解構「民粹主義批判」話語產業所建構的意識形態幻象的。
躲在「民粹主義批判」背後的中華型川普邏輯
為此,我們或許就必須對儒教帝國神學中的「禮教社會」觀念,具備一些必要的社會學認知。因為天朝主義下的「民粹主義批判」,背後總是預設了某種未曾明說的「禮教社會論」。
這種「禮教社會論」,當然首先是一種與「尊尊親親」的儒教倫理有關,與「華夏、夷狄」的「文明種姓」劃分有關的身份階序秩序,某種被華夏帝國儒教視為「自然社會」中的「自然秩序」的事物。
這種「身份階序的自然秩序」,乃是一種「作為整體規範的身份秩序」,而不僅是原初的家族秩序或宗族秩序的複製或再現而已。準確地說,經過儒教話語而再現的「家族秩序」,已經是一種作為制度化的規範模式的身份等級宰制構造,是不同的社會軸線中的宰制性身位的合成物與合成體。在這種「儒教版的承認政治」中,身份階序(身份服從關係)被認為是貫穿儒教帝國下各個制度領域的統攝性原理。
不過,以尊重先在的社會劃分為前提的「儒教式承認政治」,與現代社會的基本倫理情愫,終究是難以徹底契合的。
現代的承認政治,顯現了一種動態的、普遍的和多元的身份認同構造,這種身份認同的複雜性,已經不是古典的階序倫理足以恰當地處理;相反地,儒教式的階序倫理,還會到處與現代多元文化下最基本的道德規則—普遍平等與普遍承認的政治原理—發生衝突。基於這種「道德整合」或「社會整合」上的衝突來說,對儒教式階序倫理作為制度整合潤滑劑的作用,是大可存疑的。
「儒教式承認政治」與現代民主下的「承認政治」,終究是在原理上干戈不合的—這點,或許才是為何眾多的天朝學人,一方面批判川普的「民粹主義」,另方面其實對川普頗有好感的深層理由之一。對天朝學人,川普正好以他的實際作為闡釋了一個基本事實:現代的民主倫理,不是無堅不摧。或許,我們還該由此進一步看到另一個更為隱晦的疑情:每個天朝主義的「民粹主義批判」話語背後,其實可能都躲藏著一個「川普式的幽靈」。

【上報徵稿】
上報歡迎各界投書,來稿請寄editor@upmedia.mg,並請附上真實姓名、聯絡方式與職業身份簡介。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起底謝宜容!傳身家背景雄厚「善做公關」 先生和綠營高層有交情
- 一元特典!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釋出「零星票券」,11/24 採實名制一般販售
- 【世界棒球12強賽】滿足「2條件」台灣確定晉級4強 今晚是關鍵
- 先搶先贏!Ado 五月林口體育館演唱會採實名制入場,11/19 輸入「指定代碼」可優先預購
- 【內幕】T112步槍裝彈器採購案疑專利侵權 以色列向軍備局寄存證信函
- 王一博金雞獎典禮被抓包視線離不開趙麗穎 網揭兩人4年戀情無法曝光背後真相
- 勞動部涉職場霸凌不只謝宜容? 何佩珊:與輕生者中間還有2個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