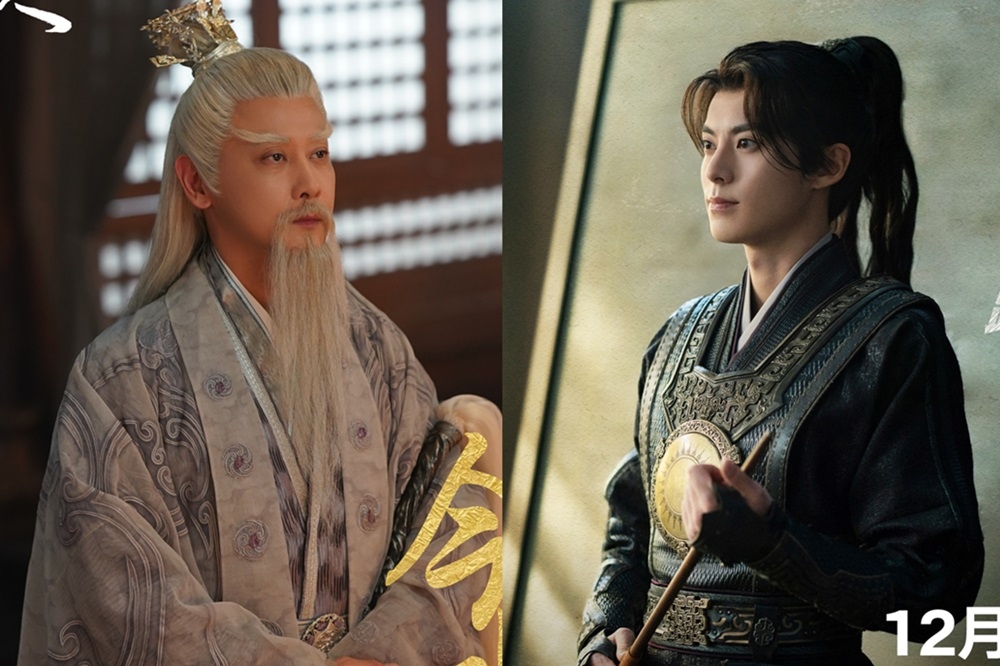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投書:台灣社會對柯文哲案應有的省思 2025-01-03 00:00
- 最新消息 柯文哲4人羈押理由曝光 柯曾說「要與妻孩出國躲紛擾」成關鍵主因 2025-01-02 23:53
- 最新消息 柯文哲再遭羈押 民眾黨籲賴清德「適可而止」 2025-01-02 23:22
- 最新消息 快訊/檢方三度聲押成功 柯文哲等4人裁定羈押禁見 2025-01-02 22:58
- 最新消息 內政部政黨審議會決議通過 聲請統促黨違憲解散 2025-01-02 22:28
- 最新消息 被緊咬是柯文哲分身 李文宗:大家都知道是蔡壁如 2025-01-02 22:12
- 最新消息 諷檢方下不了台「要關我就明講」 柯文哲:再加保就要賣房了 2025-01-02 22:00
- 最新消息 WSJ:中國已非美企「金礦」 難再幫北京說情 2025-01-02 21:50
- 最新消息 強烈冷氣團下周報到 低溫恐跌破10度、高山有望降雪 2025-01-02 21:34
- 最新消息 檢控他可能逃亡海外 沈慶京坐輪椅服藥:快80歲了怎麼跑 2025-01-02 21:08

我依照黎明的吩咐,早上十點半準時到達《夏潮》雜誌社。她電話中說,幫我約了三個很優秀的年輕朋友,也許可以做我的助選員。
「黎明來了嗎?」
「她在裡面。」龍嫂(這是我們最近對徐麗芬的稱呼)笑笑地說。我推開總編輯的房門。只見黎明趴在辦公桌上,似乎睡著了。但一聽我的腳步聲,她又立刻驚醒了,抬起臉來望著我,滿頭烏黑的長髮蓬鬆雜亂地覆蓋在額上。她雙手把頭髮往後攏了攏,露出一張沒有修飾的清麗的臉容,有點脫俗,有點倦怠的樣子。她舉起雙手略略向後仰了仰,美麗豐滿的前胸隔著衣服,玲瓏有緻地向前挺了挺。嘴裡還輕輕發出一聲慵懶的「呵──哦──」的呻吟。
我內心突然像觸了電似地,「轟!」地一聲輕響,情不自禁地喚了一聲,「黎!」
她微瞇了眼睛望我,伸出一隻手指擱在脣邊,做了一個噤聲的動作,默默地、癡癡地笑了。我覺得臉上熱熱的,有點暈眩。
「妳把自己搞得太累了。」我尷尬地嚅囁地說。
「沒辦法,我就是校長兼敲鐘兼掃地的命。」她笑笑地說,「台大政大那些學弟妹個個都是夜貓子,還好有小吳替我頂著,我才能趕最後一班車回花園新城。」
「那妳把早上的約改在下午不就好了嗎?」我恢復內心的平靜,淡淡地說。
「不行,人家下午還要上課。」黎明望了望手錶說,「他們應該要到了。」
「妳替我約了誰啊?」
「兩個政大研究生,一個讀政研所,一個新聞所。他們去年都在桃園幫羅智信打過選戰,很優秀。」黎明邊說邊向外面走去。「還有淡江的楊美君,你認識的。」她說。這時,外面好像有人進來了。只聽黎明的聲音說,「你們來了,先到我辦公室坐一下,陳宏也在裡面,你們先聊聊。」
我站起來,走向門口。只見兩個我覺得有點面熟的年輕人,站到龍嫂的辦公桌邊。「歡迎!歡迎!」龍嫂從廚房走出來,手上提了熱水壺迎上他們熱絡地說,「請裡面坐,我給你們泡茶。」
「請進來!」我伸手和他們握了握,笑著說,「我們是不是在政大校園見過?」
「是,我見過你兩次,一次聽你講張愛玲小說,一次聽你講鄉土文學。」那位身材略高,膚色白皙,長得相當清秀端正的年輕人,神情開朗地笑著說,「我叫胡飛鴻,古月胡,飛天的飛,江鳥鴻。政大政研所二年級。」
「我叫陳天祥,耳東陳,文天祥的天祥,政大新聞所二年級。」那個身材比較瘦小,膚色較黑,但臉色卻很光亮,尤其是隆起的額頭光亮而飽滿,有點矜持地微笑著。
「在政大文學研究社講張愛玲小說時,我還是政大中文研究所的學生。那時……」
「我們都在大學部二年級。」
「哈哈,我們緣分很深啊!」我笑著說,「但是講張愛玲小說時,對你們沒有印象。講鄉土文學時對你們兩個的印象就很深了。」
那天在政大樂群堂的演講也是文學研究社邀請的,他們要我講「鄉土文學」。那時,鄉土文學論戰還在報紙雜誌上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也就是說,國民黨全面掌握的報紙雜誌還不斷對我進行點名批判圍剿。我像一個被捆綁的人,遭遇一群有組織的暴力圍毆。起初,我以為這個邀請不會被校方批准。因為當初我沒獲得繼續在政大教書的原因,是特務單位認為我思想有問題,現在又被國民黨的黨政軍特的御用文人們公開點名批判,既說我是共產黨,又說我是台獨,連我寫反駁文章都不准登了,還會給我機會向大學生演講嗎?後來到底是什麼原因竟批准了這個演講會,我也沒去追問,反正可以演講了,我當然是要去的。那天,聽演講的同學是有一些針鋒相對的討論,我也明顯感覺到有些人是被動員的,有備而來的,因為那些人的提問內容,早都在報紙雜誌上由那些御用作家們講過了,例如,他們說:
「你所謂的鄉土文學,要反映社會內部的矛盾,要揭發社會的黑暗面,這與共產黨千方百計要挑撥分化我們社會的團結,破壞國家的穩定,不是完全如出一轍嗎?」
「你們說,鄉土文學是繼承日據時代台灣文學與五四時代中國新文學反帝國主義,反崇洋媚外,反殖民地經濟與買辦經濟的思想與精神,這不就是明顯的共產黨的統戰嗎?」
「你們所講的鄉土文學,強調的是台灣的鄉土,為什麼不強調中國的鄉土呢?過分強調台灣的鄉土,在政治上不就是台獨嗎?」
我記得當天對這些提問,我還沒回答時,已有其他同學也紛紛搶著發言了,其中,陳天祥和胡飛鴻所講的內容讓我印象最為深刻。
陳天祥講話的內容,大意是說:「我們不必去管共產黨要如何挑撥分化我們,我們該關心的是,我們社會內部是不是有矛盾?是不是有黑暗面?政府為了要發展工商業的國際競爭力,而壓低米價和工資,傷害了農民與工人的利益,這不是社會內部的矛盾嗎?由於政府的社會福利做得既不夠又不好,許多人吃不飽穿不暖,這是不是事實?為了吃飽穿暖,漁民冒著生命危險去炸魚,結果人被炸死炸傷了,這算不算是社會的黑暗面?既然社會內部有矛盾、有黑暗面,作家就有權利,也有責任去描寫、去反映,這有什麼不對?這與共產黨的挑撥分化有何關係?這些社會內部的矛盾與黑暗,並不是共產黨的挑撥分化才產生的。這問題的因果關係應該先搞清楚,不應該給作家戴紅帽子。亂戴紅帽子是會要人命的!像余光中在《聯合報》副刊發表〈狼來了〉,公然把鄉土文學指為共產黨的狼,太令我失望了,這不是一個知名的詩人應該有的風範與作風。因為,這會害人被抓去殺頭或坐牢……」
胡飛鴻說:「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代表政府的人要把鄉土文學和台獨掛在一起呢?從古今中外的文學歷史來考察,所有偉大的作品,幾乎都是以作家的生活與關注的土地為基礎的,這個土地就是我們今天所稱的鄉土。台灣的文學者以台灣的鄉土為基礎去從事寫作,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厚非的事。不以自己生活與關懷的台灣土地為基礎,而去寫什麼希臘羅馬的天空,去寫英國的西敏寺,像余光中那樣,這才是很奇怪荒唐的事。托爾斯泰是世界級的偉大作家,他所寫的俄國農民那麼生動鮮活,為什麼?因為那些農民生活在俄國的土地上,具有俄國的特色。魯迅的《阿Q正傳》所寫的阿Q,那麼生動,讓我們覺得心痛,為什麼?因為阿Q生活在中國那個時空背景下的中國土地上。你叫黃春明去寫中國東北的農民,可能嗎?叫王拓去寫挪威的漁民,可能嗎?叫白先勇去寫黃春明的宜蘭,一樣是不可能的。台灣的鄉土文學當然就是描寫台灣這個土地及人民的感情與生活的文學,怎麼可以把它和政治上的台獨掛在一起呢?這明顯是為了在政治上打擊異己,刻意把文學扭曲了。……」
「我記得你們,」我忍不住興奮地說,「年紀這麼輕,竟然有那麼精采的見解,實在太了不起了!」
「哈哈,阿宏這麼興奮,你們談得不錯吧。」黎明走進辦公室,頭髮挽在後腦梳成一個貴婦頭,臉容也經過淡淡的修飾整理了,除了原有的清麗脫俗,還顯得高貴雍容,容光煥發。
「我不但認識他們,我現在想起來了,我還在《夏潮》雜誌上讀過他們的文章,胡飛鴻寫鄉土文學的文章,我雖然忘記文章的名字了,但內容我還記得。陳天祥寫過幫羅智信助選的文章,〈選戰新兵,助選員的心聲〉,對不對?都寫得極好,真是後生可畏!」我興奮地說。
「你記性還不錯,他們是在《夏潮》雜誌寫過文章。」黎明對我嫣然一笑,說,「我已跟他們談過兩次了,也把你的《黨外的聲音》和《民眾的眼睛》都送給他們讀過了。他們也讀過你的短篇小說集《金水嬸》和《望君早歸》,也讀過你的文化評論《街巷鼓聲》,已算是你的知音了。」
「謝謝,謝謝,請多指教!」我說。
「鄭姊已經和我們很詳細地談過你,我們也很用心地讀了你的著作,對你的思想、文學和作為都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了解。但是,我們還有一個問題想聽你親自對我們說明,」陳天祥表情嚴肅地說,「以你目前在文學上的表現,如果你繼續寫作,一定會成為台灣文學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作家,但是,你現在卻要放棄文學,去參與選舉,為什麼?選舉的成敗不但不可知,而且還有可能被抓去坐牢。你為什麼會做這種選擇?」
「你們既然都已讀過我寫的書,我就不必再講得長篇大論了。簡單扼要地講,中華民國必須改革,已經不能再拖了!而文學的影響力太慢了,我等不及了!」我說,「難道還要再等三十年才能國會全面改選嗎?才能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和報禁嗎?……」
「但是,你難道不怕被捉去坐牢嗎?」
「坐牢嗎?參與選舉會坐牢嗎?這是憲法所保障的人民的權利,我不違法,不犯法,誰能捉我去坐牢?時代已經不一樣了,中壢事件發生那麼大的事,國民黨也沒捉人呀。……」
「阿宏,現在要請他們幫你做什麼事?就直接說了吧。」黎明說。
「我們可以發傳單、拜訪選民。」胡飛鴻笑著說。
「這,太大材小用了。」我說,「這樣吧,就請你們兩位幫我做兩件事,一是幫我組織訓練一批年輕助選員,除了上街發傳單拜訪選民之外,也要探訪民情做選戰資料蒐集和分析。第二,幫我負責所有選舉文宣,包括大字報看板、海報內容、傳單內容。還有,對外發布新聞等等。我相信,你們做的一定不會輸給林杰克和張富順。」
「組織訓練助選員的場地,台北可以在《夏潮》雜誌社,基隆可以在陳宏的選舉辦公室。」黎明說,「需要人力物力財力支援,《夏潮》會盡一切力量。」
「我在基隆招募了一些年輕人,程度都不高,國中或高中而已。」我說,「我們準備去海洋學院找些大學生,但還沒找到有效的管道。基隆比較保守,需要在台北找些人過去帶動才行。你們何時能跟我去基隆?有時間的話,下午就可以坐張文龍教授的車一起去。」
「下午我不行,我有課。」天祥說,「但明後天我可以找幾個新聞系的學弟妹一起去基隆,寫海報、大字報都沒問題。」
「下午我可以去。」飛鴻說,「我先去認識一下基隆的環境,說不定我可以在基隆住一段時間。」
「真的嗎?那太好了!」我興奮地說,「住的問題,我來設法。」
「你都不必上課了嗎?」黎明關心地問。
「研究所的學分我已修完,現在開始要寫論文了。」飛鴻說,「我已決定把這次選舉作為我論文的內容。我要以實際經驗為第一手資料寫成論文,這樣比較有意思。一般碩博士論文都是以別人的著作為研究對象,我不喜歡這樣。」
「有見識,這樣的論文才有原創性。」黎明豎起大拇指說,「你的論文一定會很精采。但是,在學的學生不能當正式助選員,這是《選罷法》的規定。」
「我知道,我查過《六法全書》。因此,我準備申請休學一年。」
「那,太感謝了!」我激動地說。
下午一點半,淡江文理學院英文系的老師王正平和他的學生楊美君一起來到《夏潮》雜誌社。
我和正平認識大約是在一九七四年吧,他剛從美國拿了一個英美文學碩士回來,在母校淡江文理學院謀了一個專任講師的教職。當時我也在政大中文系擔任兼任講師。那年屈中和大哥應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的邀請去訪問一年,他教的「中國小說選讀」便由我代理了。我和正平大概就在幾個文學界朋友替屈大哥餞行的餐會上認識的。我們年紀相當,志趣相投,後來又同為《夏潮》雜誌的固定成員,便常常互有往來了。他喜歡唱歌,又很好客,淡水山上的家,經常高朋滿座。我就是在他家認識楊美君的。
「美君,我大概也有半年以上沒聽妳唱歌了吧?妳在台視主持的節目,我一直還沒看過,」我有點歉疚地說,「改天請妳來基隆,唱給我們基隆的鄉親聽好嗎?〈少年中國〉和〈美麗島〉,讓他們開開眼界。妳唱的現代台灣民歌之好聽,之有內容,不是蓋的。」
「哈!談起這個,美君就要火大了。」正平笑著說,「剛才要來這裡的路上,美君才告訴我,台視公司節目部經理告訴她,今後在節目裡不准再唱〈少年中國〉和〈美麗島〉了,而且還要她多唱一些愛國歌曲、淨化歌曲,……」
「這是什麼意思?連〈少年中國〉和〈美麗島〉都不准唱?為什麼呢?這不也都是愛國歌曲和淨化歌曲嗎?」黎明說,「妳的節目開始時用〈少年中國〉,結束時用〈美麗島〉,我覺得很好啊,很溫馨、很有創意……」
「是啊,國民黨內就是有這麼神經病的人。我也這樣問他們,」美君聲音略見高亢,卻又很無奈地說,「節目部經理說,是上面交代的。為什麼這樣交代?他也不知道。後來我才聽說,是政戰系統的意見,說〈少年中國〉是統派,〈美麗島〉是獨派。我說〈美麗島〉歌頌台灣之美,對台灣充滿感恩。國民黨統治台灣,不就等於是在歌頌國民黨嗎?國民黨不是要反攻大陸統一中國嗎?〈少年中國〉歌頌中國的民族性,開朗勤奮,有什麼不對嗎?他們說,這是妳的解釋。但是,他們的解釋是什麼?他們又不說,真是他爹的!」美君忍不住爆出一句粗話,有點尷尬地微紅了臉,靦腆地說,「不好意思,在你們面前講粗話。」
「哈哈哈,講粗話算什麼?我們漁村長大的討海人,三句話裡至少有一句是粗話,那是我們的口頭禪,有時甚至表示親密,表示友誼,也會用三字經。」我哈哈大笑地說,「講粗話何必臉紅?在南仔寮不會講粗話才奇怪哩。」
美君長得不很高,但身材很豐滿。頭髮剪得短短的,只蓋住耳朵,卻露出白皙的頸脖子,顯得乾淨俐落。臉圓圓的,像個娃娃。雖然沒學過音樂,卻天生有副嘹亮悅耳的嗓子。熱情豪爽,大有巾幗之風。她是正平英美小說課上的學生,我曾在正平的邀約下,到他的課上講過中國傳統小說,又幾次在正平家與李雙澤、蔣勳、梁景峰和幾位學生一起喝酒聊天,高談闊論,開心歌唱,似乎每次都有見到美君。所以,這次我決定參選,就想到美君。以她的清新形象,電視台節目主持人身分,如果能來當我的助選員,那有多好!但是,她在電視台主持節目,是所有企圖在歌藝上一展抱負和才華的男女歌者,都求之不得的好位置。如果來幫黨外助選,國民黨一定不能容忍,台視公司不但會取消她的主持人合約,也一定會把她列入黑名單,從此不准她再上電視了。如此一來,豈不是就毀了她已經看好的歌藝前程了嗎?我對她既有那樣的期待,又有這樣的顧慮,所以就一直不敢向黎明或正平開這個口。沒想到,今天卻經由正平把她請來了。
「陳宏老師,你要參選,我百分之百支持。」她笑笑地說,「鄭姊私下找我談過,正平老師也和我談過,希望我能公開站出來替你助選。但是,鄭姊說,你擔心會影響我的前途,所以遲遲不敢開口。我現在要告訴你,我願意做你的正式助選員。不准我唱〈少年中國〉和〈美麗島〉的電視台,我絕不留戀!我寧可到你的政見會上把〈少年中國〉和〈美麗島〉唱給你的選民聽。」
「真的?」我興奮地跳起來,「謝謝妳!」我大聲說,「實在太好啦!太好啦!真的太棒啦!」
「我們下午就要去基隆,妳願意一起去嗎?」一直默默地坐在沙發上的胡飛鴻突然開口了,略帶著挑戰的口氣熱情地對正平和美君說。
「去基隆嗎?好呀!」美君爽快地說。
「對不起,還沒替你們介紹,」我指著胡飛鴻說,「這位是政大政研所的胡飛鴻同學,也跟妳一樣,願意到基隆做我的助選員。還有一位也是政大新聞所的同學,他剛剛有事先走了。你們都願意來幫我助選,實在太好了!」美君大方地伸手和胡飛鴻握了握,笑著說,「我們都下海了,成為陳宏集團的一分子了。以後要請你多多關照。」
「彼此彼此!」胡飛鴻也笑著說,「我很欣賞妳的豪爽大方,完全沒有一般女孩子那種扭捏作態的樣子。」
「謝謝!」美君說,「不嫌棄我太粗線條就好。」
連續二十天來,我們已經把各區的里長拜訪得差不多了。現在只剩下暖暖區有三個里,是集中在一起的眷村。我們聽從黨外前輩高明正的建議,放到最後再去拜訪。今天下午,我們就準備把暖暖區那幾個眷村的里一起拜訪完,再回到孝二路請大家來開個會。
「我願意和你們一起去拜訪眷村,晚上再與大家一起開會。」胡飛鴻說,「拜訪眷村要有心理準備,搞不好,可能還會有衝突。我們去年在桃園幫羅智信助選,我和林杰克就在眷村被那些老芋仔追著喊打哩。」
「是嗎?既然這樣,你怎麼還敢跟我去?」
「我就是有經驗了,所以也比較不怕了。」胡飛鴻笑笑地說,「其實這和狗追人有點相似。你越跑,狗就越追你,甚至還會撲上來咬你。但是,如果你不跑,還放膽慢慢走,他反而就不敢追你了。」
「哈哈哈,這個比喻有意思!」吳福成笑著說,「如果你們多幾個人去,人多勢眾,他們雖然不歡迎,大概也不敢對你們怎麼樣吧?」
「但是美君是女性,萬一怎麼樣,不好吧?」我說,「下午妳就不必跟我們去基隆,有龍哥、吳世傑、胡飛鴻和我,總共四個人也夠了。」
「不要!我要跟你們一起去!」美君笑笑地,好強地說,「我是女生,又是外省人,他們不會對我怎麼樣。」
「好吧!美君既然堅持要去,就讓她一起去吧!」正平笑著說,「讓她去見識見識也好。」
「美君很勇敢喔!」龍嫂點頭稱讚,笑著說,「我叫龍哥好好保護你。」
我們到達暖暖區已經是下午三點了。第一個眷村在碇內里,就在市立老人安養院後面,與第二眷村碇祥里緊鄰著,旁邊就是碇內菜市場。眷村的入口是一個鐵製的大門。龍哥把車開進去,立刻引來兩隻黑狗「汪!汪!汪!」地叫著追了過來。我們下車,找到蔡得勝里長的家。我輕輕按了一下電鈴,來開門的是位身材頗為高大,但背部卻已經有點駝了的大約六十幾歲的男人。
「請問蔡里長在嗎?」
「我就是,」他說,「有啥事?」濃重的外省口音。
「對不起,打攪你了。我姓陳,這是我的名片,請多指教。」
「要選舉啊?」他瞇著眼睛,把名片拿得遠遠的,又斜眼望了我一眼,「陳宏?沒聽過,」他說,「黨部還沒通知,你怎麼這麼早就活動了?」
「這是我最近出版的兩本書,也請你指教。」我恭謹地把書遞給他。
「民眾的眼睛,黨外的聲音,」他把書名念出聲來,又張大眼睛望我一眼,再把我的名片翻到背面,念出我的政見,「一、國會全面改選。二、總統由人民直選。三、廢除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四、解除戒嚴。」他雙眉緊皺,兩眼嚴厲地望著我,「你不是國民黨?」
「我不是國民黨,我是黨外!」
「這是你的政見?」他把我的名片拿在手上晃了晃。
「是,那是我的主要政見。」
「你竟敢提這種政見?」他突然大聲嚷嚷起來,「你根本就是共產黨。」
「蔡里長,你怎麼這樣講?」我心裡確實嚇了一跳,心想,這人怎麼這樣?「我不是共產黨,我是黨外,……」
「提這種政見,還不是共產黨?總統由你們直接來選?狗屁!還要解除戒嚴?這不是共產黨是什麼?……」
「老伴,老伴,幹啥這樣大聲嚷嚷!叫他們出去就好了,」一個身材矮小的老婦人巍巍顫顫地從內室走出來,「這麼多年輕人啊?你們坐,你們坐……」
「還請他們坐?坐個屁!這些共產黨……」
「蔡里長,你怎麼口口聲聲說我是共產黨?我在台灣土生土長,從小受國民黨教育,共產黨長成什麼樣我都沒見過,怎麼說我是共產黨呢?」我看他氣勢洶洶,雖然有點膽怯,但忍不住又有些怒氣了,便大聲說,「共產黨不是都在中國大陸嗎?國民黨統治台灣三十年,共產黨不是早就被消滅了嗎?台灣哪還有共產黨呢?難道你是在國共內戰時被共產黨打怕了,現在看到草繩就以為是蛇了嗎?請你鎮定一點好嗎?台灣早已沒有共產黨了啦,你不必害怕!」
「這位小哥講的對,台灣哪會有共產黨?老伴……」
「噯──呀!妳不要囉嗦!」蔡里長氣急敗壞地說,「妳不懂啦!這個混蛋寫這種書,什麼黨外的聲音,印這種名片,說要解除戒嚴,要總統民選,這不是共產黨是什麼?」
「老蔡,老蔡,怎麼回事啊?剛睡醒午覺就這麼大聲嚷嚷,幹什麼呢?」門口突然出現三四個老人在門外探了探,「家裡怎麼這麼多人?」率先走進來的老人有點威儀,後面跟了兩個和蔡里長年齡相仿的老人。
「你們來得正好,你們來看看,來看看!這個傢伙寫的這個是什麼書?還有這名片背後寫的什麼?這還不是共產黨嗎?肏他媽|的!共產黨的惡毒殘酷,我們還吃不夠嗎?你們看看,你們看看!」蔡里長把兩本書和一張名片遞給那個有點威儀的老人,氣急敗壞地說。
「噯呀,輔導長,老馬,老林,你們坐,你們坐!」蔡里長的老婆巍巍顫顫站起來,指著那些椅子說。
「黨外的聲音,民眾的眼睛,」那個有點威儀的老人念了書名,又抬眼望望我,冷冷地問,「這是你寫的書?」
我點頭說,「是!請指教!」
「這幾個……」
「都是我的朋友,台大物理系張教授,台大經濟系吳先生,政大政研所胡先生,台視節目主持人楊小姐。」
「原來都是讀書人,都是高級知識分子。」那人把書遞給另外兩人,拿起我的名片仔細看了看,「書的內容我還不知道,但名片的政見,很有問題啊!」他望著我搖搖頭,嚴厲地說,「這些是會坐牢,會殺頭的,年輕人!」
「我又不違法,不犯法,坐什麼牢?殺什麼頭?笑話!」眼看這些人這種蠻橫霸道不講理的樣子,我實在忍不住氣了,便提高了聲音說,「這些政見我都寫成文章在雜誌上發表過了,也沒事呀!怎麼各位用這種態度對我們呢?不是罵我共產黨,就是威脅我會坐牢,會殺頭!這是民主時代、民主社會欸,不是像你們以前在大陸……」
「你很大膽哦,什麼黨外的聲音?台灣有什麼黨外?黨外還有聲音?放屁!」一個矮壯的剃了光頭,也是六十來歲的老人說,「輔導長,我看把他們趕走,不准這種人來騷擾我們的安寧……」
「什麼趕走?不行!這些人根本就是匪諜。要把他們捉起來,法辦!」蔡里長大聲說。
「你們講不講理啊?我們是好意來拜訪里長,你們不歡迎就算了,還報警捉人啊?笑話!我們犯什麼法啦?莫名其妙!」龍哥突然憤怒地大聲說,「就是你們這些人,才把好好的大陸給搞丟了,你們不知反省,還在這裡欺負台灣人嗎?中華民國又不是只有你們這些人,還有我們這些台灣老百姓,人數比你們多得多,你們敢這麼欺負人嗎?」
「肏你媽!就欺負你,怎樣?你這個共產黨,老子揍你!」那個蔡里長突然欺向龍哥,我反射性地立刻將他攔住,同時用力推了他一下。他向後仰了仰,退了兩步,立刻又向前跨步,抓住我的衣領,我立刻揚起雙手向外一撥,腦門充血似地轟轟響著,所有的膽怯緊張害怕突然都消失了,只覺得全身鼓滿了怒氣,像一隻被威嚇的貓那樣,全身戰鬥式地弓起來。
「怎麼?要打架嗎?我肏你媽!」蔡里長叫嚷著,又作勢向我欺近。吳世傑立刻穿身切入,把我們隔開了。
「蔡里長,有話用講的,怎麼動手動腳呢?」吳世傑雙手護胸沉靜地說。
「好啦好啦,各位叔叔伯伯,給我們晚輩一點好榜樣好不好?」美君突然以嘹亮的聲音大聲說,「我是外省子弟,從小也在眷村長大,不是台獨,更不是共產黨,諸位伯伯叔叔的心情我了解。但是,現在是民主社會,參與選舉是人民的權利,……」
「好啊,妳這女娃兒,既是眷村子弟,怎麼跟這些人混在一起呢?妳這不是吃裡扒外嗎?妳父母怎麼教妳的?」蔡里長突然一個箭步欺向楊美君。這同時,站在旁邊的胡飛鴻立刻橫身擋住蔡里長,美君似乎受到了驚嚇,猛地向後退步,突然,「狂郎!」一聲,撞倒了茶几上的熱水瓶,立刻把碎玻璃和熱水灑滿了一地。
「你們,太過分了!到人家客廳來撒野啊?」那輔導長大聲怒責。
「美君,龍哥,我們都出去。」我也大聲說。同時退出蔡家的客廳。胡飛鴻和吳世傑殿後,背對大門,也一步一步慢慢退了出來。
這時,門外已經聚集了好些人了。
「蔡里長,這些人幹什麼的?來鬧事啊?」
「這幾個,肏他媽的,共產黨,把他們抓起來。」
門外聚集的人,真的就有一個跨著大步要欺過來的樣子。我頓了一下,大喝一聲,「退下!」吳世傑立刻站到我面前,雙手環抱在胸前望著那人。
「我們好意來拜訪里長,送書給他,請他指教。他卻一再罵我共產黨,還罵我娘!怎樣?你們這裡沒王法嗎?還以為是在大陸時代,可以任你們胡作非為嗎?我們又不違法不犯法,還捉我去派出所?好啊!我這就去派出所報案,告你毀謗,公然侮辱!」我大聲嚷嚷地說,「台灣是有法治的,姓蔡的,我去法院告死你這個老渾蛋!」
龍哥早已坐到車裡發動引擎了,我護著美君先讓她上車,等胡飛鴻和吳世傑都上車了,我才坐到前座龍哥的旁邊。原在里長家門口的人,突然有人把寶特瓶紙杯往車上丟過來。龍哥踩了油門,把車馳向大門。有幾個比較年輕的人,這才向我們的座車追過來。「不要理他們!」龍哥微微加速,車子立刻駛離了眷村。
「哈哈,眷村的老芋仔原來是這樣子的。」吳世傑不論遇到什麼事,總是都那麼笑笑地說,
「膽子小一點,真會被嚇住了。」
「真的!嚇死人了!我還以為會被打哩。」美君有點驚魂未定地拍拍胸口,接著又笑笑地對胡飛鴻說,「還好有你替我擋著,不然,那個里長真的要打我的樣子,嚇死人了!」
「他不敢啦!他只是嚇唬你。」胡飛鴻笑笑地說,「像那隻狗,不是追著車子吠嗎?我們停車下車,不理牠,牠不是就夾著尾巴跑了嗎?」
「難怪台灣會有所謂的省籍情結,像我這樣的人都受不了這些老芋仔了。」龍哥兩眼望著前方,面無表情地說,「太不講道理了,還滿嘴髒話!」
「後面還有兩個里的里長也都在眷村哩,你們說,還要去拜訪嗎?」
「我看,不必了。眷村的票不會給我們啦。」胡飛鴻說,「去年我們去幫羅智信助選,眷村的反應也是這樣,林杰克還被他們用石頭打哩。」
「那──去派出所吧,」我說,「先報警,以防萬一。」─
「要報警嗎?」胡飛鴻說,「我們要選舉,為這種事報警,不好吧?這些人惡人先告狀,講不清楚的。」
「就是要防他惡人先告狀,所以才要去派出所報案呀。」我說。
「龍哥,你認為呢?」吳世傑笑笑地說,「那個里長雖然大吼大叫,過了大概就沒事了。但是,他們叫輔導長的那個,大概會向上報也說不定。」
「我們又不是國民黨,他向上報也不能對我們怎麼樣,不必理他!」龍哥說,「我較想知道的是,他罵陳宏是共產黨,如果報紙登出來,對一般選民會有什麼影響?」
「張教授提這問題有意思,我就擔心這個。」胡飛鴻說,「國民黨長期實施反共仇共教育,說萬惡共匪禍國殃民,讓我們聽了一輩子。一般人如果聽到有人罵陳宏是共產黨,是會對陳宏害怕?厭惡?仇視?還是會對陳宏同情、抱不平?這確實值得研究。」
「如果相信陳宏是共產黨,就會對陳宏害怕、厭惡、仇視。如果不相信他是共產黨,就會同情他,替他抱不平。」美君說,「所以,要讓選民認為那個蔡里長講的根本是胡說八道,這樣選民就會支持陳宏了。」
「美君講的有道理。但是要如何讓選民認為蔡里長講的是胡說八道呢?報紙都是國民黨的,如果報紙去訪問蔡里長,他說陳宏是共產黨,我們能去哪裡辯解呢?怎麼破他這招呢?這要想一想。」龍哥說。
「去年縣市長選舉,國民黨是不是也說羅智信是共產黨呢?他怎麼對付這種惡毒的謠言?」吳世傑望著胡飛鴻問。
「國民黨確實說過羅智信是共產黨,但桃園人都知道羅智信是國民黨員,被開除黨籍後,還發表一張文宣,題目是『願此心永永遠遠成為國民黨員』,在桃園縣廣為散發。羅智信當選省議員時也是國民黨提名的,現在因為他不聽話,就說他是共產黨,桃園人不相信。」胡飛鴻笑笑地說。
「國民黨到時候一定會用這招對付陳宏。把你抹紅,讓一些人仇視你、怕你。這招很惡毒,要使你落選,這招是有效的。」龍哥擔憂地說,「因為你跟羅智信不一樣。」
「所以,龍哥,你的意思還是不要去報案比較好,免得事情鬧大了,讓報紙登出來,對我們反而不利。是不是這樣?」我沉吟了一下,說,「龍哥的考慮也有道理,這問題真的要好好研究一下破解的辦法。國民黨幾十年反共教育,已讓人民都有恐共仇共的心理。這點不破解,選舉時還真不好說明。我們又沒報紙沒電視……」
傍晚在孝二路辦公室,由黑常、李通達和海洋學院的葉晉玉邀來的朋友總共有二十五位。
葉晉玉是我太太淑貞的表弟,廣東客家人,從小跟著他父母在我岳父母家進進出出,所以跟淑貞娘家的兄弟姊妹都很親近。他大概是從淑貞那裡聽說我要參選的消息,就親自跑來孝二路辦公室自我介紹,說他要來替姊夫助選。他說他在《中國時報》副刊上讀過我的文章,也有看到鄉土文學論戰的一些新聞和文章,對我很佩服,所以就大力在學校幫我招兵買馬,找了幾個熱心的同學和我談過兩次話,也在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時替我在熱鬧的街道貼過海報。今天晚上找大家來開會,就是要去張貼慶祝媽祖誕辰的海報。
貼海報都是兩人一組,一輛自備的機車,一桶漿糊,一支刷子,幾十張海報。這事的總負責人是黑常,海報送到辦公室後,當天晚上一定要張貼完畢。
「宏舅仔,效果不錯喔!」黑常在上次貼完慶祝青年節的海報後,一早見到我,立刻喜形於色地說,「我透早在嵌仔頂賣魚,就有人在問了,陳宏是誰?伊是做啥的?我故意反問他們,你為啥問這?問這做啥?他們說,嵌仔頂的電線桿、走廊的柱仔腳,都有貼海報,貼的人就叫陳宏。」
「姊夫,海洋學院也有人在討論,說有一個作家叫陳宏要出來競選,他是南仔寮的人。」葉晉玉身材有點矮小,但在學校滿活躍,對人很熱心,講起話來嘰嘰呱呱,做事也很俐落,是那種短小精悍型的人。
「人手差不多到齊了,就剩牛頭要帶來的幾個人,說已經在路上了。」黑常一看到我進門,立刻迎上來說,一面和張文龍、吳世傑打招呼,一面主動去和胡飛鴻、楊美君握手自我介紹,「我叫做黑常,南仔寮人,陳宏是我阿舅,多謝你們來幫忙。」
「大家辛苦了,多謝大家!我先來介紹兩位朋友跟大家認識,」我用力拍拍手,大聲向在場的人說,「這位帥哥叫胡飛鴻,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的學生,去年在桃園替羅智信做助選員……」大家突然不約而同地鼓掌,大聲說,「中壢事件,讚啦!」
「這位小姐叫楊美君,淡江英文系高材生,台視公司音樂節目《跳躍音符》的主持人……」
「啊啊啊,我很愛聽妳唱〈美麗島〉,……」大家紛紛鼓掌,意外地看到電視明星似地興奮起來。
「宏叔仔,尹攏是來替你助選的嗎?」那位杜伯齡的姪仔問。
「是啊,他們都要登記做我的正式助選員。」我笑著說,「到時,他們都會上台替我助講,美君也會上台教大家唱歌,唱〈美麗島〉、〈望春風〉、〈補破網〉、〈丟丟銅〉,還有一首〈少年中國〉。」
「好啊!那麼現在就先唱一首給大家聽聽,鼓勵一下嘛!」李再生突然從門口那邊冒出來,大聲說:「我們這些兄弟等一下就要出去貼海報了,很辛苦呢,先唱一首歌把熱情鼓舞起來。」
「牛頭,別再亂彈了啦!貼海報有什麼辛苦?我又不是沒貼過,」黑常站起來說,「要聽楊小姐唱歌,直接講就好了,還講東講西,找什麼理由嘛?」
「你上次貼海報沒遇到巡邏的警察,我在愛三路夜市就遇到,差一點沒跟那兩個警察打架。」李再生瞪著兩隻牛眼虎虎地說,「幹伊娘哩,說叫我不可亂貼。我說,我沒亂貼啊!我貼得平平穩穩,怎麼叫亂貼?伊講,就是不准你四處隨便貼啦。我講,貼電線桿不行嗎?貼柱仔腳不行嗎?令爸覅睬伊,機車騎了就跑了,管伊去死!我總共遇到三次,另外兩次我車一騎就閃人了。」
「好好好,大家很辛苦,我就來唱首歌慰勞大家好啦。」美君大方地說,「但我沒帶樂器,就用清唱的囉。」
「好,就唱那首〈美麗島〉,」有人帶頭鼓掌大聲說,其他人也都紛紛鼓掌附和。
「那就唱〈美麗島〉吧。」美君輕輕咳了一下,清了清喉嚨,雙手互握放在胸前,以充滿溫暖的感恩的深情的聲音,唱著: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複地叮嚀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複地叮嚀 篳路藍縷 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篳路藍縷 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美君輕軟的溫柔的聲音,輕聲地緩緩地結束了她的歌唱。再緩緩地彎腰向大家深深一鞠躬。
「好欸,好聽欸,」一陣宏亮的粗壯的叫好聲,伴隨一陣如雷的掌聲,「劈劈啪啪!」地響起來。
「好!各位兄弟,楊小姐的歌聲溫暖了鼓舞了我們的心,現在便當也來了,我們也要填飽肚子,就出發去貼海報了。」黑常大聲說。
大約傍晚七點多,窗外已經幾乎全黑了。一大夥人,兩人一組,紛紛騎上機車,提了漿糊刷子和標語海報出發了。辦公室只剩下黑常、李通達、葉普玉、胡飛鴻、吳世傑、楊美君和龍哥和我了。
我把今天去暖暖區拜訪眷村里長的經過向大家作了報告,也提出龍哥提到的,萬一被國民黨抹紅成為共產黨,要如何破解?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談了一會兒,似乎也沒什麼定見。我內心覺得有許多事情,千頭萬緒地糾纏在一起。但我每天都在拜訪、拜訪,根本沒時間、也沒心情去整理這些千頭萬緒的事。我必須要儘快找個能替我總攬全局的人。作為候選人,我不能成為「校長兼撞鐘,甚至兼掃地的人」。但誰有能力又有意願替我總攬全局呢?
我想到高明正,明正仙的年齡其實沒有很大,但他出道早,不到三十歲就當了林番王市長的機要祕書。而他,確實也聰明能幹,辦事有效率、有紀律。輔佐過番王仙競選連任,也輔佐過番王仙的兒子參與市長補選,他對選舉是有充分經驗的。但是,雖然已見過他幾次面了,他卻只肯暗中協助。
「坦白說,我是被國民黨特務盯死的人,我做的又是旅館生意,營業執照的發照權在人家手裡,雖然我們做得非常乾淨,根本不敢做一點點與黑的色情的有關的事。但是,他如果要隨便栽我一個罪名也很容易,我就吃不消了。孩子都還小,一個剛讀大學,一個讀高中。旅館生意萬一不能做,我全家就要喝西北風了。」他說。
既然這樣,我怎麼能勉強他?
我也想過龍哥,基隆人,大學教授,思慮清晰,條理分明,做事又仔細認真,行政能力一流。但我不敢開口。因為,直覺上,他的學術地位與身分,和選舉時需要應付周旋的人,太不搭調了。而且,大學教職很容易被國民黨搞掉,因為聘書在校長手中,而校長敢不聽國民黨的嗎?
我必須找一個對基隆熟悉,又能全心全意,每天二十四小時耗在選舉上,又有多方面才幹和能力的人,我能到哪裡去找呢?
我帶著這樣的煩惱回到木柵忠順街的家,已經超過晚上十一點了。母親、淑貞和兩個孩子都睡了。我輕躡著手腳,先到母親的臥室,站在床前替她把毯子向胸前拉了拉。然後走進我們的臥室,兒子睡在裡面靠牆的位置,女兒睡中間,淑貞則睡在最外側。我似乎已有很久沒和他們一起晚餐、一起在睡前聊天了。我內心突然感到一陣巨大的失落和寂寞。
我這樣一頭栽進選舉裡,果真是對的嗎?值得嗎?
我內心閃過這樣的疑惑。帶著歉疚的心情,輕手輕腳退出臥室,走進書房。等到洗完澡後,坐到書桌前,這份疑惑和不安的情緒仍然在心裡繚繞,久久不去。
我習慣性地拿出菸斗,塞了菸絲。這時,書房的門卻輕輕被推開了,燈也被關了,一個柔軟的溫暖的身體從後面把我抱住了。我轉身,把她摟進懷裡。窗外淡淡的街燈映進書房,把我們緊貼在一起的身影拉長了,模糊地映在牆上。
那晚,我作了一個美麗的夢。
夢見我陪著母親,牽了淑貞的手坐在沙灘上,兩個孩子在我童年的南仔寮故鄉的沙灘上奔跑跳躍。
金黃色的沙灘在夏末的初秋的黃昏的夕陽下一閃一閃地發著亮光。風微微吹著,夕陽的餘溫把沙灘曬得很溫暖、很舒服。海浪輕輕拍打著沙灘,發出「嘩——哬啦——,嘩——哬啦——」的聲音,細膩纏綿,像母親輕撫著孩子的背唱著兒歌的歌聲,也像母親對孩子的呼喚,「回家啦!回家啦!」
一艘漁船寂靜無聲地駛向大海,船尾拉曳出一條長長綿綿的水痕。天上白雲一片片飛著,幾隻海鷗在空中展翅飛翔盤旋。
兒子站在沙灘上,面向大海,手指向遠遠的天邊,回首對我大聲問:「爸爸,那隻船要開去哪裡呀?……它一直開一直開,開到大海和天連接的地方,那是哪裡啊?」
女兒指著天上的海鷗大聲嚷嚷,「媽媽,妳看,鳥鳥,鳥鳥……」

※本文摘自《吶喊》(王拓三本遺作之一,印刻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