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謝宜容起碼幹掉賴清德半壁江山 2024-11-22 00:02
- 最新消息 投書:立院惡鬥 只會讓更多科技人企業人不敢投身政壇 2024-11-22 00:00
- 最新消息 勞動部稱謝宜容失聯明天不出面 吳母淚控:霸凌太過分、太惡毒 2024-11-21 22:05
- 最新消息 俄烏戰況恐升級 烏克蘭是否有能力攔截ICBM 2024-11-21 21:50
- 最新消息 明後兩天各地氣溫回升 北部、東北部18到23度濕涼舒爽 2024-11-21 21:45
- 最新消息 劍橋詞典2024年度代表字出爐 「manifest」反映人們追求身心健康趨勢 2024-11-21 21:43
- 最新消息 為了9萬元勒斃馬國女大生 陳柏諺一審判賠父母逾638萬元 2024-11-21 21:32
- 最新消息 觸犯戰爭罪、違反人道法 ICC對納坦雅胡、哈瑪斯領導層發出逮捕令 2024-11-21 20:47
- 最新消息 【世棒四強賽】「CT AMAZE」自費飛東京應援 推掉台灣活動損失近10萬 2024-11-21 20:45
- 最新消息 蔡英文抵達加拿大 感謝台灣鄉親熱情接機 2024-11-21 20:37

導演趙德胤的大哥想改變家族命運,在他年幼時便到緬甸從事採礦工作,為記述這段家庭故事,趙德胤深入緬甸拍攝當地採礦實況,完成了《翡翠之城》這部紀錄片。(翡翠之城劇照)
錯過台北電影節,我是在公共電視的紀錄觀點上看趙德胤的《挖玉石的人》。凌晨一點的重播,無燈客廳,液晶螢幕開著卻彷彿關閉—工人摸黑挖玉石,躲避查緝,為了保生,奇異的是,這反讓他們宛如鬼魅。工人的行徑逸軌於常人的知覺,整部紀錄片有光亮祭祀音聲吃食甚至災難,我的腦海卻只一片無盡闇黑。闐闇與徒勞相扣,濃縮著玉石場裡勞動者的一生。恍惚裡,直想叫電視裡的遊魂們別再挖掘,但趙德胤用一事故作為終局,慘忍的。
片裡趙德胤不特別擘出區塊探討龐大的結構問題,諸如毒品氾濫、軍人勒索、自然破壞。「生」字底下,結構會被真實的人化為淡薄的背景。趙德胤懂得,因而將壓制的結構散亂在日常裡。捨去煽情的敘事,樸實觀照玉石場裡的一個一個人,看人如何活。這樣的視角,使「家常便飯」四字成為雙關—那不只是《挖玉石的人》裡,軍人追捕或死亡的自嘲語彙,而更蛻變為具反射意義的銀針一根。這根銀針日後穿過趙德胤兄長長年不歸的敘事支線,在趙德胤對兄長的空白記憶與諸多疑問之上,繡成另一紀錄片《翡翠之城》。
《翡翠之城》的行銷,側重於透過追索失聯多年大哥的秘密而達成和解的家族故事自我揭露。但在看過之後,我以為趙德胤所做仍是觀看與探問—如果紀錄片具備新聞工具的批判本質,分析前仍須有足夠豐厚的敘事存在,才有層層顛覆與其後身份置換的可能。站在《挖玉石的人》的勞動描繪基礎上,趙德胤於《翡翠之城》裡探究幻夢—
背景依舊是從2011年緬甸武裝衝突以來,宛如化外之地的克欽邦的帕敢玉石場。這裏被軍方高層、毒梟和權貴企業掌控,一無所有的哥哥為什麼想著回去?趙德胤的旁白像私密日記一一揭露,觀眾在喃喃獨白與趙德胤大哥始終偏離鏡頭中央的細瑣回應,窺見人與人間生疏距離的產生與剝削由何而來。
我以為選擇大哥做為觀看標的有其深意。無論十多年前的更早或翁山蘇姬執政的現在,趙德胤的大哥始終是在戰亂縫隙苟且偷生的挖玉工人。趙德胤大哥的形象鞏固時間的座標,讓採石場的工人們得以反映當代緬甸的切片:一位從未有過採礦經驗的農夫,握著手機通話,苦難不得張揚,和妻子討論電腦課程的培訓經費,面有難色,羞辱感在農夫的臉上浮現。人在前現代的生活場域償還全球化的經濟壓榨,轉型是什麼?民主是什麼?而那是否僅是「國家」、「政治」、「路線」的問題?
趙德胤將探問與戳刺幽微埋在運鏡裡。當攝影視角拉廣,全幅照出帕敢玉石場,很難不聯想攝影師薩爾加多在1986年記錄的巴西礦工。禿山金礦裡,工人攜帶著鏟子攀爬狹窄的梯子,若近看,觀者會為其遭受折磨的苦痕動容,但當鏡頭拉遠,觀者會悚然意識:景框之內,上天下地,皆無去處。
「他們的身分是奴隸,但並沒有任何一個人真的是奴隸。是財富使他們為奴,這是充滿奴性的層面,礦工分到的袋子或許一無所有,或許擁有一公斤黃金,在那刻,靈魂的自由危在旦夕,一旦接觸到黃金就永遠無法離開。」薩爾加多將巴西礦工的景狀描繪為煉獄,但煉獄的意義不止肉身受桎梏:「當我走到那個巨大坑洞邊緣,那一瞬間,人類的歷史在我面前展開, 人類建造金字塔,巴別塔和所羅門王的寶藏。」薩爾加多的慨嘆和片中趙德胤大哥所言,跨越時間,遙遙呼應:「這個洞子,你媽的,前仆後繼多少人幹,就是夢想挖到一顆好玉,究竟這顆玉石在哪兒?」、「人就是為了一個夢,將山挖成谷,將谷挖成山⋯⋯」
幻夢如毒。毒品創造遁逃的空間,讓人以為與腐敗仍有遙遠的距離。我由此推測趙德胤為何安排大哥吸食鴉片的畫面,以及仍在《翡翠之城》置入坍塌的事故。土方裡有屍,人卻不只是急於營救,更多旁觀,因危機與麻木已成日常。若真如此,觀看本身是否還具備召喚的可能?而幸運得以脫逃於那荒涼日常的倖存者,是否可以滿足止於旁觀?
趙德胤剪入大哥和礦工朋友設計的吸毒場景,同時讓大哥譏諷評論:「你們拍的電影《冰毒》太不像。」那一刻,電影院裡所有人都笑了出來,空氣的共振瞬間讓觀看不止於瀏覽再現,而是藉以翻轉、詮釋另種可能。片尾字幕cast出現「飾演」二字,一秒成為刺點,那一刻,才終於流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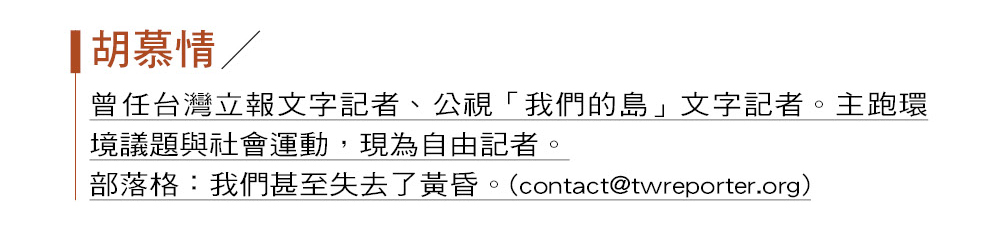
【上報徵稿】
上報歡迎各界投書,來稿請寄editor@upmedia.mg,並請附上真實姓名、聯絡方式與職業身份簡介。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起底謝宜容!傳身家背景雄厚「善做公關」 先生和綠營高層有交情
- 一元特典!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釋出「零星票券」,11/24 採實名制一般販售
- 【世界棒球12強賽】滿足「2條件」台灣確定晉級4強 今晚是關鍵
- 先搶先贏!Ado 五月林口體育館演唱會採實名制入場,11/19 輸入「指定代碼」可優先預購
- 【內幕】T112步槍裝彈器採購案疑專利侵權 以色列向軍備局寄存證信函
- 王一博金雞獎典禮被抓包視線離不開趙麗穎 網揭兩人4年戀情無法曝光背後真相
- 勞動部涉職場霸凌不只謝宜容? 何佩珊:與輕生者中間還有2個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