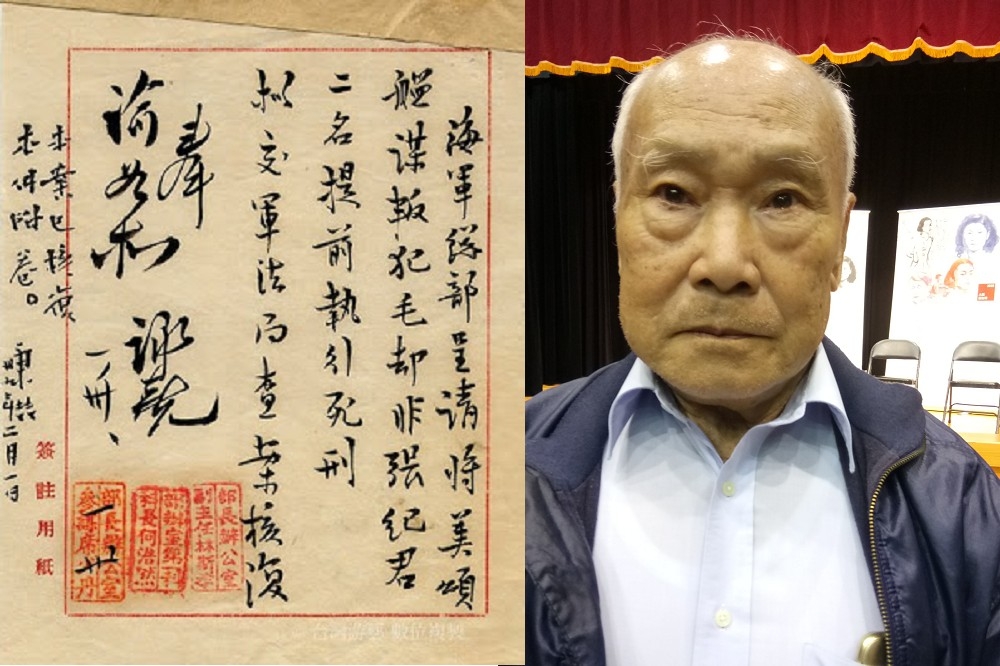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Angelababy新劇虐戀宋威龍接檔王鶴棣《大奉打更人》 瘋馬秀遭封殺後宣告全面復出 2025-01-15 12:15
- 最新消息 TikTok在美大限將至 逾50萬用戶湧入「小紅書」恐觸北京禁忌 2025-01-15 12:00
- 最新消息 侯明昊《異人之下》第二季預告曝光 來自台灣的「她」演暗黑超能力少女全網驚艷 2025-01-15 11:58
- 最新消息 【TPOC民調】賴清德滿意度52.9%過半 民眾黨支持者最「賭爛」 2025-01-15 11:45
- 最新消息 麥當勞持續炎上!美樂蒂聯名突喊停 傳三麗鷗接獲抗議急踩煞車 2025-01-15 11:36
- 最新消息 逆轉川普1.0政策 拜登將古巴移出資助恐怖主義國家名單 2025-01-15 11:28
- 最新消息 《永夜星河》丁禹兮爆紅微博發文被起底 他「這句話」疑酸虞書欣引爆雙方粉絲戰火 2025-01-15 11:12
- 最新消息 川普就職典禮動用2.5萬人維安 眾議院「順他意」宣布取消降半旗 2025-01-15 11:07
- 最新消息 地下電台始祖、台灣「名嘴祖師爺」徐明正過世 曾大酸民進黨:變民金黨 2025-01-15 11:03
- 最新消息 搶購蛋黃酥、鳳梨酥春節禮盒!陳耀訓、不二坊、佳德糕餅過年營業時間一次看 小潘蛋糕坊漲價日期曝光 2025-01-15 11:00

平行世界是存在的,世事不只有一個出口,寬恕自己與否,比後悔、渴望他人的寬恕更重要。(《一一》劇照/圖片取自時光網)
2019年終了的時候,很多朋友都交出自己的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電影榜單,我也列了一個很有私心的,僅限於華語片。包括這十部:《夏宮》《刺客聶隱娘》《鬼子來了》《麥兜菠蘿油王子》《黃金時代》《一代宗師》《站台》《大象席地而坐》《立春》《大佛普拉斯》,排名有先後,純屬個人品味沒有太考慮電影史。
然而朋友們還是很大意見,一種是強烈抗議《黃金時代》名列前五的,一種是強烈抗議沒有楊德昌導演遺作《一一》的,許多人都把它名列第一。前者見仁見智,不必解釋,而且有著我對蕭紅的情結在。後者我也納悶,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可是我的百年華語片的第一名,重複看過多遍,所謂大歷史在小歷史里的隱雷悸動,充盈在每一個細節里,那是一部如神物在呼吸一樣的傑作;那為什麼導演自己非常看重的《一一》我卻並沒那麼在意呢?
因為我看《一一》的時候,二十年前,還自詡是一個少年,完全不能共情於吳念真飾演的商人南峻的中年況味,以為自己仍是那個憤世的殺人者小四。記得2007年7月1日在街上,突然看見露天螢幕新聞播報楊德昌去世的消息,心中震動,也是視之為小四與少年的自己之死,幾天後寫了一首詩《消息》,副標題是「寫給小四、楊德昌」。裡面有這樣的句子,可見我等決絕:
當我在幽暗的浴室里沐浴的時候/我常常想起你;/當我深夜裡把鉛筆折斷的時候、把燒毀的日記/倒進花盆的時候,我常常想起你。//就像想起竹林般的青春,就像想起火折成的紙鶴。/就像想起血液、血液還在潔白的身體裡面激突。
然而現在我也四十多歲的中年之初了,並且旅居於楊德昌先生的台灣,想必會對電影另有一番滋味吧。
於是我在2020年的頭一個週末,打開Netflix重看《一一》,重看二十年前的台灣——其實2000年,那也是我第一次訪台的時間,看見片中清麗寂寞的台北街道,今天走過仍然是二十年前的樣子,物是人非,未免傷感。
在這種傷感情緒中,很難好好判斷一部電影的好壞。當年忽略《一一》,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個人的電影趣味,我傾向看非現實當下的電影,科幻或者古裝都好,我以為《一一》也是一部我所不耐的家庭倫理片。其實,我這個誤解也被《一一》調侃過一下,女主角婷婷說:「如果電影都是過生活,那我們就過生活就好了。」
這是針對「胖子」的玄思:「電影發明以後,人類的生命至少比以前延長了三倍」的。其實《一一》細看下來,就是比現實生活延長了不止三倍的藝術。南峻、婷婷、洋洋甚至那個討厭的阿弟,四條線有條不紊地編織著,拉扯著楊德昌六十年生命的感悟,把觀眾深深捲入,發現自己也不見得比他們活得明白。
當然現在的我,更接近南峻的歲數了。他面對的抉擇,往往也是每一個驚覺身已中年的男人會黯然自問的吧。所謂「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每個中年人都會在某一刻困惑,我是不是在某一個時刻下錯了車、走錯了路?我現在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嗎?然後就會有一些所謂的機會出現在眼前,也許是出軌,也許是換工作,也許是離家出走……對於南峻,則是重遇初戀,甚至借出差同游日本,「重回了七天青春時光」他這樣向妻子坦白。
但是他的結論是「本來以為,我再活一次的話,也許會有什麼不一樣。結果還是差不多,沒什麼不同。只是突然覺得,再活一次的話,好像,真的沒那個必要。」這裡面深深的虛無,其實還是帶著不忿。所以才有洋洋這個男孩角色的出現,來平衡男人楊德昌所面對的時光之凌虐。
藝術家一般的洋洋,接過了爸爸南峻的照相機,也接過了他的少年心。洋洋從此用不一樣的角度看世界,去拍攝一隻消失在乏味空間里的蚊子,去拍攝每個人看不見的自己的後腦勺。他因此看見了南峻黯然抹去的,世界本來有的另一種可能。南峻不能再活一次,洋洋能。
我寧願相信,洋洋是一個死而復生的人,他的確在游泳池裡淹死了,是婆婆顯靈用自己的一命換回了他的一命——婆婆拯救了的,還有洋洋的姐姐婷婷,她交給婷婷那朵花是電影的超現實妙筆,我們可以看到它依然存在於睡醒的婷婷手上。這個細節把夢與現實銜接起來,告訴婷婷也告訴我們:平行世界是存在的,世事不只有一個出口,寬恕自己與否,比後悔、渴望他人的寬恕更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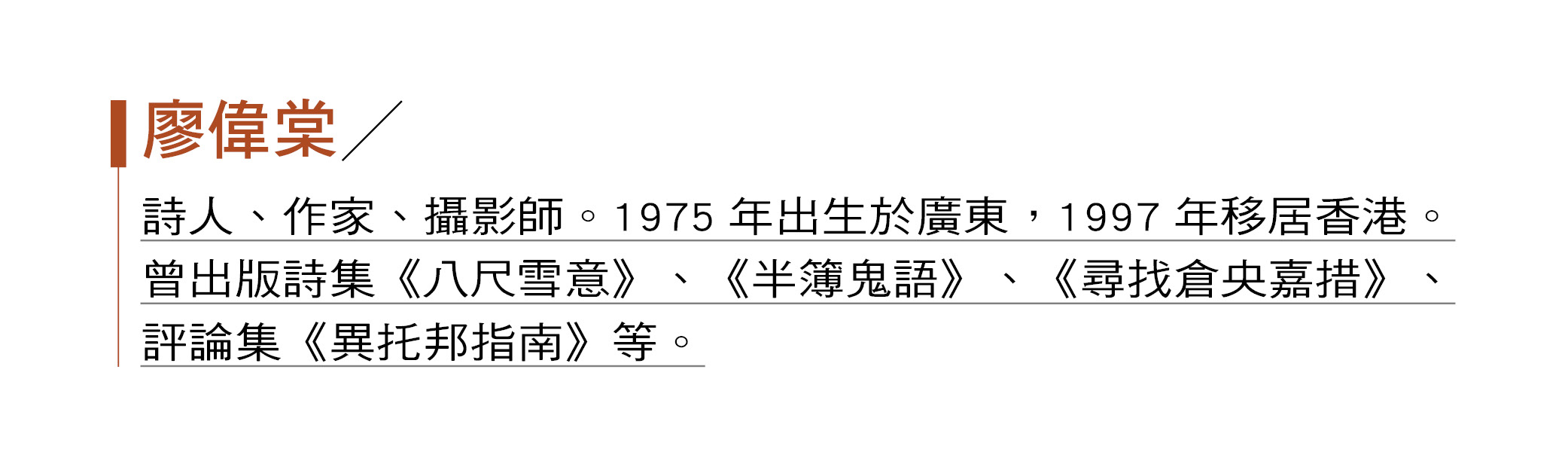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楊紫《國色芳華》播放量破2億狠甩《長相思》口碑慘澹負評 李現暱稱她「4字」全網嗑翻
- 黃牛退散!劇場版《進擊的巨人》完結篇首週特典、票根活動、聯名商品一次看
- 有票噴霧!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加開包廂區 1/19實名制一般售票開搶
- 快存沙漏!《PTCG Pocket》A2 卡包預計 1/29 推出 「洛奇亞、水君」等城都寶可夢即將登場
- 不斷更新!《跑跑卡丁車》2025《大馬猴盃》1/15 32 強中國山東開打 賽程分組、賽制晉級名單一次看
- 【微博之夜】王一博與《國色芳華》李現調換座位 竟是為了《慶餘年》肖戰內幕曝光
- 海軍承德軍艦升級外購裝備全到位 依計劃期程今年9月交艦
- 《九重紫》孟子義新劇熱戀《永夜星河》丁禹兮被看衰 原因與虞書欣、李昀銳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