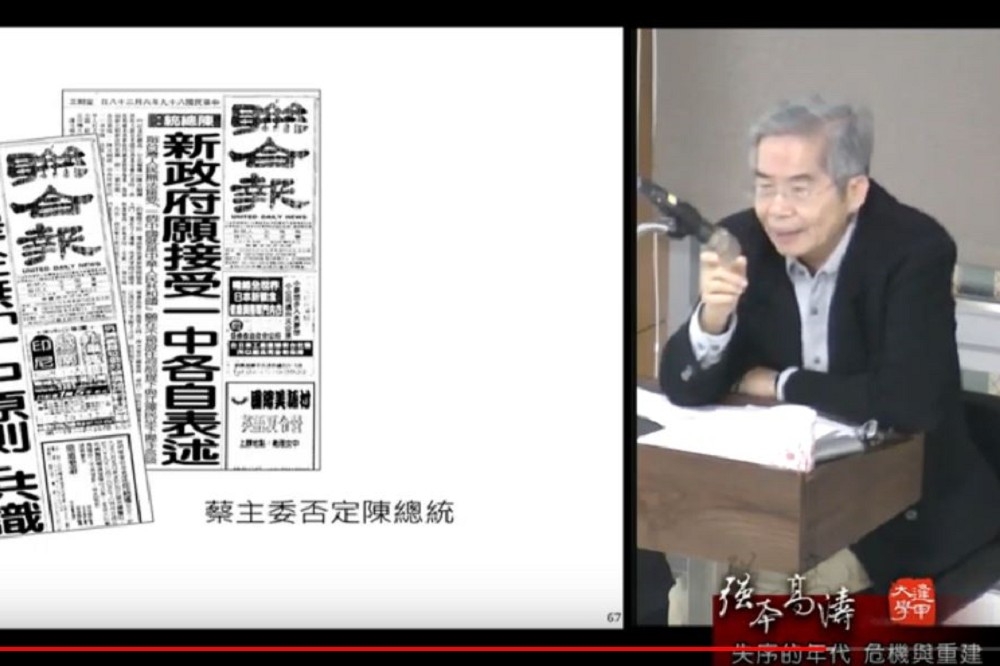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新北都會盃電競大賽》十六強Day3戰報:「妳還愛我嘛」逆轉獲勝,「稻江」成為最後希望! 2024-11-22 08:27
- 最新消息 【有片】普丁證實用最新「榛果樹」飛彈攻擊烏國 具MIRV技術可攜多枚彈頭 2024-11-22 07:50
- 最新消息 陳嘉宏專欄:「勞動部慘案」的背後是賴政府失能 2024-11-22 07:02
- 最新消息 投書:藍白已是不分青紅皂白踐踏台灣民主法治 2024-11-22 07:00
- 最新消息 2024 高雄城市咖啡節週末登場!集結 60 家咖啡與甜點店 冰滴、手沖、咖啡酒通通有 2024-11-22 07:00
- 最新消息 投書:當APEC的C位不是美國而是中國 2024-11-22 07:00
- 最新消息 謝宜容起碼幹掉賴清德半壁江山 2024-11-22 00:02
- 最新消息 投書:立院惡鬥 只會讓更多科技人企業人不敢投身政壇 2024-11-22 00:00
- 最新消息 勞動部稱謝宜容失聯明天不出面 吳母淚控:霸凌太過分、太惡毒 2024-11-21 22:05
- 最新消息 俄烏戰況恐升級 烏克蘭是否有能力攔截ICBM 2024-11-21 21:50

《美洲中國時報》於1982年9月1日正式發刋。余紀忠董事長(左四)在紐約總部印刷廠與同仁一起迎接第一份報的誕生。圖右二是黃肇松。是他參加報紙實務工作的開始。。(圖片由作者提供)
編者按:應本報之邀,在台、美新聞界、媒體圈從事新聞相關工作達50年的資深媒體人黄肇松,從今天起定期在《上報》發表以《行間字裹」為題的自傳。
黃肇松很年輕時,就被稱為「肇公」,新聞界認為他行事稳健,但規劃新聞常很勇健。在他的自傳中。他將回顧訪問多位國際领袖人物的台前、幕後及影響,也將詳述台灣媒体—尤其是報紙的過去、現在和「有沒有未來」。
新春伊始,今天刋出的《行間字裏》自傳首篇,已展開格局,未來請期待。
媒體叨叨摧歲月
白浪滾滾留沙痕
黃肇松
「白玉堂前一樹梅,為誰零落為誰開。唯有春風最相惜,一年一度一歸來。」
年年迎春詠花,在迎春的詩詞中,北宋著名政治家兼文學家王安石這首集句詩《梅花》,清冽孤清,卻又情意深切,讓人回味無窮。當然,王安石是在當年變法失敗後,領略人情冷暖,以這首詩感恩友人的慰藉。進到他的心境,進出新聞界50年的我,目睹台灣成千上萬的新聞工作者,不分晝夜絞盡腦汁採訪、報導、分析、論述,但是辛苦常不為人知,還經常受到批評究責,真有「為誰零落為誰開」的心酸,所幸還有最相惜的春風,吹拂著梅花,我也相信有不少有識之士,感謝記者在字裹行間維謢護他們的知的權利。
在經濟學家薛琦為迎接2020金鼠年新春而召集的晚宴上,我先與會眾分享了王安石的《梅花》共同迎春,來客多半是新聞學者和媒體工作者,一年一度的聚會,機會難得,談話主题很自然的繞著總統大選及媒體表現種切。坐在我對面的资深評論家《上報》董事長王健壯熱烈發抒讜論,散席之前對我説:「待會我們到東峯街小店再小酌一下,鴻仁已先到那邊等候。」
盛情難卻。返家招呼罹慢性病多年的妻子吃藥、安寢之後,抵達小館子,健壯和《上報》社長胡鴻仁應已談了一陣子。老友們晤聚毋需客套,甫坐定,健壯就説:「要請你在《上報》寫你的自傳,給你一㸃時間安排,最好在農曆過年前後就開始,定期刊出,風雨無阻。」
找不到寫自傳的心境和理由
寫自傳,茲事體大,劈頭來這一傢伙,著實嚇人。驚魂未定,我以三個理由推辭。其一、長期照顧病妻,自己也晉入初老,且仍在大學兼課,實難兼顧。其二、自傳者,傳世之記載,我不敢確定自己有什麼重大事蹟可記載傳世的。其三、總而言之,此時此刻,我還找不到寫自傳的心境和理由。

健壯立刻回應:「照料家事,非常重要,但鴻仁説,你已找妥外籍幫手,可幫忙照顧大嫂,問題可解。有關寫傳的資格,是我們來判斷,不是你能決定,當局者迷嘛。至於發表自傳的理由,你在新聞界半世紀,你不寫,誰寫?而論及寫自傳的時機,你夫子自道已步入初老,我看精氣神還行,此時不寫,更待何時?」
除了論㸃獨到、文筆犀利的專欄擁有不少粉絲之外,健壯的能辯、善辯、樂辯,聞名媒體界和知識圈,我自嘆弗如,而寫傳的心境、資格和理由,也不是適於深入探究的論辯主题,應予「戒糾」,倒是他提到我出入美、台媒體圈50年,不留個某種形式的「傳」,似有「失職」之嫌,頗打動我心,具說服力。新聞是歷史的初稿,寫歷史初稿的媒體工作者,把漫長的新聞生涯中的所見、所聞、所得、所失,擇要作成紀錄,即使是雪泥鴻爪、沙上留痕,應仍具有其歷史參考價值和背景解析意義。
媒體50年,你不寫,誰寫?
就像詩仙李白的名句「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春夜宴諸從弟桃李園序》首句)意指萬物短暫棲身於有如一座旅店的遼闊大地,之後便走向永恆的放逐;而面對無邊無際的時光,世代流轉更迭的人眾,也不過是步履匆匆的過客。如果沒有人用文字等工具把變遷的大地和人們在其上的活動,忠實的留下紀錄,所有的一切終將湮沒在歷史的煙䴤中。從集結歷史大視野的個體現時微觀角度觀察,浮生若夢,記載幾何,人人鼓足勇氣向寫傳挑戰,確實是人生逆旅不應推卸的責任。健壯的嚴詞㸃撥,不失為醍醐灌頂的啓發。
當然,從最髙層次的國史的研修,到中層次的地方志的撰述,涉及論述臧否之間的平衡公正的考量,許多國家設有類似國史館的組織主持其事,地方亦有文獻委員會支持、協助地方志的作成,其作法都是集結學者專家的智慧和力量衆志成城,個人傳記的撰寫則是獨力為之,過程是相當辛苦的,也是孤獨寂寞的。而構築傳記工程所需的種種元素,包括各類資料、圖片、表格、統計及編年史料的耙疏,工程浩大,甚費心力,所幸,胡鴻仁社長慨允《上報》可予支援,讓我鬆了一口氣,顿時提振不少勇氣。
健壯推算我入行新聞界50年,其實我真正進入新聞實務界,始自1982年在紐約参加《美洲中國時報》的創刋工作,迄今從事媒體實務及新聞教學38年,在那之前的12年,是我在政治大學畢業後,於1970年參加公務人員髙考,獲新聞行政科優等錄取,被分發到行政院新聞局,從事為國内外媒體記者服務的工作,箅是後期我的新聞實務工作的養成階段,仍然是我大半生新聞生涯重要的一部分。
34歲入行媒體是否晚了些
三十出頭入行媒體實務界,是否晚了些?可能有仁智之見。當時我已經是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前駐美大使舘)紐約新聞處一等秘書,台灣家鄉父兄親友,都希望我在外交、新聞行政系统作下去,起碼做個簡任官,光宗耀祖,但我回歸新聞實務工作的意願很堅定,多方請益,不改其志。其間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1982年3月在纽约市曼哈頓中央車站(Grand Central)上方的君悦飯店,與美國新聞同業卡威爾君(Jacques Caldwell)的餐敍。
當時,卡威爾擔任總部設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史克利普斯霍華德報團(Scripps Howard Newspapers Group)總經理。該報團斯時在美國擁有大小報纸30多家,還經營電視台和廣播電台,很有影響力。卡氏於1979年夏間訪台,我負責邀訪事宜並協助安排在台灣的行程。他對台灣人民的善良熱情印象深刻,與我漸成朋友,我兒子黄柏春1980年出生後乘坐的嬰兒車,就是他送的。卡氏每月月底到紐約主持報團業務會議,得空會找我聚晤。我在這次餐敍中告訴他,我將離開新聞處,去報纸工作。
 黄肇松經常在報纸上批事論人,而報紙寫他較多的一次,卻是10年前《聯合報》對他的專訪。(圖片由作者提供)
黄肇松經常在報纸上批事論人,而報紙寫他較多的一次,卻是10年前《聯合報》對他的專訪。(圖片由作者提供)
卡威爾有些意外,喃喃道:「你在新聞處作得很好啊」,然後問:「英文報嗎?」我回答,中文報,台灣《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來紐約創刋的。他沈黙了片刻,像在想些什麼。我乘機問道:「我今年34歲了,改行做報紙工作,是否太老了。」他很快回答:「不會。30出頭正是創造力最豐富的年紀,何況你前後的工作有很大的連貫性,基本上,不是大轉行。Now, you observing from the outside(現在,你從外頭作觀察),in the future, you working from the inside (將来,你在裹頭参加工作。)」
卡威爾還擧他自己的職場轉換經驗為例,他20年前從企業轉業到媒體,𨍭眼都已經50多歲了,仍能不斷創新,「創新是媒体的生命」。
如果我是你,我會重作考慮
停頓片刻,卡氏又問:「你台灣報紙的老板今年幾歲了?」這回換我感到意外,何以有此一問,但仍回答:「72歲」。他盯著我看了約有一分鐘,有點難以置信的説:“Mr. Huang,if Iwere you,I would seriously reconsider it .”(如果我是你,我會很嚴肅的重作考慮。)
我理解他的「疑慮」。在美國,各類型媒體負責人與其他企業負責人一樣,基本上65歲就退休養老去了,卡威爾認為我追隨一位70出頭的長者去辦報,應考慮其「風險」。我更體悟他的考量,乃是為我「設想」的善意。我作以下的回答,技巧性𨍭換話題:「余先生生活作息規律,運動量多,身體很健朗;而且就我接觸交談的印象,他的創意似乎隨著年歲所累積的經驗而增加。」卡威爾顯已收到我傳給他的「訊息」,欣然説道:「那就好,祝你們成功。」
就這樣,帶著友人「善意的疑慮」,我開始我的報紙生涯。歲月如歌也如流,我現在的年歲,就是余紀忠先生當年到美國創辦《美洲中國時報》的歳數。除了這份報紙,余董事長在72歲之後,又創辦了一些新的報刋雜誌,甚至還創辦了台灣第一份網路報—中時電子報。回首歲月的軌跡,余先生一以貫之的報人生涯與我的報纸工作重疊的有21年,他在2003年4月以93歲髙壽辭世,五年後我從《中國時報》退休,轉往其他媒体工作。其間的漫長歷程和之前累積满長的「養成階段」—為賦新詞强説愁的青少年的探索;把新閜系作為「輔系」的大學階段;磨練協調力、組織力、觀察力和耐性耐力的新聞行政公職生涯,都將是白浪滾滾留沙痕的或大或小、或重或輕、或長或短的自傳素材。
到這年歲,該怎麼寫就怎麼寫
然而,如果從早期與文字結緣的少年時代說起,到現在還在寫社論的初老,歷時一甲子,足跡遍五大洲,如何選材、如何耙疏、如何部署、又如何撰述,自當慎重規劃。首先向自傳的「催生者」王健壯、胡鴻仁兩位老友請益。王董事長仍一如旣往維持快人快語的風格:「怎麼選材和書寫,都由你決定。」稍後,好像不太放心,又叮上一句;「到了這個年紀,該怎麼寫,就怎麼寫唄。」言簡意駭,自當納行。
胡鴻仁社長仍維持一貫的溫穩深思的風格:「你的美國報人老友卡威爾不是説創新是新聞的生命嗎,就以你認為有那些創新之擧貫穿全書吧,最好能結合今昔,寫出新義。」他希望我的傳記旣能勾起我們這個世代的一些共同記憶,又能給當代的新聞工作者一些參考和啓發。我們都同意,這樣的傳記寫作,才能把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聯結意義彰顯出來,也才能突出歷史初稿的價值。
兩位報界老夥伴對我的自傳期許很髙,究竟能不能做到?或者能做到幾分?提供何種面貌的「歷史初稿」?或是中途難以為繼,愧對老友和讀友,一如前人所云「自忖不材終放棄,江潭瓠落寄吟身。」(清朝黃景仁《送容甫歸里其二》詩句)?旣已出發,只能盡其在我,責任自負。我邀鴻仁檢視:20世紀後期,在國際新秩序震盪發展之際,在余纪忠先生支持下,在鸿仁及同仁協助下,我在《中國時報》推推動的「全球重要領袖系列専訪」,是不是富有創意的新聞規劃?對當時台灣的主流報紙是不是有「推波助瀾」的引導作用?是不是迄今對媒體仍有一定程度影響?是否應該作為傳記主軸之一?
具創意的國際領袖系列專訪
胡社長答覆都是肯定的,並認為至少是我的傳記的重要精華。同時,他再度強調,傳記中對當年訪問國際領袖作回顧的同時,不可忘記論及現況,並作今昔比較,則不僅可串連同世代人的共同記憶,也可作為當今新聞傳播學府有關國際傳播的參考教材,及媒體處理國際新聞實務的參考。以1992年在馬尼拉訪問當時菲律賓總統羅慕斯為例,他坦承讓包括大學畢業生的菲國男女青年長期到國外當工人或女傭,為國家賺外匯,是主政者「心中的最痛」,當時讓在場的我們動容,過了近30年,這心中最痛的一塊,於今如何,應予檢視,讓當年的專訪賦有穿透時空的新義。
其後的十餘年,二十多次的國際重要領袖專訪,屢屢出重要領袖所説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國際級「金句」,迄今還有什麼啟發性,亦値再探。譬如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在1993年辜、汪新加坡會談之前,首度接受我和記者徐宗懋專訪時,欣然的說:「如果兩岸要求我當『公親』,必定不偏不倚。」但是,1997年再訪,李光耀卻黯然的说:「針對兩岸,我已經退出了!」其間不過相隔四年,沒有內幕,卻有原由,在自傳中,我會詳述。另一次重量級專訪,舉世聞名的南非鬥士曼德拉(Dr.Nelson Mandel)1993年南非總統競選期間,於來台訪問前夕接受我、徐宗懋及另位記者曹郁芬專訪時說:「忙著思考南非的未來,我沒有時間回顧過往的苦難。」晚年堅持包容主義的曼德拉,如果在天上看到南非貪凟風行的現況,不知作何感想?愧對曼德拉的南非領導人又如何自處?我在自傳中會以專章探討。
 黃肇松當年在報社推動的「國際领袖系列事訪」,頗受注意。圖為1997年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接受專訪,訪問完成,黄肇松馬上要搭機返台。李光耀可能有㸃過意不去,主動送一本自傳新著,還簽了名。(圖片由作者提供)
黃肇松當年在報社推動的「國際领袖系列事訪」,頗受注意。圖為1997年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接受專訪,訪問完成,黄肇松馬上要搭機返台。李光耀可能有㸃過意不去,主動送一本自傳新著,還簽了名。(圖片由作者提供)
訪楊尚昆主席與習近平書記
當然、在上世紀90年代國際新秩序形成的衝撞中,不能忽視崛起中的中國大陸,尤其蔣經國總統在1988年1月辭世前半年,在病塌上連發三箭—解除報禁、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两岸關係解凍,為满足民衆知的權利,台灣的主流報纸更不能忽視其發展。然而,解凍之初,媒體跨海採訪的限制仍多,報端常見美、日政客熱中為两岸「傳話」的報導。
基於兩岸問題宜由媒體作直接採訪報導,避免「二手傳播」可能導致事實真相的落差,《中國時報》在1990年9月北京亞運舉行期間,根據新聞專業原則,接洽安排訪問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因先前早已決定我將前往北京主持報系亞運採訪事宜,所以對楊尚昆的訪問,也由我擔任採訪團領隊,成員包括副總編輯黃輝珍及大陸新聞中心主任俞雨霖、副主任張所鵬等。楊尚昆答問時指出「同胞不會打自己的同胞」,「希望兩岸有直接溝通的渠道加強交流」,在1994年「千島湖事件」發生之前,應該是中國大陸對台政策的基調,兩岸關係平穩發展。連美國前總統老布希都稱之為「一次重要的採訪」的専訪楊尚昆的經過和影響,當然會在我的自傳中詳述。
來自台灣的報紙專訪大陸國家主席,之前從未有過,之後也沒有第二例。然而,1991年7月我偕同《中國時報》記者走訪福建期間,曾訪問當時擔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他詳細的介紹了褔州發展情況,以及福州與台灣關係的源遠流長;而在當時中國大陸邁向經濟改革的另一波髙潮之際,習近平強調台商赴褔州投資是未來經貿工作的一個重㸃。回顧採訪印象,習書記描刻的似乎不只是一個省會城市的發展願景;而近距離的觀察,他的穏健也似乎超過他的年紀。習近平當年不到40歲。

報纸創新難擋網路致命性衝擊
「國際領袖系列專訪」是我當年主導《中國時報》內容創新的重要規劃,但只是報紙創新的一部份,在余紀忠董事長和後繼的余建新董事長的支持和督促之下,包括版面編、採元素及經營方針、營運策略的全面創新,我或者主導編務部分,或者對營運部門提供建議,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並且督促自己身體力行,尤重编經的全面合作。《中國時報》在20世纪後期,經美國權威的「報紙銷數稽核局」(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簡稱ABC) 嚴格審核,銷量超過百萬份,最髙達130萬份,影響力巨大,我與有榮焉。
以這樣的銷路和影響力,於台灣在20世紀90年代迅速的進入完全民主的時代,自然是動見觀瞻,我們以第四權監督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運作;廣大群眾也在監視我們:是否據實報導?是否公正評論?是否嚴格把關?是否切中時弊?總之,是否善盡媒體的社會責任?在這個我個人認為是台灣百年一遇的大時代,我們忠實反映民意的作法是什麼?成效如何?得失如何?在自傳中,我都會詳為解析。
最後,容我借用李白的樂府《將進酒》的頭四句:「君不見黄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髙堂明鏡悲白髪,朝如青絲暮成雪?」來形容報紙的處境。在上世紀末,就在我們爲報紙公共性的打造,絞盡腦汁全力以赴的時候,科技帶來像從天上滾滾而降的網路,攬鏡不勝哀悲的,就是傳統媒體,尤其是報紙。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報紙是如何因應的?我們並没有「不戰而降」呀!我在1994年就参加了中時電子報的創設,是紙媒成立電子報的前驅者,迄今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仍難謂成功,原因何在,亦請容以後解說。
《 作者素描:黄肇松 的唯一:新聞 》
黃肇松「矢志新聞工作」,是從小學五年級投稿《國語日報》學府風光版開始;省立苗栗中學初中部期間任《青年戰士報》校園記者;髙中時任《中央日報》苗栗特約記者,並任《苗中青年》總編輯及《香港工商日報》市聲版特約作家,是黄肇松少年時期對新聞採、寫、編的探索。
考入政治大學東語系讀語文,常常出現在政大新聞舘,把新聞系當「輔系」,後考入政大新聞研究所的「正途」,為其後的新聞工作紮基。
黃肇松的「廣義的新聞工作」,從通過髙考,進入行政院新聞局開始。為國內外的媒體記者提供資訊服務,歷任科員、編審、科長及駐紐約新聞處一等秘書。
1982年轉入中國時報集團在紐約創刋的《美洲中國時報》工作,歷任主筆、編譯主任、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後任《中國時報》駐紐約特派員。前後在紐約從事新聞相關工作11年。
1987年返台,開始他在台灣大開大闔的新聞實務工作。先後任《中國時報》副總編輯、總編輯、社長,中時報系總管理處執行副總經理、總經理,常務董事兼《時報周刋》董事長。2008年從時報退休,任職27年。其後,先後被聘為中央通訊社董事長、《台灣中華日報》董事長。其間曾獲世新大學聘為專任客座教授,執教六年。
從嚮往新聞到讀新聞、做新聞、教新聞,一以貫之,新聞,是黄肇松的唯一。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起底謝宜容!傳身家背景雄厚「善做公關」 先生和綠營高層有交情
- 一元特典!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釋出「零星票券」,11/24 採實名制一般販售
- 【世界棒球12強賽】滿足「2條件」台灣確定晉級4強 今晚是關鍵
- 先搶先贏!Ado 五月林口體育館演唱會採實名制入場,11/19 輸入「指定代碼」可優先預購
- 【內幕】T112步槍裝彈器採購案疑專利侵權 以色列向軍備局寄存證信函
- 王一博金雞獎典禮被抓包視線離不開趙麗穎 網揭兩人4年戀情無法曝光背後真相
- 勞動部涉職場霸凌不只謝宜容? 何佩珊:與輕生者中間還有2個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