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不斷更新/【世棒四強賽】「中華隊 vs 美國」中華隊9局三上三下未建功 暫以8:2領先 2024-11-22 14:17
- 最新消息 清華大學擬併中華大學 將設「清華平方科技園區」發展半導體 2024-11-22 13:51
- 最新消息 英王查爾斯三世加冕禮花費高達29.5億元 逾半民眾表態反對政府買單 2024-11-22 13:48
- 最新消息 【京華城弊案】朱亞虎200萬交保 李文宗11/26開延押庭 2024-11-22 13:30
- 最新消息 【世棒四強賽】峮峮也來了! 啦啦隊女神團美到登上東京巨蛋大螢幕 2024-11-22 13:10
- 最新消息 「巴西川普」波索納洛涉嫌政變 與4將軍企圖毒死或炸死正副總統 2024-11-22 12:50
- 最新消息 賴清德總統任內首次出訪選擇南太 黨政人士曝戰略考量 2024-11-22 12:40
- 最新消息 《大夢歸離》侯明昊錄真人秀在非洲草原拉屎 全程被外國遊客拍下秒登熱搜糗爆 2024-11-22 12:34
- 最新消息 【有片】露面了!謝宜容鞠躬道歉 落淚稱對不起家屬:孩子成冷冰冰遺體 2024-11-22 12:20
- 最新消息 美特使還在以色列進行調停 以軍持續對黎巴嫩空襲釀47死 2024-11-22 12:03

如果把一戰換成別的戰爭,甚至我們身處的抗疫之戰,我們能否領悟出更多的寓意?(《1917》劇照/圖片取自時光網)
《1917》,死神篩籃上的倖存
西方近代史,每逢瘟疫蔓延的黑暗時期——無論是病毒瘟疫還是政治瘟疫,常常會出現愚人船(The Ship of Fools)的寓言,有歌謠有詩篇,也有畫作。最有名的是Bosch的《愚人船》,畫的是一艘搖搖欲沉的小破船,上面坐著各種愚人、小丑,他們為著種種執念作出可笑的舉動,在某種想必也是愚昧的力量引領下駛向死亡。
但愚人船的極致表現,是愛德華.李爾(Edward Lear)的詼諧詩《呆頭人》(The Jumblies)所寫:
They went to sea in a Sieve, they did,
In a Sieve they went to sea:
In spite of all their friends could say,
On a winter’s morn, on a stormy day,
In a Sieve they went to sea!
And when the Sieve turned round and round,
And every one cried, ‘You’ll all be drowned!’
They called aloud, ‘Our Sieve ain’t big
But we don’t care a button! we don’t care a fig!
In a Sieve we’ll go to sea!’⋯
「他們乘著篩籃出海⋯」全然不顧海水上漲輕易淹沒自己,這明顯是愚蠢至極的行為,但又流露著一種盲信的宗教意味,帶著神秘色彩。春節自閉,在一片瘟疫宣告勝利的消息包圍中,我意外聽到這幾句詩,如在夢魘中驚醒。
說是意外,因為誰也想不到,當《1917》裡的傳令兵Schofield下士對著他在法國淪陷區裡遇見的嬰兒,喃喃背誦出來的,是這樣一首奇異無比的詩。
但也只有這麼一首啟示錄一般的詩才能配得上電影裡這一段神奇場景,以及這個最不可能的嬰兒——就像照顧他的女郎所說,他並非她的孩子,不知道來歷——這樣的組合,歷史上只有瑪利亞與耶穌,那麼慷慨照應她們的Schofield,無意擔當了聖約瑟的角色。
很有可能這都是Schofield頭部受傷之後的夢幻,當他走下塔樓,置身於一個燃燒的教堂與乾涸的噴泉前面,這就展開了艾略特《荒原》裡的現代啟示錄——一系列的光影交錯既是現實可能有的照明彈所營造,更是Schofield的內心隱喻。他所穿過的地獄廢墟亟須被照亮,然而這聖光是超乎善惡的,搖曳不定的。夢醒後,Schofield依然得靠自己穿越戰火,給前線帶去停止進攻的消息,然後找到本來就屬於他的那棵可以依靠的小樹。
可以說,廢墟中藏匿的嬰兒就保證了結尾的小樹的出現,就像塔可夫斯基《犧牲》裡那個因為不能說話的孩子保證了電影結尾的小樹一樣。
《1917》的導演薩姆.門德斯在出離全片的現實主義戰場描寫而營造的夢幻感,的確帶有濃烈的向塔可夫斯基致敬的意味:除了《犧牲》裡的救贖隱喻,曳光彈掠過奔跑的Schofield那段,也讓人想起塔可夫斯基早年作品《伊凡的童年》裡男孩情報員伊凡穿越戰火泅渡夜河那一段。他們都是和平所索求的犧牲。
在這樣的背景下看Schofield讀「他們乘著篩籃出海⋯」分外觸目驚心,「他們」是被戰火摧毀的一代精英還是好戰的民族主義者?他們都是無辜但又有共業的一代人,最終都會陷入《1917》裡無處不在的死神盛宴一般的地獄變圖卷。經過了一戰,為何沒幾年又有了二戰?人類真的有反省能力嗎?為什麼他們始終都選擇坐上篩籃出海而不看看腳下湧出的海水?
Schofield本來也是篩籃中的一人,但他對信念的選擇拯救了他也局部拯救了世界。在受傷一刻分割的前後兩個世界之前,有一個細節確保了這場拯救:當Schofield與Blake走過那個被遺棄的農莊,只有Schofield欣喜地留意到牛奶桶裡的牛奶依然新鮮,於是他灌滿了自己的水壺。所以當他後來遇見無母嬰兒的時候,他才得以把這罐牛奶送贈給後者。他珍惜生命,珍惜和平中應該有的牛奶。
也是在這個恍惚出離戰火之外的農莊,有這樣一段對話:「那麼說櫻桃樹沒救了?不,果實腐爛時還會再長出更多的樹」。同理,戰爭所遺棄的牛奶也拯救新生,使得Schofield、聖母子以及被Schofield傳信拯救下來的士兵們都成為篩籃上的倖存者。
這些充滿救贖意識的對話、隱喻、潛文本,拯救了《1917》非常單薄的劇情,也使得它所謂的一鏡到底式技術奇蹟不至於流於炫技。本來這是一個屬於技術時代的沉浸式體驗電影,結果被塔可夫斯基的靈魂附體,加持成為寓言級別的佳作。如果把一戰換成別的戰爭,甚至我們身處的抗疫之戰,我們能否領悟出更多的寓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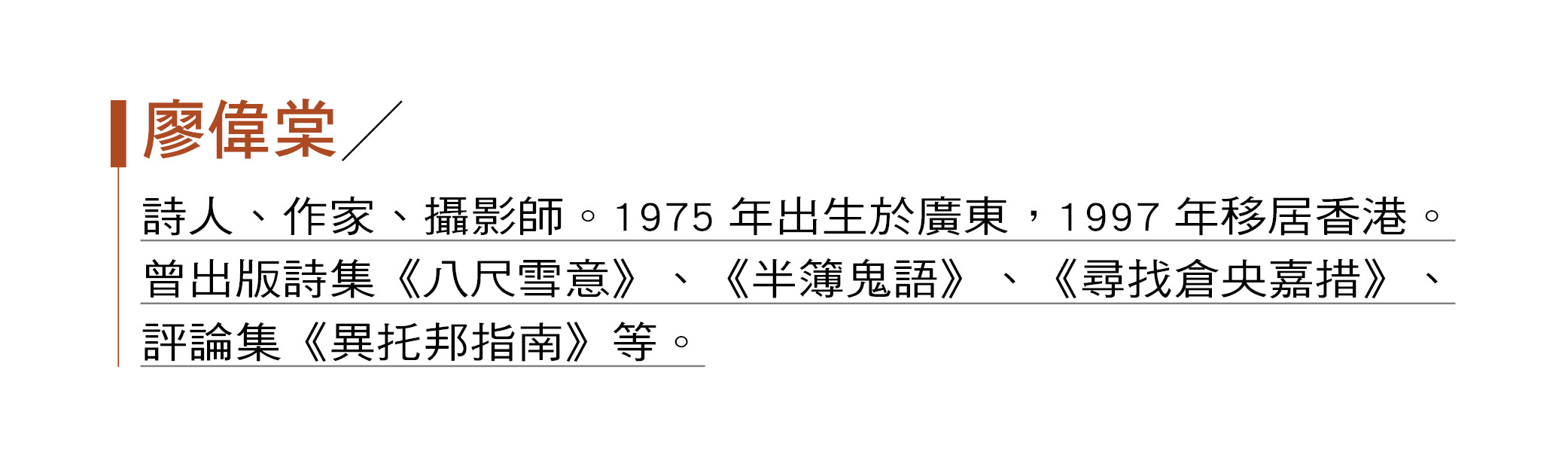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起底謝宜容!傳身家背景雄厚「善做公關」 先生和綠營高層有交情
- 一元特典!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釋出「零星票券」,11/24 採實名制一般販售
- 【世界棒球12強賽】滿足「2條件」台灣確定晉級4強 今晚是關鍵
- 先搶先贏!Ado 五月林口體育館演唱會採實名制入場,11/19 輸入「指定代碼」可優先預購
- 【內幕】T112步槍裝彈器採購案疑專利侵權 以色列向軍備局寄存證信函
- 楊冪人氣暴跌與《慶餘年》張若昀演新片淪鑲邊女主 造型曝光全網夢回《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 王一博金雞獎典禮被抓包視線離不開趙麗穎 網揭兩人4年戀情無法曝光背後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