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硬抗川普關稅】中國政策宣傳攻勢連發 專家打臉不看好 2025-04-08 23:00
- 最新消息 王鴻薇指控潘孟安住免費豪宅 「金屋藏潘」涉不實指控判賠50萬 2025-04-08 22:02
- 最新消息 北約秘書長稱中國軍事擴張驚人 籲日本加強雙方合作 2025-04-08 21:45
- 最新消息 反傾銷調查聽證會今舉行 台灣釀酒商協會:中製啤酒低價策略損害產業 2025-04-08 21:35
- 最新消息 美智庫揪出「對等關稅」算法竟高估4倍 日媒:台日韓關稅應為10% 2025-04-08 21:28
- 最新消息 蔣萬安市府人事再異動 台版「地面師剋星」出任地政局長 2025-04-08 21:08
- 最新消息 陽明海運員工墜樓涉職場霸凌? 公司發3點聲明已啟動調查 2025-04-08 20:45
- 最新消息 檢銀啟動「可疑金融帳戶通報機制」 中國信託攜手士檢抵禦金融詐騙 2025-04-08 20:28
- 最新消息 準備變天!2波鋒面接力報到 明晚起雷雨狂掃全台 2025-04-08 20:11
- 最新消息 【獨家】民進黨北市黨部爆大量黑道入黨申請 愛情詐欺犯、毒蟲成特定派系人頭 2025-04-08 20:00

政大早年地處木柵鄉下,保持文科大學的傳統,開設不少文史哲及社會科學的博雅課程供學生選修。圖為課後師生在校園留影。作者在前排左三。 (圖片/作者提供)
新聞人生三部曲 初譜在大學
承《上報》之邀,年初起開始定期撰寫自傳系列。主編在首篇「媒體叨叨摧歲月 白浪滾滾留沙痕」之前的「編者按」,和欄目之後的「作者素描」、如此介紹我:「黄肇松『矢志新聞工作』是從小學五年级投稿《國語日報》學府風光版聞開始- - -從小時嚮往新聞到讀新聞、做新聞、教新聞,一以贯之,新聞,是黄肇松的唯一。」簡單扼要的介紹,刻劃了我新聞人生三部曲,是名編的神來之筆。
卻讓我想起傳頌千年的東波先生的《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 ,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林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首著名的詞是蘇軾人生三部曲的「夫子自道」。面對自然風雨,他吟嘯慢走;面對政治(事業)風雨,他醒酒迎斜陽;面對人生風雨,他以「無風無雨也無睛」的坦然自持相對。這種以大智慧、大境界的曠達樂觀來抖落人生種種失意、落寞和痛楚的胸懷和涵養,千年以來,幾人能及?回首前塵,我在追求媒體生涯、打造新聞人生的過程中,歷經風雨波折的滄桑和難測未來的頓挫,有時不免油然而生引退之心、放棄之意,比起歷朝歷代先賢前哲如東波先生的無畏與堅持,能不慚愧?
也無風雨也無晴應善自規劃
值得慶幸的是,比起蘇東坡、李白、杜甫、柳宗元、韓愈這些封建時代動輒遭貶斥的知識份子或詩人文人,在人生各個階段中,常彳于獨行,處蕭瑟之處,現代學子在求學過程中,知識份子在與社會接軌時,專業人士在提升素養上,基本上可得到不少助力,包括:提供各類學習機會的現代化機構如大學、研究院;保障研究成果或創作成果的典章制度;旣能竸爭又可合作的同儕比肩;以及職司監督褒貶的新聞媒體。每個個體要做的,是在「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寧靜而公平的環境中,以自己的興趣、心力和能力,打造自己的人生。
當然,林林總總的各類型社會機制,並不能保證一個人的人生规劃總是一帆風順的。我自己的經歷就是一例。在我十一歲那年小年夜的家庭聚會中,公開表示將來要當記者,接著在小學、中學階段對新聞工作進行早期的探索之後,讀新聞、學新聞,完成新聞教育,入行媒體,應該是我人生順理成章的規劃。其實不然,民國55年夏,在填满舊制大專聯考乙组(文、史、哲、新聞、教育類组)170多個「志願」,經過不很順暢的兩天六科考試,結果是被分發到政治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土耳其文組。
記得放榜是8月8日,晚上聴中廣公司報榜,一些親友帶了鞭炮來一起聽。聽到我名字,掌聲響起,鞭炮放了。一位長輩問我:「介遮系,是做嚒怪耶?」(客語,那個系是做什麼的?)我説:「我也不知道!」大家一陣哄笑。我當然知道,只是在亂哄哄之中,不知如何解釋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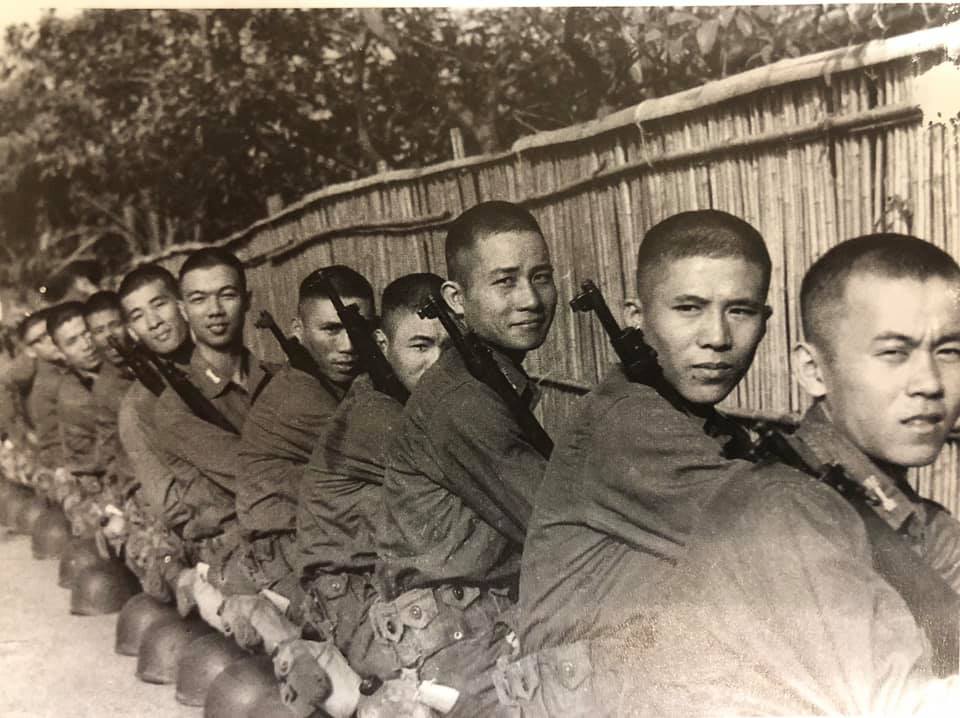
把新聞系當「輔系」規劃人生
東語系是我的第三志願。第二天看報上的分數一覧,我距第一志願台大外文十二分,距第二志願政大新聞系兩分,我是土語組「榜首」。有些悵然,但一陣過後,也很釋然。之所以在科學邏輯上並不合理的數以百計的「志願排行榜」上,我把土語組排那麼髙,是有我的規劃。1960年代中東戰火頻傳,是國際新聞的焦㸃,土耳其雄據博斯普魯斯海峡和達達尼爾海峽,主控亞歐地缘政治,如能通土語,到土國當台灣媒體特派記者,自是新聞生涯的合理安排。加上我髙中時代讀過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的傳記,對他推翻延續了400多年的鄂圖曼帝國,與孫中山先生在同時期創建一東一西两個民主共和國,同表欽佩,如能到他創建的國度作較長時間的深入採訪,益增新聞生涯為所應為的獨特性。
就懷著如此的細膩心思和豪情壯志,進了當時坐落在堪稱偏僻的台北縣木柵鄕的政治大學。發現讀這种特殊語文很有趣,也很辛苦。已經十七、八歲的大學生,卻要像土耳其六、七歲的小孩從土語字母學起;從1、2、3、4- - -的土文數字記起;還首次接觸到與中、英文大不相同的特殊文法結構—動詞永遠擺在句子最後,或說或寫都急著找受詞加受格的慌亂。儘管如此,我讀的很認真,也很用心。
總结大學四年,土語組相關必修、選修課程,我修了19門,實得104個學分。當年政大畢業只需128學分。除了土語課程,我修習了土國歷史、土國地理、土耳其文學史、名著選讀、現代文選、修辭學及土語翻譯等。基本上在「土耳其學」的範圍內,我完成博雅教育的基礎訓練。
研習博雅教育 磨練新聞專業
用進廢退,畢業50年,我的土文、土語都已忘得差不多了。但在我坦白從寬的同時,還容我回憶一個似可作為「成果報告」的往事,大四上學期我找到一位土耳其歷史學家所撰,有關西元八世紀後半葉義大利探險家馬可波羅東遊至中國,往返都經過土耳其安那托利亞髙原的見聞,頗有歷史意義,藉「土英詞典」的幫忙,我花了一些時間譯成中文,文長萬餘字,獲當時頗為𣈱銷的中油公司支助發行的益智刋物《拾穗》月刋登出,賺了一些稿費,更蒙 教了我們四年土語的劉恩霖教授嘉獎為:「學以致用」。
對一位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而言,這是很有鼓舞作用的勉勵,迄今難忘。但我從小想要「致用」的目標是在新聞,所以大一開始,我就常出現在新聞舘,我不是去串門子,也不是隨興旁聽,而是把新聞系當「輔系」,認真修課。我不太相信自修成功的神話,是一個願承受學分壓力的「苦讀派」(我畢業時得173學分,平均成績91.2分,應可證明)。接觸愈多,愈暸解新聞是通往社會的窗口,也是將學校教育與社會連結的有效觸媒。因此,接觸新聞教育後,也更體會新聞工作者需要全人教育、通才教育和素質教育,也就是博雅教育,不能只學「新聞術」(journalistic craftsmanship)。執美國新聞教育牛耳多年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一向偏重學生在「術」上的訓練與培養,17年前波林傑(Lee C. Bollinger)接任校長,要求新聞學院提髙博雅課程比重,引發美國學術界熱烈討論,不少新聞學者附和。
所謂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是西方傳統引以為傲的教育理念,拉丁文叫 artes liberales,意指「適合自由人」,由人文教育(或稱文理教育、文雅教育或通識教育)培養而成;其實在東方,孔子和其門徒所留下的「遺書」—《大學》,強調「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博大的學問,也與博雅教育相通,只是當時沒這個稱呼而已。從西方古希臘大教育家柏拉圖提出「人文七藝」的教學理念,到今日更廣泛、更符潮流的通識教育,都在提倡學科之間的相互融合,其作用並不在與專注某一領域的專門學科相抗𧗾,而是恢復文科教育的真貌,引導學生從根本的思考開始,追求思考的完整。這就是博雅教育的真諦。
 小班制是政大博雅教育的特色之一。最後一排右一是作者在課堂上課。(圖片/作者提供)
小班制是政大博雅教育的特色之一。最後一排右一是作者在課堂上課。(圖片/作者提供)
單調的理性難成稱職的窗口
旣云「新聞是通往社會的窗口」,追求成為新聞工作者,需先瞭解我們與社會的關係是什麼?我們對社會有什影響?過度專注於某一個領域的學習,忽略對人文精神和通識內容的適度的關注,剩下一種「單調的合理」,可能喪失與社會的溝通能力,那要如何「為民先鋒」,滿足受衆知的權利?如競相追逐專業的利益,而讓吾人以往依賴的道德觀、倫理觀和專業價値準則淪喪了,一如當前一些媒體的所作所為,那又如何維繫媒體的公共性,善盡社會責任?博雅教育對新聞教育的重要性,至為明顯。
所幸,在師長和兄長的引導下,我自幼培養了還算不錯的閲讀習慣。在鄕間放牛的時候,卷不離手,進入各級學校「讀冊」,漸求廣濶多樣,雖無博雅之名,漸有其實。更幸運的是,政大當時雖地處鄉間,但秉持文科大學的悠久傳統,開設不少人文社會課程,讓學生徜徉其間。我就在這種人文氣習濃郁的環境中,選修了培養學生的思辨邏輯和思考完整的「哲學概論」和「理則學」;我也修了三門歷史課程「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及「西洋文化史」,我們可從史識中鑑古知今,遇到問題,學習古人是如何解決的;我還選修「政治學」和「憲法」,以助理解當今社會整體運作的法理基礎和制度規範。這些博雅教育中的「博大學問」,應該都是追求成為新聞人的必修功課。至於我修習吳盛木教授(東京大學心理學博士)的「普通心理學」,博大精深,更是我瞭解閲聽人資訊需求和閱讀心理的重要一課,至今受用。
新聞教育我來了 譜我人生樂章
就這樣,在語文教育和博雅教育的「加持」之下,我延續少年時代的夢,在政大初譜我的新聞人生三部曲的首部—學新聞。當然,我不是完成「土耳其學」的學習和在博雅人文教育的學習初立基礎之後,才開始研習新聞傳播的,而是從大一開始就同時並進。
這人生三部曲的第一部,譜得很長久、很辛苦、也很有趣。初階段學習新聞學、傳播學、中外新聞史及新聞編輯與採訪,是在政大大學部新聞系(1966–70),重㸃是基礎理論及編採實務養成等打樁工程;進階學習是同校新聞研究所(1971–74),聚焦於各類型傅播效果研究、及媒體在新事物傳播過程中的角色及功能之研究;在美國紐约大學的進階研究(1978–82),則聚焦於國際資訊傳播與國際關係及國際經濟NIEO學派(New I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的互動。民國76年返台提任《中國時報》總編輯,面對傳媒從傳統類型轉型到網路及社交媒體的劇變,基於編務之需及個人興趣,從事當代傳播問題的研究,以迄於今。
如果問我在漫長的新聞傳播學習過程中,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領域是什麼?我會説是有關傳播效果的研究。回憶五十餘年前,師承傳播學大師徐佳士教授的指引,開始捧讀加拿大哲學家麥克魯漢的經典名著《理解媒體》、《媒體即訊息》等,從其所作「媒體直接對(受眾的)神經系統施展魔法或傷害」的論述中,激發我研究台灣各類型傳播效果的熱情,尤其著重傳播效果對政府施政的影響。具體事例是民國62至63年間,在楊孝濚教授的指導下,以當年猶屬創新的「社會調查法」從事「大眾媒介與親身接觸在台灣農村家庭計劃消息傳播中角色」研究,藉以瞭解媒體對政府施政傳播效果影響之比較,並探討若干歐美當時的傳播理論,在台灣農村家庭計劃消息傳播過程中的適用性。
 美國哥大校長波林傑(圖中)來台作「大師開講」,以法學權威的觀點,強調媒體要善盡社會責任,媒體工作者對新聞專業教育和人文博雅教育應該並重。演講後參加與談者左起曾志朗教授、殷允芃發行人、成露茜教授(右),黃肇松(右二)參加對談,並協助主持。 (圖片/作者提供)
美國哥大校長波林傑(圖中)來台作「大師開講」,以法學權威的觀點,強調媒體要善盡社會責任,媒體工作者對新聞專業教育和人文博雅教育應該並重。演講後參加與談者左起曾志朗教授、殷允芃發行人、成露茜教授(右),黃肇松(右二)參加對談,並協助主持。 (圖片/作者提供)
清風明月 吾與子之所共適
從事學術探討的青年學子,一般説來是寂寞而清苦的,但有時也有令其欣喜的收獲。我的經驗可提供作一實例。民國63年夏,我把研究結果撰成論文獲口試通過,碩士學程結束。論文於同年獲「董顯光新聞獎基金會」頒予優秀新聞學術著作獎;政大新聞研究所發行之「新聞學研究」半年刋於同年底摘要刋登;翌年獲教育部發給「青年著作發明獎」著作類優等獎;民間基金會則於民國70年補助出書,由「中國出版社」出版。

連串的鼓勵,支持我繼續從事相關之新聞傳播學術研究的心志,也讓我像撿到了幾顆石頭,可向新聞媒體「投石問路」,展開我新聞人生三部曲的第二部—做新聞。
天從人願,是每個人最髙的期望;一帆風順,是對親友最大的祝福。但如西諺所云「預測是危險的行業」(Prediction is risky business) ,世間事總是曲折難料,就像我在政大畢業後,没到土耳其深造或擔任駐土記者;學業完成後,没進媒體,卻進了新聞局,並在若干年後派到紐約;同様想不到的是,大學畢業12年後,還是進了報社工作,而且是参加《美洲中國時報》在紐約的創刋。
末了,請容再引用蘇軾《前赤壁賦》的一段:「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為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明月清風蘊藏無限、變化多端;知識學問亦復如此。回顧半世紀前「學新聞」階段的「學校治學」和「稻田治學」,其後「做新聞」階段的「公職治學」、「報社治學」、「編採治學」;晚近十年走入校園「教新聞」階段的「授課治學」和「研究治學」;以及自幼迄今横貫大半生的「寫作治學」,都經歷漫長歲月,也在理論和新聞實務工作的相輔相成,融合共「治」之下,成為「吾與子之所共適」。無論是得是失,我都至感慶幸和感恩。
《 作者素描:黄肇松 的唯一:新聞 》
黃肇松「矢志新聞工作」,是從小學五年級投稿《國語日報》學府風光版開始;省立苗栗中學初中部期間任《青年戰士報》校園記者;髙中時任《中央日報》苗栗特約記者,並任《苗中青年》總編輯及《香港工商日報》市聲版特約作家,是黄肇松少年時期對新聞採、寫、編的探索。
考入政治大學東語系讀語文,常常出現在政大新聞舘,把新聞系當「輔系」,後考入政大新聞研究所的「正途」,為其後的新聞工作紮基。
黃肇松的「廣義的新聞工作」,從通過髙考,進入行政院新聞局開始。為國內外的媒體記者提供資訊服務,歷任科員、編審、科長及駐紐約新聞處一等秘書。
1982年轉入中國時報集團在紐約創刋的《美洲中國時報》工作,歷任主筆、編譯主任、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後任《中國時報》駐紐約特派員。前後在紐約從事新聞相關工作11年。
1987年返台,開始他在台灣大開大闔的新聞實務工作。先後任《中國時報》副總編輯、總編輯、社長,中時報系總管理處執行副總經理、總經理,常務董事兼《時報周刋》董事長。2008年從時報退休,任職27年。其後,先後被聘為中央通訊社董事長、《台灣中華日報》董事長。其間曾獲世新大學聘為專任客座教授,執教六年。
從嚮往新聞到讀新聞、做新聞、教新聞,一以貫之,新聞,是黄肇松的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