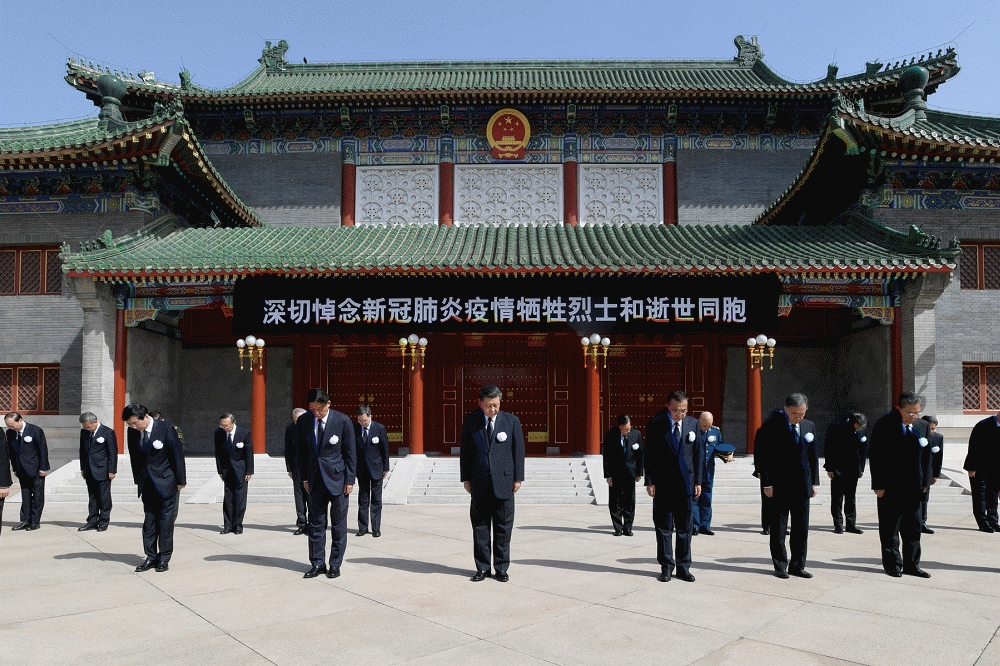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日本航空系統遭網攻 國內、國際航班受影響 2024-12-26 10:39
- 最新消息 柯文哲遭求刑28年6月 台北地檢署完整起訴內容曝光 2024-12-26 10:30
- 最新消息 快訊/柯文哲涉收賄、圖利、公益侵占遭起訴 北檢求刑28年6月重刑 2024-12-26 10:13
- 最新消息 直播/北檢10:00記者會 說明柯文哲涉「2大案」完整內容 2024-12-26 10:00
- 最新消息 松菸快閃!《賽馬娘Pretty Derby》繁中服 2.5 週年活動開跑 登入就送 10 連抽 2024-12-26 09:56
- 最新消息 【《陳情令》CP】王一博新歌預告曝光 被抓包與《慶餘年》肖戰隔空放閃4細節掀暴動 2024-12-26 09:55
- 最新消息 暴風雪侵襲東南歐地區 波士尼亞20萬戶寒冬中連2天電力中斷 2024-12-26 09:52
- 最新消息 快訊/京華城弊案偵結 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押抵北檢 2024-12-26 09:50
- 最新消息 台北市跨年舞台意外!工人未用安全帶墜15公尺亡 市府一度下令停工 2024-12-26 09:28
- 最新消息 俄羅斯貨輪地中海爆炸沉沒 俄物流企業稱遭恐怖攻擊 2024-12-26 09:18

中共與中國是一體的,那種試圖將中國與中共分開的做法——中國是好的,中共是壞的——早已跟今天中國的現實嚴重脫節。(湯森路透)
中國是一個黑洞,將你的聰明全部吸走
2020台灣大選之後,西方左派公共知識分子伊恩·布魯瑪在臺北的新書發表會上,提出「華人國家治理的新可能?」這個已然脫離台灣社會現實的「過時的問題」。
在這場選舉中,布魯瑪當然察覺到了台灣選民強烈的台灣自決意識,以及蔡英文獲得八百一十七萬票背後的「抗中」因素(蔡英文並非魅力型領袖,在前一個任期內也沒有靚麗的政績,此次大獲全勝,除了對手太弱,還有無償擔任其競選總幹事的習近平幫了大忙)。這使布魯瑪在談及Chinese一詞時,呈現出某種難以明確定義與理解的尷尬——政治中國?地理中國?族裔中國?文化中國?他說的是哪一個中國?而這些不同面相的中國,可以明確區分開來嗎?訪談者寫道:連布魯瑪自己也如此感覺,自嘲得就此打住其主體演講,進入問答環節。然而,第一位發問的讀者,偏偏大膽追問,布魯瑪對Chinese的定義究竟為何?
布魯瑪只是搖搖頭,稱台灣人不必要拒絕Chinese。他進一步表示,反對這個詞彙,只會讓中共更加主張它是更具正統性的政權,更具有正當性,「你如果反中共,就是反中國」。他認為如此一來,反抗中國的行為只是更落中共的口實,將民主自由的一切都視為「外國勢力」。
這種解釋極其荒謬——難道一個兇悍的強盜闖上門來對你說,你必須承認我是你的爸爸,否則我就殺了你;而你為了避免與他發生衝突、避免讓自己受到傷害,就逆來順受地叫他爸爸嗎?難道僅僅為了避免讓中共獲得所謂的「口實」,就讓自己永遠處在「中國」的陰影之下動彈不得嗎?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混賬邏輯?
可以駁斥布魯瑪的一系列事實是:中共對台灣、香港、東突厥斯坦、西藏的吞併野心和實質性的暴政,總能找到「口實」,甚至連「口實」都懶得找就直接出兵。西藏與中共簽署了《十七條和平協議》,一旦解放軍完成兵力部署,就大開殺戒,一紙協議被束之高閣,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從此被剝奪殆盡;在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之前,百分之九十九的香港人從未有過「港獨」思想,他們認為有《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保障,至少基本人權不會被剝奪,然而數以百計的香港年輕人卻遭到香港員警及潛入香港的中共秘密員警的屠殺。
民主和自由確實是外來物,不是中國自生的。所以,自由人既要反共,又要反中國,這沒有什麼錯。中共與中國是一體的,那種試圖將中國與中共分開的做法——中國是好的,中共是壞的——早已跟今天中國的現實嚴重脫節,幾乎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國人都支持中共對台灣、香港、東突厥斯坦和西藏動武。中共不是一個依附於中國肌體上的、尚可切除的癌細胞,中共就是流淌在中國血脈裡的血液,你能把血液從一個病人的軀體中全部清除、再讓病人復原嗎?
任何人,即便是像布魯瑪這樣的學富五車的西方學者,一旦被大中華、大一統思想沾染,照樣變成失去理性和常識的白癡。中國就像一個深不見底的黑洞,將你的全部智慧和判斷力統統吸走。
儒家文化與民主自由相容嗎?
布魯瑪不至於愚蠢到為中共的暴政辯護,他跟很多西方左派知識分子一樣,在批評中共的同時,對中國文化懷有一廂情願的想像。就像到中國訪問之前的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一樣,以為中國遍地都是李白杜甫,白衣飄飄的詩人;來了之後才發現,中國人隨地大小便,騙子小偷比比皆是,最後得出結論「中國就是猥瑣、殘酷、貪婪、髒亂」。但布魯瑪連芥川龍之介的觀察能力都不具備,他到過中國很多次,仍然癡迷於中國的崛起和中國的文化。他的推論方式是,共產黨固然很壞,但儒家文化是好的——而且正因為共產黨打壓儒家文化,更說明儒家文化是好的。
布魯瑪反對「儒家文化必然導致專制」的觀點,他的第一個論據是從儒家文化內部尋找反叛思想,「他們會說儒家思想就是要服從,卻罔顧孟子提過人民有權反抗政府一事」。他的第二個論據是,在所謂的「儒家文化圈」中,也有若干成功實現民主化的例子,「台灣和香港的華人已經證明瞭,華人文化並沒有一定要接受集權或民主政體的內在文化必然性」。依其新作《亞洲主題樂園》所述,台灣與香港皆被置入華人的脈絡裡,即使是韓國,也同樣位在儒家文化圈中。布魯瑪指出,韓國人來自同樣的儒家傳統,甚至是特別極權式的版本,但他們成功爭取到較為自由的政治體制。

布魯瑪的這兩個論據都站不住腳。第一,孟子確實說過「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等名言,但這些觀念並未成為被中國各階層認可並實踐的公理,乃至憲政之基礎。暴君朱元璋直接將《孟子》中他看不順眼的話刪掉。反之,在西方,君權民授觀念深入人心,君王在上帝法和自然法之下,違背上帝法和自然法的君王,被民眾罷黜乃至誅殺,符合上帝的公義。正如索爾茲伯裡的約翰(John of Salisbury)在《論政府原理》中所說:「誅殺一位公共的暴君是合法的和光榮的。」中世紀偉大的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亦指出:「特別是在一個社會有權為自身推選統治者的情況下,如果那個社會廢黜它所選出的國王,或因他濫用權力行使暴政而限制他的權力,那就不能算是違反正義。這個社會也不應為了廢黜一個暴君而被指責為不忠不義,即使以前對他有過誓效忠誠的表示也是如此;因為,這個暴君既然不能盡到社會統治者的職責,那就是咎由自取,因而他的臣民就不再受他們對他所作的誓約的拘束。」如果說孟子的話只是他個人孤獨的洞見,那麼約翰及阿奎那的思想則成為西方憲政的根基。
第二,台灣、香港、韓國的現代化的文化資源不是來自於儒家傳統或所謂的「亞洲價值」,而是來自於西方,尤其是英美的憲制傳統,他們都接受過漫長的西方(明治後的日本也是西方之一員)的殖民統治或在冷戰中受美國的庇護(同時也受美國的政治改良的壓力)。當然,這些地方確實也深受中國儒家傳統的影響,但儒家傳統帶來的是負面的影響,這些地方的民主自由制度目前仍然存在若干的缺陷或局限,很多都與儒家傳統有關。它們的民主的深化,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進一步去儒家化。
民主自由跟基督教沒有聯繫嗎?
布魯瑪在此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一個政權將自己的正當性建立在民族或某些意識形態上,反抗者是否也必須使用替代的意識形態來推翻?「如我剛才所說,中國一直是政教合一,若反叛者想要推翻某個政權,就會高舉另一種宗教或意識形態。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正是如此。」他舉的例子還包含中國異議分子。這些異議分子多信仰基督教,有人甚至成為牧師,他們的經驗信仰使他們相信民主自由與基督教是連結在一起的,甚至做出如此推論:如果中國要改變的話,就應該讓所有人都信仰基督教。「他們藉由基督教信仰與西方文化的觀念,來對抗中華文化的價值與制度。」布魯瑪表示,他雖可以理解這個想法,卻也反問:這之中是否有什麼誤解?
作為西方左派,標誌性的思維方式就是相對主義和多元主義,即否定西方民主自由制度背後有一個偉大的基督教傳統。他們連韋伯在社會學意義上論證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也不願承認,他們只承認啟蒙主義和進步主義的價值。他們對基督教的反感,甚至超過了對納粹和赤納粹的反感。
這種相對主義和多元主義認為,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不是普世價值,各種價值體系和文化傳統是平等的,沒有真理與謬誤,也沒有善惡之分,即便是食人族的食人習俗也應當得到充分尊重——當然他們自己是絕對不願成為食人族的盤中餐的,誰被吃掉也不是他們考慮的問題。這種所謂的「平等的正義」是羅爾斯的發明。美國思想家艾倫·布魯姆批評說,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將一視同仁當作一條道德律令,因為它與歧視相對立。「這種蠢話意味著,不應當讓人們去尋找人類的本然之善,就算找到了也不應當加以推崇,因為這種發現也伴隨著對惡和相應的鄙視態度的發現。」這種想法應用到當下的輿論場域中,就是咬定「武漢肺炎」或「中國病毒」這類「實事求是」的命名是「地域歧視」或「種族歧視」。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法國尚慕蘭里昂第三大學學者蘇哲安早前譴責,香港學者袁國勇批評中共對武漢肺炎處置不當的文章構成「殖民種族歧視」,並於網上發起聯署要求校方調查。
在西方,質疑他人的宗教信仰既不禮貌,也不「政治正確」。中國的人權捍衛者們信仰基督教,首先是他們個人生命的抉擇,是他們應當得到尊重的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居然受到布魯瑪的質疑和調侃,甚至用洪秀全的天平天國運動來刻意妖魔化,這一點也不紳士。以布魯瑪對中國的研究,難道不知道太平天國並不符合基督教教義,根本就是東方薩滿教及偶像崇拜結合的怪胎?如果中國的人權捍衛者信仰的不是基督教,而是佛教、儒教乃至形形色色的民間宗教,大概布魯瑪要為之歡呼雀躍了吧?看來,左派的宗教信仰自由,是不包括信仰基督教的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改革對現代民主自由的影響並不比啟蒙運動小,布魯瑪曾經獲得伊拉斯謨獎,難道他不知道這位人文主義立場的宗教改革者在思想史是上的貢獻嗎?以美國為例,美國固然沒有國教,但美國是清教徒創建的「山上之城」,基督教為美國提供了某種類似於「公民宗教」的精神背景,正如艾倫·布魯姆所說:「憲法不僅是一套統治規則,而且有著在整個合眾國實現一種道德秩序的內涵。」不承認這一前提,西方文化將無以為繼。
左膠的最大之惡就是不顧事實和真相
時常寫文章批評川普政權的布魯瑪忍不住高聲大呼:在台灣的選舉場合,竟然看到有人揮舞美國國旗,「而且不少香港人跟台灣人支持川普,成為他的粉絲。不可思議!」他不以為然地說:全世界只有這兩地的人會挺川普這樣的人——這當然也是源於中國因素。
在這裡,布魯瑪又犯了幾乎所有的左膠都會犯的錯誤:枉顧事實和真相,用他們的抽象的原則和情緒的好惡去判斷人物和事件。反對和批評川普當然沒有問題,是個人言論自由的一部分。但是,反對和批評所依賴的是事實和真相,而不是道聽途說的傳聞或者「Fake News」,更不應當為了維持自己「想像的烏托邦」的完整性,就像駱駝一樣就頭埋在沙堆之中。
如果真如布魯瑪所說,全世界只有絕望的台灣人和香港人會支持川普、成為川普的粉絲,也就是說,所有美國人都反對川普,那麼川普為什麼在大選中獲勝呢?而且大部分川普的反對者都接受這一選舉結果呢?布魯瑪是記者出身,他真應當到美國各地走一走、看一看,特別是到紐約、新英格蘭和加州之外的美國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川普造勢活動現場熱烈的氛圍——當然你可以指責說川普的支持者是愚民,是烏合之眾,是被川普催眠,是民粹主義。但是,你無法自圓其說的是:為什麼支持你所支持的政治人物,就是睿智、理性、正確的判斷;而支持你所反對的政治人物,就是白癡、情緒化和失敗者——這就是希拉蕊在競選中對川普支持者的「道德謀殺」和「人格謀殺」,她很快意識到自己的失言並迅速公開道歉。沒有想到,布魯瑪又犯了跟希拉蕊一樣的錯誤。
台灣人和香港人對川普的支持不是沒有理由的,毫無「不可思議」之處。台灣和香港面對著巨無霸一般的中國,單單靠自己的力量無法撼動這個可怕的敵人。而川普政府是三十年來對中國最強硬的政府,對台灣和香港的關注及諸多政策法案亦遠超過「只說不做」的歐巴馬政府。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和尊敬,台灣人和香港人並非布魯瑪所想像的那種傻瓜。
而且,在世界範圍內川普的支持者也越來越多。川普主義代表的是對全球化和世界主義的放棄,是重新以民主國家和價值為中心。這當然是被視為「新世界主義」的代表人物的布魯瑪不能接受或不能理解的變化。中國評論人許知遠將布魯瑪與奈保爾相提並論,其實兩人的基本立場是針尖對麥芒:奈保爾是西方中心主義者,捍衛「我們的普世文明」,對「第三世界」的批判從來不假辭色;而布魯瑪者是西方價值的解構者,不承認文明與野蠻是有差別的,更願意給予東方或中國之類的宏大敘事以「同情的理解」。布魯瑪曾經寫過若干關於歷史和政治的暢銷書,在西方享有相當的知名度和聲譽。但是,他對當下東亞情勢尤其是中、港、台狀況的觀察和評論完全錯了,而且錯到「不可思議」的地步(用他的原話來說)。這只能說明,任何人過去的知識和榮譽都不足以支撐他對新時代做出正確判斷,如果他不及時調整自己的觀念秩序,如果他不懷著謙卑的心去觀察和對話,他就不能避免自己從先知淪為笨蛋。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