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勞發署輕生公務員用輪椅送醫遭質疑 新北消防局說明原因 2024-11-22 18:20
- 最新消息 網友亂槍掃射謝宜容娘家 受害業者:別成為另一個霸凌者 2024-11-22 18:00
- 最新消息 2024《讚讚盃》12月火熱開打,即日起開放全台《傳說對決》電競好手報名 2024-11-22 18:00
- 最新消息 【金馬61】《漂亮朋友》奪觀眾票選獎最佳影片 中國導演耿軍盼「入圍就能在台灣上映」 2024-11-22 17:59
- 最新消息 北市府長官斥下屬「說明個屁」挨告 法院駁回:有失莊重但不算侮辱 2024-11-22 17:47
- 最新消息 蔡英文與加拿大政商學界餐敘 盼台加合作更有韌性 2024-11-22 17:34
- 最新消息 北市社會局也有職場霸凌? 市府澄清:投訴信內並未提及 2024-11-22 17:19
- 最新消息 陸軍無人機反制系統第三次開標 仍只有兩家廠商投標 2024-11-22 17:15
- 最新消息 《珠簾玉幕》劉宇寧虐戀趙露思爆紅 他客串《斗羅大陸》第二季「海神」造型曝光帥翻 2024-11-22 17:08
- 最新消息 全民通話北京都能聽到 美參議員:「鹽颱風」電信入侵史上最嚴重 2024-11-22 17:08

任何對毛時代文藝政策略有接觸的人都知道,那就是個黨指揮筆的時代,一個著名作家公開呼喚「指引者」(毛),不得不說是奴性的流露。(一尊打造中的巨型毛澤東雕像/湯森路透)
中國文聯、作協代表大會最近召開,這兩會一向是中國部分官方作家表忠心、獻諛詞的重要舞台。今天在政治強人領導的氣壓下,後者更賣命演出是最正常不過的,只是當「習總書記是我們的讀者,也是我們的朋友,當然也是我們思想的指引者」一語出自大陸唯一一位諾貝爾文學獲獎者、小說大家莫言口中的時候,我們還是被震驚了。
「思想的指引者」,任何對毛時代文藝政策略有接觸的人都知道,那是黨指揮筆—「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的變奏。但在文學強調精神獨立、不附庸意識形態的今天,一個著名作家還公開呼喚「指引者」,不得不說是奴性的流露。
不必以莫言身居高位來替他辯解,說什麼他言不由衷,莫言一貫的紀錄都顯示他絕非一個潔身自愛的「莫言」者。獲諾貝爾獎之前他曾參與抄寫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那是一份把大陸作家藝術家思想禁錮為宣傳工具的圖騰性文獻,作家抄寫它無異於馬戲團的動物舔鞭。獲獎之後他說了許多個「故事」,講人應該有不哭的權利、講向帝王脫帽鞠躬的歌德比不讓路的貝多芬更有勇氣…
作為一個講故事高手,莫言善言。在脫帽致敬勇氣論中,他把向權勢致敬偷換成向世俗致敬,為前者辯護;在新聞檢查論中,他把新聞審查比喻為機場安檢,偷換成對新聞真實性的確證檢查,為前者尋找合理性;在聲稱譴責哭泣時,他把為現實之殘酷哭泣偷換成洗腦下為虛假宣傳哭泣。
大家想必也記得他在獲獎時對著西方媒體替在囚的劉曉波說過兩句好話,但不多人知道,他還有一首詩和劉曉波有關。「唱紅打黑聲勢隆,舉國翹首望重慶。白蛛吐絲真網蟲,黑馬竄稀假憤青。為文蔑視左右黨,當官珍惜前後名。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這是莫言寫給薄熙來掌權下的重慶的。
天上有兩個太陽
詩言志,這首詩裡面有莫言真性情的流露。不說首聯他對重慶大吏的阿諛,頸聯就流露出其對擁有新式話語權的網絡自由的不滿,對非犬儒者的不滿—「黑馬」二字,熟悉當代中國文學的人都知道,那一度是專指劉曉波的,後泛稱像劉那樣的不羈者。所謂「蔑視左右黨」的孤傲,原來不過是為引出後面「當官」的竊喜;最後兩句刻意拔高,俗套之餘,不免讓人想起郭沫若那首寫給毛澤東那首「天上有兩個太陽」。
因此莫言在「兩會」講話一出,我的第一反應就是「中國從來不缺郭沫若」。但莫言不如郭沫若自我洗澡得徹底,他畢竟是一個大作家。莫言獲諾貝爾獎時,我曾斷言:是莫言而不是莫言的作品更令一個中國讀者驚嘆而反思。莫言,是他那一代中國人的典型、集大成者,包括其老實與圓滑,其忍辱與耍潑,其充沛與虛無,其應聲與沉默,其謹小慎微與磅礴—這一切在他自身和作品身上混雜而生。
這樣活著未免太痛苦了。誰是造成他的痛苦的人?他本應該可以像其他大作家一樣痛快生活、直面自由的欲望,他本來可以把用來敷衍領導的時間用來寫作,為什麼要活得這麼憋屈?莫言和莫言們自己都應該知道,施壓的不只是那叫他莫要言的人,還包括自己的怯懦。
怯懦者總是以為自己可以面對抉擇聰明過關,像這次兩會講話,莫言前面耍了一個小說家的花招:他說「習總書記關於文藝的講話能夠讓很多文藝工作者感覺到:讀到會心處想拍案而起,有心領神會之感⋯」熟悉小說敘事學的讀者能看出,這裡使用的是傳統小說的全知全能敘事者視角—莫言竟然代入了其他文藝工作者心裡表達他們的歡欣鼓舞。這樣一來,將來要有人責問起來,莫言也可以說,這些諛詞不過是他創造的人物所言,與他無關。
但無論如何用語言變魔法,這都是在屈辱下的表演—就像郭沫若那些打油詩一樣,以郭沫若之國學功底、文學才傲,能不知道那些諛詞之可笑?只不過理應狂狷的中國知識分子,到了關鍵時刻只能裝瘋扮傻,為自己的奴顏婢膝找一個小丑自虐式的掩飾,這是他們的喜劇、文學的悲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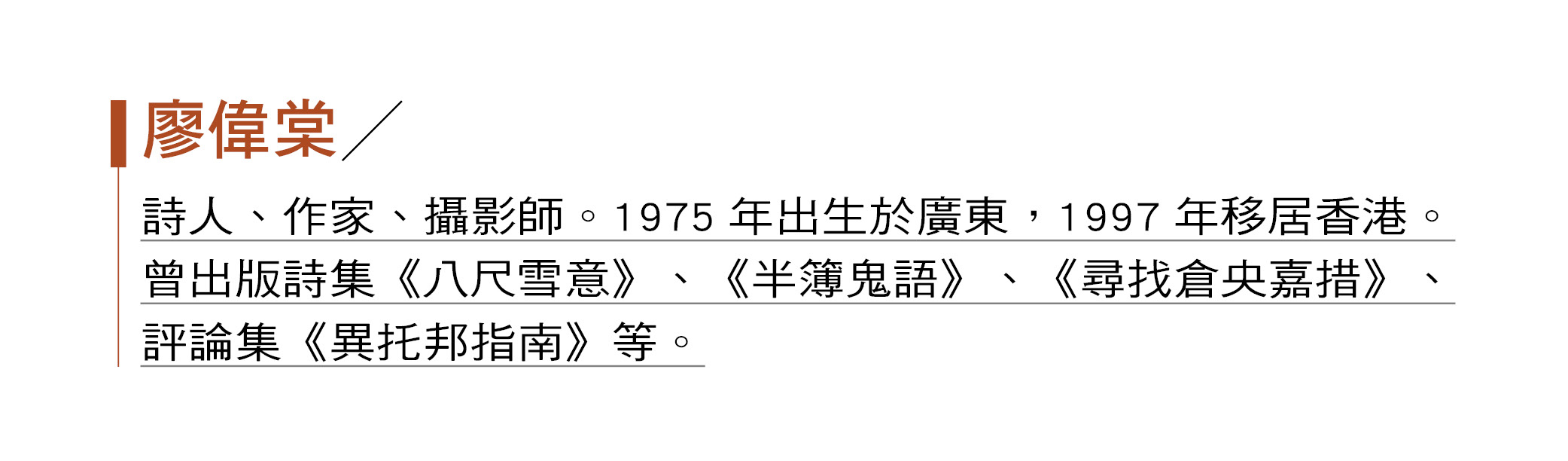
【上報徵稿】
上報歡迎各界投書,來稿請寄editor@upmedia.mg,並請附上真實姓名、聯絡方式與職業身份簡介。
一起加入Line好友(ID:@upmedia),或點網https://line.me/ti/p/%40zsq4746x。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起底謝宜容!傳身家背景雄厚「善做公關」 先生和綠營高層有交情
- 一元特典!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釋出「零星票券」,11/24 採實名制一般販售
- 【世界棒球12強賽】滿足「2條件」台灣確定晉級4強 今晚是關鍵
- 先搶先贏!Ado 五月林口體育館演唱會採實名制入場,11/19 輸入「指定代碼」可優先預購
- 陳妍希與陳曉鬧婚變疑復合 她素顏與閨蜜聚餐模樣超清純全網夢回《那些年》
- 【內幕】T112步槍裝彈器採購案疑專利侵權 以色列向軍備局寄存證信函
- 楊冪人氣暴跌與《慶餘年》張若昀演新片淪鑲邊女主 造型曝光全網夢回《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