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高爾宣 OSN、MATZKA 等超強卡司!「金色三麥啤酒音樂節」暨「超麥力音樂大賽」11/23 大稻埕碼頭盛大開唱 2024-11-22 09:00
- 最新消息 蓋茲涉性愛趴退提名 司法部長改由「佛州首位女檢總」出任 2024-11-22 08:25
- 最新消息 【有片】普丁證實用最新「榛果樹」飛彈攻擊烏國 具MIRV技術可攜多枚彈頭 2024-11-22 07:50
- 最新消息 陳嘉宏專欄:「勞動部慘案」的背後是賴政府失能 2024-11-22 07:02
- 最新消息 2024 高雄城市咖啡節週末登場!集結 60 家咖啡與甜點店 冰滴、手沖、咖啡酒通通有 2024-11-22 07:00
- 最新消息 投書:藍白已是不分青紅皂白踐踏台灣民主法治 2024-11-22 07:00
- 最新消息 投書:當APEC的C位不是美國而是中國 2024-11-22 07:00
- 最新消息 謝宜容起碼幹掉賴清德半壁江山 2024-11-22 00:02
- 最新消息 投書:立院惡鬥 只會讓更多科技人企業人不敢投身政壇 2024-11-22 00:00
- 最新消息 勞動部稱謝宜容失聯明天不出面 吳母淚控:霸凌太過分、太惡毒 2024-11-21 22:05

在這24天,這裡是作者的全世界。(圖片由作者提供)
「請問,這是我的房間嘛?」我問著剛剛打過招呼的護理師,然後我們都笑了。原來上一次進門已經是24天前了。
「不用擔心啦,至少你已經在台灣了」
那一天傍晚六點,我接到衛生所的來電,之後便開啟了一段奇幻的隔離生活。「先生,你的報告出來了,是陽性。」我下意識地先道歉。雖然我先在英國自主記錄體溫一週,確認自己沒有任何病狀才敢安心搭機返國,深怕自己也成為防疫破口,因為當時國內對於境外移入案例也議論得沸沸揚揚。「你不用擔心啦,至少你已經在台灣了。」衛生所小姐像是發現了我的焦慮,安慰著我並且囑咐著:「你記得打電話聯繫理幹事,並且請他通知派出所,否則你一出門,警察就會馬上到你家喔。」
歐伊歐伊歐伊,穿著全套隔離衣、口罩、護目鏡的醫護人員已經站在救護車旁等著我上車。第一次搭救護車的經驗,跟電影裡的畫面不太一樣,車子內裝都被塑膠袋封住了,包括窗戶。車子駛離家門時,我只能從車子後門一點點縫隙,看到被鳴笛聲驚嚇而跑出來一探究竟的鄰居們。一路上,我腦中一直回放這幾週的日常景象,車水馬龍的大街,人擠人的酒吧,突然間的一道命令,全部嘎然而止。週一還在上學的我,隔天就突然停課,再隔一天學校甚至發出了一封email寫道「Go home if you can」,那種末日感倒是跟電影裡的很像。
我試圖從記憶裡搜索被傳染的可能:是走路去學校的路上嗎?是上個月底請病假的老師嗎?是咖啡廳的店員嗎?室友?還是飛機上? 醫院距離我家並不是太遠,答案還沒解出來,救護車已經停了下來。
護理師領著我走在像是秘密通道的地方,進了電梯,從此開始了長達24天的獨居生活。走到病房的路,我已經不記得了,我低著頭像是做壞事被抓到一般,領路的護理師問著我從哪裡回來?什麼時候回來的?會不會很累?會不會很緊張?像是要我不要擔心,聊著聊著就到了我的房間 — 接下來24天都沒有離開過的房間。 護理師離開前叮嚀了我一聲「裡面有監視器喔。」


我變成一個生化武器
當天晚上,或許是時差,或許是對於未知的恐懼,只睡了三個小時就醒來。看著新聞媒體的報導,紐約的感染人數持續飆高,西班牙,義大利,英國的死亡人數也持續上升著,末日般的無力感又突然襲起 ; 幸好木質調的病房,黃色的燈光,伴著空調微弱地持續運作的聲音,讓人稍微心安一些。國外的朋友在社群分享著未來感很強的新型社交模式,有視訊聚餐的,有情人視訊約會的,雖是新奇但也隔著螢幕的見面總是少了溫度。對比台灣的朋友,行動被限制感受不到外面溫度的我,還以為我在英國,只是醫護人員都會中文罷了。
隔天一早,我房間的門被打開了,我終於聽到了一點真實世界的吵雜聲,走進全副武裝的醫師與護理師,我才發現,現在的我真的是一個生化武器。護理師輕輕拍著我,找著我的血管,我問「我的血管是不是很難找?」 他尷尬地回著「因為戴著三層的手套,手感真的完全不一樣。」醫師開始跟我講解之後的治療過程,詢問我的身體狀況,了解我的旅遊接觸史,試圖得到更多協助判斷的線索,即便他對這個病毒也很陌生。問診的過程中,我做了第一次鼻腔採檢,是一支目測約15公分的塑膠棒,從我的鼻子一路穿進去,在裡面稍微旋轉一下後抽出來,過程大概就是三-五秒鐘,但眼睛立刻泛淚。那時還不知道24天後的我,對於採檢早已經沒有不適感了,但醫生還是每次都會說「會有點不舒服,忍耐一下。」

「三個聖筊」才能出院
在病房裡度過的時間,比我想像中快很多,但每天的時間被護理師們切割得好好的:早上七點送早餐,然後量血壓及體溫,中午十二點多送午餐,量血壓及體溫,晚上六點多送晚餐,量血壓及體溫,晚上九點多,量血壓及體溫。我的一天好像被一個一個的數字切割成四份,每一份含有舒張壓 115、收縮壓82、心跳77、體溫35.8 這樣的四個數字,而我的一週被醫生四天一次的採檢切割成三份。醫師每天更新我的身體狀況,回覆我一些相關問題,也一直照顧著我在這個過於安靜的空間裡,或者是因為「生病」、「住院」這個前提下,過度放大感受而帶來情緒。台灣的採檢關主應該是目前最世界上嚴格的關主了,連續三次陰性才算闖關成功,或許是我們很習慣擲筊了吧,「三個聖筊」很有被批准的感覺。就這樣生活在「三個聖筊」的解除隔離闖關活動中度過了快一個月。
住在隔離病房裡的生活其實非常需要自我調適,原本無限的生活空間,突然被縮小到那個約4坪大的空間,不能開窗,不能出門,設置在病床上方的對講器是我對外的唯一通道,護理師們與我培養出一套搭配監視器與對講機的溝通模式。記得第二次闖關失敗當晚,凌晨兩點多我又醒了過來,突然間對講機又響了,是護理師的來電。「曾+,你有沒有想吃什麼? 什麼零食阿,飲料什麼的。 你關這麼久了,會不會很無聊?應該會想吃一些其他的吧,我明天買一些給你,你不要客氣, 餅乾?綠茶? 咖啡?罐裝的可以嗎?不要覺得氣餒,加油,晚安。」 隔天早上的早餐旁邊,多出了一大袋零食,以及一張寫著「早安哦! 加油!咱們一起努力哦,Fighting!!」的紙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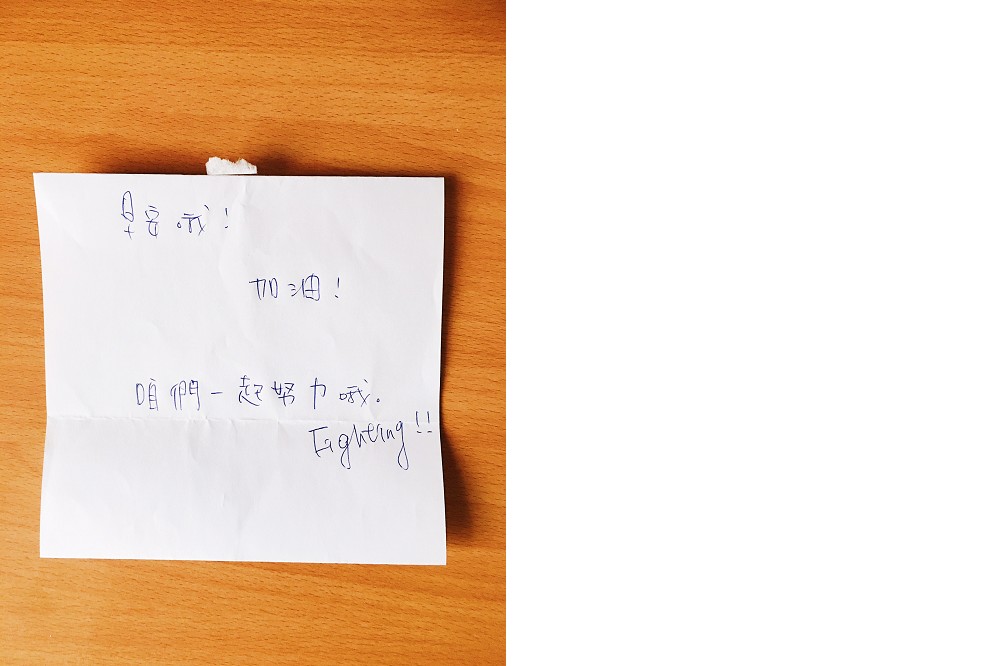
某一天我問醫生,這兩個多禮拜我好像每天都有見到你,你是不是都沒休假?他說:「為了要降低風險,所以由我一個人來看診目前所有確診病患。」每天看著醫師及護理師離開病房前繁雜地脫去保護罩,每脫一件,就得用酒精消毒一次手,再脫一件,再消毒一次手,這個回歸現實生活的儀式,非常的瑣碎,但是需要非常的仔細,因為他們必須為現實生活中接觸到的人負責。一件一件的隔離衣,一雙一雙的手套,一個一個的口罩,隔離了病毒也隔住他們或許疲憊的眼神。但我看到他們的專業,他們的驕傲。


那些非凡的醫護人員
第23天的早上,穿著白袍的醫師和一名穿著粉紅色制服的護理師推開了我的門,「原來他們的制服長這樣」我心裡獨自想著。「看到我們穿這樣進來,你應該知道是什麼意思了吧?」醫師有點神情雀躍的說著。在等待指揮官批准解隔離這段時間,我竟開始回味起這近乎一個月武漢肺炎生活,想著那一通傍晚六點的電話像是啟動了警報系統一般,動員了上至國家級的指揮官,下至衛生所及醫院,自責著自己竟動用了如此龐大的資源之餘,也看到了政府系統的縝密佈局,心中還是竄起了一股暖流「好險,我在台灣。」而這一通電話也串起了我跟這些陌生人的一些小小情感,我們像是一起打了一場勝仗,只是敵人在我的身體裡。
我的解隔離通知已經下來,隔天早餐後,我儀式性的換下病人服,穿上我的便服。結束最後一個心電圖檢查,我好奇地拿著手機拍著醫院設備,回到十樓,往我房間的方向走去,但我已經不知道是哪一間, 「請問,這是我的房間嘛?」我問著剛剛打過招呼的護理師。「對,沒錯。」,然後我們都笑了。上一次進門竟然已經是24天前了。
出院的這幾天,看著新聞各國的疫情並沒有趨緩的現象,只要不是自己一個人的時候,也是全程戴著口罩,每天酒精消毒,跟家人不同桌吃飯。精神還是很緊繃,一直以來都沒症狀的我,總還是擔心。突然想起在醫院遇見地那些非凡的醫護人員,不知道這幾個月下來是怎麼過生活的,應該也是這樣緊張兮兮的吧,在疫情尚未結束之前,這樣的生活還要持續多久呢?聽到英國,法國,西班牙,紐約,義大利等各國民眾會在某些時間點,一起為醫護人員拍手打氣,然而,在新聞上時常看到的竟是台灣醫護人員遭鄰居懷疑帶有病毒甚至排擠。我出院了,就結束這一切了,而他們只是再換上新的一批戰友,繼續作戰。
我想,我們更應該給與病毒面對面的台灣的醫護人員一個掌聲吧。


※作者為返國留英學生,確診已治癒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起底謝宜容!傳身家背景雄厚「善做公關」 先生和綠營高層有交情
- 一元特典!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釋出「零星票券」,11/24 採實名制一般販售
- 【世界棒球12強賽】滿足「2條件」台灣確定晉級4強 今晚是關鍵
- 先搶先贏!Ado 五月林口體育館演唱會採實名制入場,11/19 輸入「指定代碼」可優先預購
- 【內幕】T112步槍裝彈器採購案疑專利侵權 以色列向軍備局寄存證信函
- 王一博金雞獎典禮被抓包視線離不開趙麗穎 網揭兩人4年戀情無法曝光背後真相
- 勞動部涉職場霸凌不只謝宜容? 何佩珊:與輕生者中間還有2個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