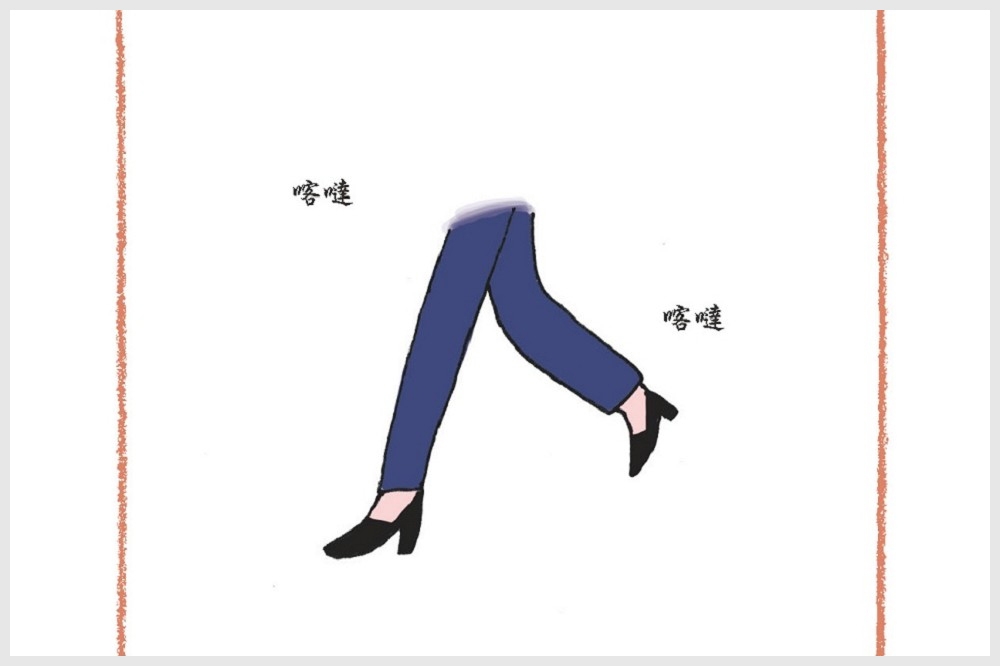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談中日關係 王毅警告:藉台灣生事就是給日本找事 2025-03-07 11:21
- 最新消息 王毅記者會提2758號決議:台灣在聯合國唯一稱謂就是中國台灣省 2025-03-07 11:06
- 最新消息 王毅強調中俄不對抗不結盟 批美「退群」恐倒退成叢林法則 2025-03-07 11:05
- 最新消息 核三廠才剛失火!台中火力發電廠傳火警 濃煙直衝天際畫面曝光 2025-03-07 10:48
- 最新消息 太空任務一日兩挫敗! SpaceX星艦升空爆炸 月球登陸器「沒站好」 2025-03-07 10:40
- 最新消息 批評國民黨把立法院「玩成屎盆子」 親藍名嘴:罷免柴火是自己添旺的 2025-03-07 10:33
- 最新消息 李孟諺婚外情閃辭後又回鍋行政院 卓榮泰親揭原因:需要治水專業 2025-03-07 10:30
- 最新消息 《難哄》白敬亭與章若楠參加朋友婚禮 「這一幕」全網夢回《偷偷藏不住》趙露思與陳哲遠 2025-03-07 10:22
- 最新消息 歐盟挺法國核武計畫 俄國說不具威脅反諷馬克宏「矮」 2025-03-07 10:03
- 最新消息 【販售通路】轉大人的第一把刮鬍刀!舒適 Schick FIRST TOKYO 刮鬍刀登台開賣 2025-03-07 10:00

標榜尊重個人、包容差異的「自由主義精神」形塑了阿姆斯特丹,引領荷蘭開啟黃金年代。(湯森路透)
第九章
「我們在此通知, 強大的德軍即將展開行動」
如果上網搜尋「安妮.法蘭克影片」,你會找到一段二十秒的黑白影片片段。它攝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的阿姆斯特丹,大約就在鮑柏.德榮寫詩給法芮達.布羅梅那時,在納粹成為恐怖夢魘前夕。這一天,一對新人在梅爾維德廣場結婚,新人有個朋友拍攝新郎和新娘離開公寓的畫面。在那段既平凡又不凡的影片中,有三個特別突出之處。第一個,也是最明顯的,當鏡頭短暫往上搖,你會看到安妮.法蘭克,剛滿十二歲的她把頭探出公寓窗戶,看著那對穿著華麗服裝的新人步入陽光中。值得注意的除了那是她現存僅有的影片之外,還有這個短暫片段其實也讓人大致了解到她的個性。幾乎每個認識她的人都記得,安妮.法蘭克好動、古靈精怪,是父母難掌控的調皮女孩。你在影片中會看到她頭突然一轉,對著屋裡某個人說了些話,應該是她的母親或父親。那是個活潑的動作,充分展現出一種態度,完全符合世人所知的她。
這段影片次而顯示的是阿姆斯特丹的新區域,由福羅爾.魏包特負責監督興建。它看起來清新、乾淨,最重要的是充滿現代感。那不是林布蘭的城市,甚至不是梵谷在一八七○年代逗留時漫遊的那座城市。我們看得出來那是今天任何人都會覺得熟悉的地方,你幾乎聽得到馬桶沖水聲,也知道夜幕低垂時住戶會打開電燈。
第三個突出之處是那生活看起來如此尋常。影片末尾,鏡頭往下搖向街道。我們看見人們在散步、騎腳踏車;兩輛汽車在街角轉彎。那是風和日麗的一天,一對新人正要出發前往自己的婚禮,其他人則偶爾注意到他們。
大約在前一年,當納粹德國開始鯨吞歐洲區域之際,荷蘭卻仍維持輕鬆的態度,這令人意外。荷蘭人相信歷史會重演,一如二十六年前,他們宣布保持中立,大部分荷蘭人也像過去一樣,認為參戰者會尊重他們的宣示。事實上,希特勒在國會的一場演說中曾誓言尊重荷蘭的立場,但隔天他卻下令入侵荷蘭,並說了一句有幾分正確性的話:「待我們攻克後,無人會提出質疑。」一九四○年五月九日晚間,即使在諸多跡象顯示攻擊行動即將逼近之際,《共同商業報》(Algemeen Handelsblad)的編輯還是非常樂觀地將一篇標題為「緊張情勢化解,預期的事件不會發生」的報導放上版面。黎明之前,在報紙上架前幾個小時,全國各地的民眾都穿著睡衣跑到戶外,看著重裝飛機從頭頂轟隆飛過。幾個小時後,德國駐荷蘭大使胡里葉.馮.柴克伯克斯羅達伯爵(Count Julius von Zech-Burkersroda)與荷蘭外交部長埃爾科.范.克萊芬斯(Eelco vanKleffens)會面。柴克伯克斯羅達伯爵是非常老派的外交家,職業生涯始於貴族式微的一九○九年。他跟荷蘭人一樣遭希特勒欺騙,而此時他的職責是向范.克萊芬斯宣讀一份宣戰電報,但因為羞恥與慌亂之故,這位伯爵外交官唸不出來。范.克萊芬斯於是拿起那份文件自己宣讀:「我們在此通知,強大的德軍即將展開行動。反抗毫無意義可言。」
荷軍於是展開強力但短暫的防禦行動,但那可能比立即投降還要糟糕。部隊對抗德軍的行動在鹿特丹郊外停頓後,荷蘭指揮官彼得.夏盧上校(Colonel Pieter Scharroo)拒絕投降,即使獲知德軍的空襲逼近也不為所動。九十架德國戰機於是投下一百多噸炸彈,引發大火,燒毀了市中心。德國軍機飛進荷蘭領空之後五天,德軍也威脅要以與攻擊鹿特丹相同的手法轟炸烏特勒支,荷蘭負責指揮的將軍這才投降,納粹占領於焉開始。
戰爭對阿姆斯特丹造成的損害並不大。一架在空中被荷蘭擊中的德國軍機投下兩枚炸彈,其中一枚落在紳士運河與布勞勃格運河(Blauwburgwal)轉角,炸毀了一棟建築,導致四十四人死亡。四天後,也就是一九四○年五月十五日,一長列的德國士兵長驅直入,占領了這座城市。荷蘭納粹黨「NSB」過去數年曾有多人遭殺害,但此時該黨黨員紛紛站在街道兩旁向納粹行禮,而其他人只是冷眼旁觀。
***
荷蘭人對納粹的協助點出了那場戰爭中一項最黑暗的統計數字。荷蘭猶太人的戰時存活率是全歐洲最低,甚至遠低於其他地區的猶太人。比方說,法國的猶太人有百分之七十五撐過了納粹時期,而荷蘭猶太人僅有百分之二十七。戰爭開始時,阿姆斯特丹約有八萬名猶太人,到戰爭結束時,估計其中五萬八千人已死亡,其中大部分都死於集中營裡。荷蘭人在不經意中以超高效率支援了一項系統性滅絕行動,消滅了自己國家的自由主義傳統。
猶太人自己也在他們對德國人的協助中發揮了作用。納粹占領者命令兩名重要的阿姆斯特丹猶太人組成一個猶太人委員會,負責將相關指令傳達給猶太人,他們分別是鑽石商人亞伯拉罕.阿斯徹(Abraham Asscher)以及大學教授大衛.柯恩(David Cohen),兩人都對德國人言聽計從。這個委員會出版一份週報,以傳達命令,例如所有猶太人必須配戴黃色星星的政令。當驅逐令開始出現時,該報也勸告民眾遵守。當然,當時無人知道遭驅逐的那些人是要前往死亡集中營;阿斯徹與柯恩說服自己,他們是在極艱困的情況下做出最好的安排。不過,就像盧.德榮所寫的:「通敵的道路︙︙是最滑溜的一條。」納粹慢慢將猶太委員會納入他們的系統,首先要求其成員只能發驅逐通知給住在荷蘭的德國猶太人,接著對象便擴及所有猶太人,然後再「建議」委員會自己列出應該遭驅逐者的名單。最後,在大部分人都被遭驅逐之後,阿斯徹、柯恩和猶太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也收到自己的驅逐通知。儘管委員會所有其他成員全死於集中營內,阿斯徹和柯恩卻活了下來;一九四七年,兩人因為協助納粹而遭猶太榮譽委員會(Jewish Council of Honor)判處有罪。
阿姆斯特丹的納粹統治者透過猶太委員會不斷緊縮對該市猶太人的束縛。首先,猶太教師遭解雇,市委員會的猶太議員隨後被迫辭職。「NSB」成員摸透狀況後,就公開展開行動,在眾目睽睽下對猶太人進行族群攻擊。一九四一年二月,北區市場舉行了一場大型會議,會中宣布這座城市要展開總罷工,以抗議當時發生的狀況。那場罷工是由共產黨所策劃,社會主義分子也共同參與。此時罷工已成為工人熟悉的手段,似乎也是一項理性的行動,不過,這次它對抗的是手法與工廠老闆截然不同的對手。那場罷工不同凡響,儘管阿姆斯特丹同樣也和其他歐洲城市一樣,存在相當普遍的反猶太主義,但它顯然同情自己城裡的猶太居民,同時也支持被遣送到德國工廠強制勞動的荷蘭工人。那是一項非凡而大膽的全市行動,德榮稱之為「人類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反大屠殺罷工」。
那場二月大罷工造成阿姆斯特丹停擺,也引起德國人注意。此時,猶太人遭受的束縛變得更緊。猶太醫生不准行醫,隨後猶太人禁止進入城市公園、音樂廳、圖書館、餐廳及搭公車。到了一九四二年三月,猶太人與非猶太人發生性關係也屬違法。五月,納粹規定所有猶太人外出時都必須配戴黃色星星。法芮達在一九四二年時正值青春年華,當我問起那些星星時,她如此描述:「每個人都有幾個星星,那是棉布製的。」我接著問:「妳把它別在外套上嗎?」法芮達回答:「沒有,我母親會把它縫上去。我記得我們出門時,她會說:『你戴上星星了嗎?』好像在問我是不是戴了帽子一樣。你想看嗎?」
我驚訝地說:「妳有?」
她在抽屜裡翻找了一會兒,拿出一小片布放在我手上。它非常薄,黃色裡帶著些微金屬光澤;互相交叉的三角形線條看起來很稚氣,彷彿是用馬克筆畫的。然而,我注意到上面寫著「Jude」,德文的「猶太人」之意,而不是荷蘭文的「Jood」。「這個不是我的,」法芮達說:「是一個德國猶太老婦人給我的。她去世後,她的朋友邀我去看看她的遺物,看有沒有我想要的東西,我要的就是這個星星。」
法芮達的母親感受到那些輕若羽毛的布塊有多麼沉重,納粹的下一道命令更增加了那個沉重感—人晚上八點後猶太不准外出。「這下我們動彈不得了,」蕾貝卡.布羅梅當時說:「我們已經落入他們的手中。」
驅逐行動在七月展開。當法芮達的名字出現在第一批要被送到「工作營」的猶太人名單上時,她的父親逼她拿砂紙搓全身。父親這個奇怪的命令竟然比納粹更讓她害怕。她聽話照辦,搓到自己身體流血,然後赤裸裸地站在浴室裡顫抖;父親仔細檢查她十六歲身體的每一吋肌膚時,她既羞辱又困惑。接著他找上有關當局,執行他的計謀—他告訴他們,他女兒感染了猩紅熱。這個騙局為這家人爭取到一些時間,法芮達獲准晚一點再報到。
贏得這場小小的勝利後,喬爾.布羅梅在返家途中因為一場「razzia」而被捕,那是對猶太人的隨機突襲,此時已成為一種恫嚇伎倆。他被兩名德國士兵拘捕,另外還有大約二十名猶太人也同遭囚禁。不過他成功脫逃,他利用士兵疏忽時逃走,丟掉他的白色雨衣,沿著之字形路線奔跑,以躲避槍火。
此時整個社區陷入恐慌。那些還沒想過、或無法躲藏的猶太人,突然間全急著要躲起來,可是躲藏地點不容易找。法芮達的舅舅路易表示他知道一個地方,但他父親不相信路易(法芮達向我形容他是家族裡的害群之馬),然而他們沒有多少選擇。路易認識一個名叫賈普.施里佛斯(Jaap Schrijvers)的男子,此人跟女兒住在二十四英哩外一處名叫華蒙(Warmond)的小村莊;施里佛斯的腳踏車店樓上有一個小空間,他願意提供「onderduik」給猶太人使用(這是躲藏起來的荷蘭文,字面意思是「下潛」)。跟大多數提供避難處的人一樣,施里佛斯也要收費。
事情一開始感覺就不對勁。當布羅梅一家人抵達時,施里佛斯見面就說:「你們是猶太人嗎?你們看起來像普通人。」
納粹占領將社會分成四個類別,如遭追捕的猶太人、吉普賽人;其他的「不受歡迎者」;基於信念或自我保護而協助納粹的通敵者;還有一小批人士,為數應該有幾萬人,他們組成活躍的反抗勢力,刺殺知名的通敵者、運送槍枝、經營地下報紙。當時最大膽、範圍最大的反抗行動是由一對兄弟所指揮—沃拉文(Walraven)與希斯.范霍爾(Gijs van Hall)。他們出身富貴的銀行家庭,二戰爆發時,兩人加入試圖在通敵與反抗之間找到中間立場的荷蘭聯盟(Nederlandse Unie)。隨著戰爭持續進行,范霍爾兄弟設法幫助那些財務最困難的人,包括寡婦、無法再領取福利金,還有躲藏起來的猶太人。沃拉文.范霍爾利用他在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的職位,作為一項祕密行動的基地,向富有的荷蘭人募款,然後分配給有需要的人。范霍爾兄弟與流亡倫敦的荷蘭政府之間保持溝通,他們達成一項協議,政府將在戰後還錢給所有捐款人。沃拉文.范霍爾設計出一種簿記機制,其中包含假股票。例如,捐款者會收到爪哇石油學會(Java Petroleumociety)的股票,最後可用來交換退款。
***
法芮達的健康逐漸惡化,被送往疥瘡病房,她在那裡遇到了安妮.法蘭克;後者同樣健康不佳,骨瘦如柴,身上還長滿疹子。這時候,為了拯救女兒,蕾貝卡.布羅梅和伊迪絲.法蘭克開始通力合作。她們的孩子一直挨餓,兩人便在營房牆上挖出一個洞,當其中一人爬進去,把設法找到或偷來的任何東西拿去餵給女兒吃時,另一個人就負責把風。法芮達.布羅梅與安妮.法蘭克因為同樣遭受恐怖凌虐而成為親密夥伴。
到了十月下旬,安妮的健康好轉,已經可以離開病房。然而,健康改善卻讓她賠上一條命。她和姊姊瑪格被送往伯根─貝爾森,結果在那裡踏上黃泉路。法芮達的諸多病痛—傷寒、胸膜炎、猩紅熱、腹瀉,反而救了她一命,讓她一直待在病房裡,直到德軍在一九四五年一月棄守奧許維茨集中營。有一天,黨衛隊的士兵突然莫名其妙地衝進病房,命令所有病患到外面開始走路。「留下來的人一律射殺!」她拖著腳步蹣跚前進,走沒幾步就跌倒在地。對我訴說那段被其他囚犯踩踏過去的回憶時,她閉上眼睛。她和其他人都認為,不前進就是死,但她卻走不動。可是,虛弱的身體又救了她一次。那些踩著沉重步伐走進一月雪地裡的人不幸身亡。她和她母親留在原地,抱在一起取暖,翻找蕪菁果腹,在逐漸腐爛的屍體之間與集中營廢墟裡撐了九天。
接著,彷彿靈異現象般,出現了一些身穿白衣、體型高大、踩著滑雪板而來的男人,他們是俄羅斯士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

作者:羅素・修托(Russell Shorto)
畢業自喬治・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家、作家與記者,擔任《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特約作家、二○○八至二○一三年間曾擔任阿姆斯特丹約翰‧亞當斯學院(John Adams Institude)院長。著有《革命之歌》(Revolution Song)、《笛卡爾的骨頭》(Descartes’s Bones)以及《世界中心的島嶼》(The Island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2/27 4D上映!劇場版《進擊的巨人》完結篇每週特典、票根活動、聯名商品一次看
- 有牌快抄!《PTCG Pocket》超克之光 3/3 千人大賽牌組推薦:戰槌利歐、阿爾帝牙
- 《難哄》白敬亭愛戀章若楠Netflix收視奪冠 兩人上節目熱舞卻因「這理由」互動超尷尬
- 《愛你》劇情開虐徐若晗因「這理由」拒絕張凌赫追求 他含淚視訊道別全網心酸
- 《難哄》章若楠戀上白敬亭獲讚「天選溫以凡」 她為戲暴瘦到41公斤內幕曝光全網心疼
- 台港限定!劇場版《進擊的巨人》3/6 4D 第二周特典「我回家了」曝光
- 《繁花》唐嫣新劇熱戀劉學義播出倒數 《掌心》鄭業成與來自台灣的「他」參演造型帥翻
- 《白色橄欖樹》陳哲遠新劇搭檔《惜花芷》張婧儀 兩人演武士虐戀盲眼公主「這畫面」超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