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黃國昌提案砍中研院預算 范雲批:為政治聲量傷害栽培過他的人 2025-01-15 22:43
- 最新消息 呂國臣陞任氣象署長 明進行交接 2025-01-15 22:23
- 最新消息 香港名作家遺產之爭!李怡之女跨海提告 二婚妻邱近思:將在記者會說明 2025-01-15 22:07
- 最新消息 英、日舉行「警戒島嶼」年度聯合軍演 展現對印太安全堅定承諾 2025-01-15 21:54
- 最新消息 警政署遭控編2千萬給「黑熊學院」 內政部:依法編列受國會監督 2025-01-15 21:36
- 最新消息 家長崩潰!全台最大寶可夢盜版商栽了 查扣市價3億偽卡爽賺4千萬 2025-01-15 21:09
- 最新消息 競選稱「24小時結束俄烏戰爭」吹過頭 川普幕僚稱可能須「數個月」解決 2025-01-15 20:49
- 最新消息 黃仁勳來台行程曝光 首站拜訪台積電、矽品台中新廠 2025-01-15 20:41
- 最新消息 【內幕】財務+司法+議會3大壓力齊聚 京華城揮刀自砍容獎爭議樓層 2025-01-15 20:10
- 最新消息 簡舒培批京華城解套「內行騙外行」 李四川:若無罪恢復容獎須回饋70% 2025-01-15 20:08

「六四」的冷酷,跟它發生在炎夏有關。(湯森路透)
「六四」的冷酷,跟它發生在炎夏有關。對於我來說,那是我少年時代最後一個夏天,那一年我學會了寫詩,在把墨污的白色飄帶鎖進抽屜的那一天開始。
少年過去後的第二個夏天,1990年,我讀到了日本詩人清水哲男的《少年》:「讓人面對火。把我帶進酒。逼我坐在花前丶坐在永遠年輕的時間前面。
我十二歲。戴著紅眼鏡。已經無法相見的年輕的雙親安睡在鋪滿小碟的屋裡。我為著什麼希望而工作?潮濕的流星。人要過了十二歲真無可救藥。牙齒間的風暴。水的外套。我切割時間如淚水。呵,精神,相信行走著的姿式最醜陋的精神。我脫下外套一甩,拓開婆娑流影的退路……」
日本現代詩不像俳句,沒有標示季節的「季語」,我卻能感到那一本《黃金幻想:日本現代散文詩選》里所寫的少年的季節都是夏天。詩集里最耀眼的一個詩人大岡信彷彿預言一般在1977年寫道:「一個夏天就這樣被埋葬」——四十年後,他去世的時候,我也用這個題目寫他的、少年的悼詩:
「今天就是另一天
我卻不是另一個人。
不是那個水紅色寬沿帽遮臉
走過巨大墳冢之間的少年
也不是被閃電擊落的蜻蜓
不是潛入深水中為喪子哭泣的母魚
中微子的激流每秒數萬億地
錘鍊我的肌肉使它保持美味。
除了生活,我們渴望另一種地獄
……一個夏天就這樣被埋葬
我們在一枝箭的盡頭行善。
讓她帶給你所有愛之中最銳利的一種:死。」
不過在電影里,除了宮崎駿動畫里、是枝裕和的輕喜劇里,夏天的不斷綿延擁有童年與少年的檸檬味道,很多電影的夏天都是像詩一樣殘酷的。我曾經在二十多年前、1997年香港第一個中國「國慶節」的晚上,重看姜文《陽光燦爛的日子》。真是莫大的諷刺,剛剛進入青年時代的我,突然加深了對馬小軍的孤獨丶失敗感的體會,在狂亂的夏日,茫然的自由卻令人不知所措,讓我們成為一個遊蕩於空宅丶房頂丶愛與暴力,最後在空無中沈落的幽靈。
夏天就是如此恍惚,我們在對回憶的質疑中一切都褪色丶失去,屈辱與痛苦都化作了一場嬉笑,化作了——流年的泡沫。還有什麼回憶可言呢…「那一年的陽光異常燦爛,讓我覺得眼前發黑。」馬小軍那句獨白永遠烙印了在我心裡,孤獨丶天真的人是注定要失敗的,但是又有誰能說自己是勝利的呢?
另一部我目為最偉大的華語片,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與《陽光燦爛的日子》有異曲同工的夏日激情。兩部片分屬兩岸最壓抑的年代,青春卻不可抑止地昂首衝向絕境,血性被政治風雲沖淡,最後是夏天永不結束的漫長的惆悵。黃耀明有一首不那麼廣為人知的歌《忽爾今夏》(林夕作詞)絕佳地概括了兩者,這也是我最鍾愛的一首六四潛藏主題的歌,因為它把殘酷的別離還給了少年的私情:
「那是某年驚心動魄一個炎夏
無端過去
迷離面孔
像昨天的我
曾相識而難以碰面
然後在今天 忽爾今天
再遇 這孤獨少年」
又很多年後,我從青年走進中年,看到了一部屬於憤怒中年回顧昨日的《盛夏》,裡面都是一些無法等待的人,在那個俄羅斯永不終結的夏天,我終於再遇見三十一年前那個少年的我。也許是我早已老過電影裡韓裔俄羅斯詩人歌手維克多·崔死去的年紀(1990年,28歲),甚至也老過裡面俄羅斯早期朋克搖滾明星麥克死去的年紀(1991年,36歲而已)。回看他們的隕星般的夏日時光,我更多的是豔羨而不是惋惜。
「十六歲的時候,
他學習成為一個朋克
像倫敦或者列寧格勒的某人
他不知道朋克是天然生成
咬石頭時嗑落的一地水晶。
二十六歲的時候,
他突然從pogo的人群中抽身
像一個厭倦了錯軌列車的扳道工
他不知道錯軌是上帝的需要
站在舞台上他突然想起了冥王星。
這就是我的夏天之歌,你說的夏天是什麼意思?肯定與我的不同,因為夏天的本質,就是變動不居。My heart is broke/But I have some glue——Nirvana曾經這樣唱道,如今我們也可以說「盛夏冰冷,但我有暖氣」,我們如此戲謔地回憶起那年夏天痛快淋灕的炎熱,然後一起痛哭吧,搖擺吧,回不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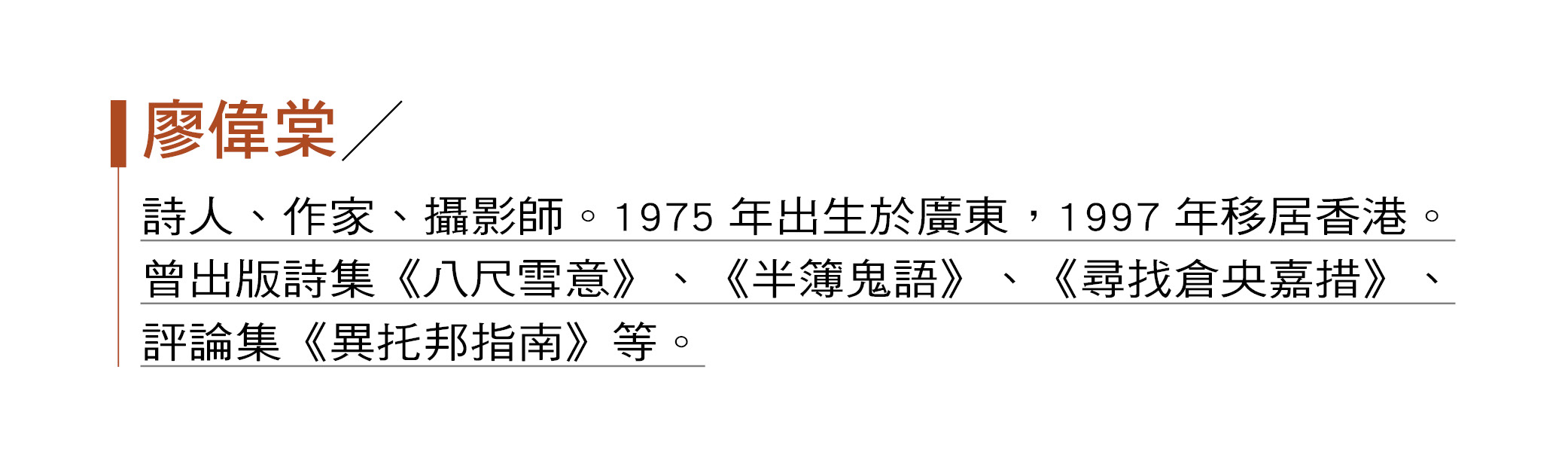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楊紫《國色芳華》播放量破2億狠甩《長相思》口碑慘澹負評 李現暱稱她「4字」全網嗑翻
- 快存沙漏!《PTCG Pocket》A2 卡包預計 1/29 推出 「洛奇亞、水君」等城都寶可夢即將登場
- 有票噴霧!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加開包廂區 1/19實名制一般售票開搶
- 不斷更新!《跑跑卡丁車》2025《大馬猴盃》1/15 32 強中國山東開打 賽程分組、賽制晉級名單一次看
- 黃牛退散!劇場版《進擊的巨人》完結篇首週特典、票根活動、聯名商品一次看
- 【微博之夜】王一博與《國色芳華》李現調換座位 竟是為了《慶餘年》肖戰內幕曝光
- 海軍承德軍艦升級外購裝備全到位 依計劃期程今年9月交艦
- 《九重紫》孟子義新劇熱戀《永夜星河》丁禹兮被看衰 原因與虞書欣、李昀銳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