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LINE Pay、Apple Pay都可以用 北捷電子支付最快10月上路 2025-01-15 19:30
- 最新消息 【2025 福袋】全聯、大潤發蛇年福袋和福箱搶先看!周子瑜同款行李箱、小時達幫你送到家 5 台豪華電動車等獎項總覽 2025-01-15 19:00
- 最新消息 出席施明德紀念午宴 韓國瑜憶和解咖啡、柯建銘提大罷免 2025-01-15 18:56
- 最新消息 2025文化幣開放領用15天 行政院長卓榮泰與三個麻瓜體驗《接招吧!決戰除夕夜》密室逃脫 2025-01-15 18:38
- 最新消息 成功打造加盟四品牌 永慶董事長孫慶餘讓店東開店給兒子女兒經營傳承 2025-01-15 18:33
- 最新消息 全台首創! 政大攜手木柵集應廟撰寫廟宇ESG報告 2025-01-15 18:30
- 最新消息 綠光經典再現!黃韻玲、林美秀睽違16年重現《人間條件四》 2025-01-15 18:30
- 最新消息 包高雄展覽館辦尾牙 永慶加盟四品牌高雄區席開600桌、頭獎抽轎車 2025-01-15 18:27
- 最新消息 賴清德明接見韓國瑜與赴美團 涉外人士曝賴「以行動釋出善意」 2025-01-15 18:14
- 最新消息 同時投入美「ATACMS」、英「暴風之影」飛彈 烏克蘭對俄實施大規模打擊 2025-01-15 18:06

新加坡大街上華語痕跡已經很淺,殘存的多數是作為一種旅遊區的異國情調。(湯森路透)
《熱帶雨》紮實飽和的情節結構(不只是那缺愛女教師與衝動男學生的禁戀劇情),一下子把我帶回我的新馬記憶裡。其實「新馬」連說很不正確,新加坡華人和馬來西亞華人對待華文傳統的態度幾乎是天壤之別,就像電影所暗示的一模一樣。
我在五年前第一次受邀去新加坡,參加新加坡作家節。與會作家只有我和大陸的阿乙是純華語寫作的,而除了邀請我的策劃人,其他作家節員工幾乎都不懂說華語,即使懂說,也會先說英語。
大街上華語痕跡已經很淺,殘存的多數作為一種旅遊區的異國情調,只有新加坡華語作家英培安創辦的草根書室及其延續城市書房、百勝樓一兩間舊書店和一群年輕人組織的詩社,在勉力維持著華語文學和新加坡華人歷史的尊嚴,令人起敬。後來我寫了一首詩《死於新加坡的幾種方式》,恰巧以熱帶的暴雨和失落的漢字貫穿:
「新加坡的暴雨總在我的身側驟下
當我睡著時它在夢以外氾濫
讓一個個漢字在雨林中長出真菌
它們比我爺爺還老,拒絕我的擁抱
一如那些灰鴿拒絕飛向苦難。
暴雨說著憤懣的閩南話
把自己包圍,在放逐的島上放逐著我
⋯⋯」
馬來西亞則不然,我也曾受邀參加檳城的閱讀節,發現此間的華語環境依然生機勃勃,無論是雜誌和新聞傳媒這樣的文化層面,還是街頭巷尾商戶的次文化層面,華語依然毫不違和地在熱帶濃豔的色彩當中顯示自己的美與活力。
兩者的對比,就像《熱帶雨》裡新加坡場景永不停息的雨天,到最後馬來西亞的場景就豁然放晴,回到馬來西亞故鄉的女主角華文老師阿玲也一洗陰霾,重展笑顏。因為她到底把漠視她存在的新加坡學校、不愛她的前夫、歧視她的前夫家庭、甚至那個莽撞的戀母情結學生,都拋諸腦後了。
困於新加坡的不只是阿玲和她代表的華語文化,還有一個獨特的角色,就是困於癱瘓軀殼的武俠片迷阿公。相聲演員楊世斌飾演的阿玲的家公,是高難度角色,因為他最擅長的「說」被設定的腦溢血革除掉了,他也基本不能動彈,他三次動,都跟華文化有關——
第一次,偉倫在阿玲家做功課,不會寫一個字打算用拼音代替,阿公努力抬起手,斬截有力地用手指在偉倫的手臂上寫了這個字:「幫」——他手指那幾下的力度,差點讓我以為他就是他天天在床上看的胡金銓《俠女》裡出走的角色。第二次,是他觀看偉倫的長拳比賽之後的鼓掌。第三次,是他目睹阿玲不堪生活之慘淡而落淚時,他轉頭示意,讓阿玲看到牆上掛著的書法:一個「笑」字。
大陸影評都強調這裡面的傳承意味,不可否認導演有此用意。但事實上,在新加坡,這深陷困境的三人誰也幫不了誰,而偉倫的長拳源自他對成龍的崇拜——不,Jackie Chan的崇拜,這跟全世界的男孩喜歡的又有什麼不同?至於「笑」字,電影自己已經給出答案,它後來被瓢潑大雨淋得濕透,簡直就像在哭。
阿公就相當於老舍的斷魂槍,說著:「不傳,不傳」,在風雨的騷動裡魂斷南洋。也許只有那個夢是真正的傳承。阿公的靈魂幻化的嬰孩,除了傳宗接代的表層意味,也可以看做那一代人(相對於他麻木的兒子、阿玲的丈夫)旺盛、魔幻的生命力,就像在黃錦樹、張貴興等馬華作家筆下的叢林鬼魅,又像胡金銓的俠客,有自己的能力穿越肉體的桎梏、穿越生死。
某程度上,阿公與偉倫是一個人的兩重生命,兩者壓抑的慾望都通過功夫的意淫發洩。而當阿公逝去,偉倫便成為阿玲身邊唯一的有情男子,兩人的情愫在雨水浸淫中漸漸發酵,超越師生的禁斷,一切水到渠成般自然可喜。那些說情慾戲是強姦的人,應該也是完全不曉得自由滋味的人,在電影的死胡同困境裡,偉倫是阿玲唯一的自由,如果不是偉倫太莽撞太急於進入分手的戲劇性,說不定阿玲還會考慮與他有所繼續。
為什麼不呢?當周圍的男人盡虛偽,好男人隨著她曾捍衛的那個文化死去,小鮮肉為何不能成為一個獨立女性的選項?
雨水在阿玲確知自己懷孕的時刻停下來,就好像終於完成播種的使命。接下來是陽光的事了,阿玲回到馬來西亞的故里,母親恍然不知那一段是遙遙向《悲情城市》的致敬,最終生育/傳承與否的決定權在阿玲手裡,在她和她母親那樣強悍地在彼邦說著鄉音,直到彼邦成為此鄉的女人身上。我在她們身上又看見了去年另一部南洋華語導演電影《菠蘿蜜》裡那個女游擊隊員媽媽的堅韌身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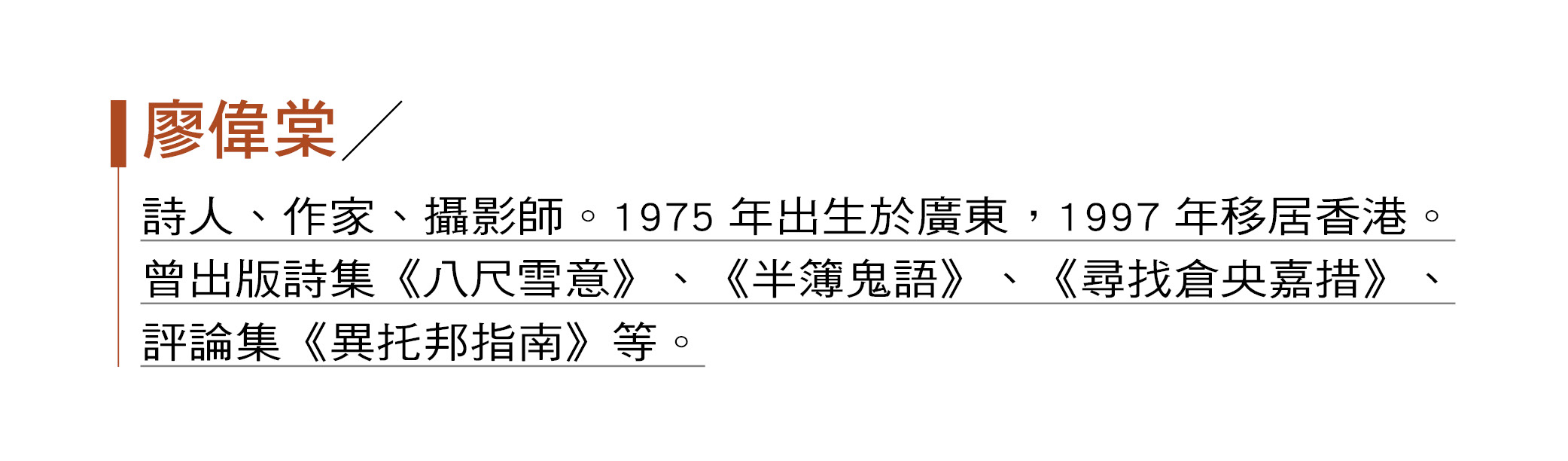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楊紫《國色芳華》播放量破2億狠甩《長相思》口碑慘澹負評 李現暱稱她「4字」全網嗑翻
- 有票噴霧!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加開包廂區 1/19實名制一般售票開搶
- 快存沙漏!《PTCG Pocket》A2 卡包預計 1/29 推出 「洛奇亞、水君」等城都寶可夢即將登場
- 黃牛退散!劇場版《進擊的巨人》完結篇首週特典、票根活動、聯名商品一次看
- 不斷更新!《跑跑卡丁車》2025《大馬猴盃》1/15 32 強中國山東開打 賽程分組、賽制晉級名單一次看
- 【微博之夜】王一博與《國色芳華》李現調換座位 竟是為了《慶餘年》肖戰內幕曝光
- 海軍承德軍艦升級外購裝備全到位 依計劃期程今年9月交艦
- 《九重紫》孟子義新劇熱戀《永夜星河》丁禹兮被看衰 原因與虞書欣、李昀銳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