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政院對川普關稅政策已有準備? 蔣萬安質疑:方案是什麼 2025-04-03 21:10
- 最新消息 直指川普關稅諸多不合理 賴清德發聲:請政院與美方強力交涉 2025-04-03 20:34
- 最新消息 民眾遭冒名簽2份「刪瑤」連署書 吳思瑤:已向檢調單位告發 2025-04-03 18:55
- 最新消息 長大後要做什麼? 日本小一生:警察和甜點麵包師 2025-04-03 18:23
- 最新消息 好市多「防試吃大隊」新制上路 入場掃卡還要補拍照被嫌麻煩 2025-04-03 18:16
- 最新消息 全中運開幕邀韓團開唱宛如演唱會 5570張票半小時秒殺 2025-04-03 17:49
- 最新消息 冷戰以來首見 美國禁止駐中官員與中國人談戀愛或發生性關係 2025-04-03 17:39
- 最新消息 新北板橋部分地區4/8將停水23小時 18里、1萬6000戶受影響 2025-04-03 17:28
- 最新消息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CP重聚】楊冪新劇二搭趙又廷 他擠走馮紹峰奪男主內幕曝光 2025-04-03 17:20
- 最新消息 【有片】木村拓哉大秀中文!對台灣這項名產驚為天人、幫忙搬道具超親民 透露有望再度訪台 2025-04-03 17:00

末次平藏旗下的末次船。(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把那群村民帶到日本的是末次平藏,他在一六二五年發生於大員灣的第一場衝突以來,就成了荷蘭東印度公司最堅定的敵人之一。他對巴達維亞的政策深感沮喪,而且又不曉得對方打算讓步,於是決定利用一項巧妙的非正統方案打破僵局。這項方案如果成功,即可望削弱該公司對於大員的主張。一六二七年,末次平藏的船長濱田彌兵衛,在距離熱蘭遮城一英里左右的新港村這座人口約有四百人的聚落當中招募了十六名原住民男子。這群村民在兩名中國通譯的伴隨下被帶往長崎,安置於末次平藏自己的住宅裡,獲得提供服裝與適當的禮物之後,再送往江戶。
這樣的做法不免引人質疑末次平藏為什麼要把一群沒有明顯可見的地位或重要性的人員一路帶到長崎,接著又送到幕府將軍位於日本中心的總部。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看看這些村民在日本受到呈現的方式。明顯可見,來自新港的這些男子不純粹只是被呈現為台灣眾多小聚落的其中一座的居民。既有的文獻顯示末次平藏著手將他們轉變為臨時大使,能夠在德川外交秩序當中扮演角色。荷蘭人在他們位於平戶的基地觀察了這項轉變,而將那群人描述為「搬弄」的大使,「被安置在他的宅邸,受到著裝打扮、訓練與指導,而且還獲得鹿皮作為他們〔進貢〕的本土產物」。
換句話說,末次平藏採取了一切做法以確保那群人能夠以外交使者應有的姿態「鄭重晉見皇帝〔幕府將軍〕」。第一步是改造他們的外表。那些村民獲得提供中國服裝以及綁頭髮的緞帶,這樣別人就「不能夠說他們是終生赤裸的民族」。使節團傳統上都會攜帶本土產品,通常是能夠代表其所屬地區的物品,用來當做呈獻的禮物。末次平藏依據這項傳統,為這支代表團提供了鹿皮這種台灣最重要的土產,另外還有一批較具異國色彩的禮物,包括虎皮、毛毯以及孔雀羽毛。這支代表團的領袖尤其受到特別重視,在當代文獻中稱為理加,他在這整個活動中扮演了中心角色。抵達日本之後,他就被稱為「福爾摩沙主要領主」(principael heer)或者「那片土地的領主」(heervan dat lant)。荷蘭人指出:「他們宣稱其中一名黑人是福爾摩沙的領主,來到日本是為了晉見陛下。」
藉著這樣的安排,末次平藏企圖喚起德川政權對於台灣島存在已久但當時仍處於蟄伏狀態的興趣。德川幕府在十年內兩度授權派遣遠征隊,就是希望能夠促使台灣派出使者,藉此將這座島嶼納入幕府將軍的影響範圍內。末次平藏置身於九州最重要的港市,必定對這兩次遠征行動有所耳聞,對於第二次行動更是絕對知之甚詳,因為那次行動的策劃者是他的其中一名對手。他也必定知道他們沒有成功,而且主要是因為台灣缺乏中央集權的政治環境,所以無法提出適當的人物。因此,將一群新港村民帶到日本的決定顯然是企圖計勝荷蘭東印度公司,提供日本政權長久以來所尋求的對象,也就是能夠為整個台灣發言的代表。藉著以這種方式呈現這群人,末次平藏的目標就是要把他們轉變為一支有效的使節團,並且由那座島嶼的領主領銜帶到日本。

這個技倆讓德川幕府更直接被拉進與荷蘭人的衝突當中。幕府將軍如果接受這支使節團的身分,而將台灣納為德川外交秩序當中的朝貢國,那麼在台灣島上只擁有一小群部隊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就難以繼續將日本水手與日本商人視而不見了,因為這代表日本在台灣擁有直接利益。此外,建立江戶與大員的外交連結也表示德川幕府更有可能會對於保持貿易航線的開放更加積極關注,即便只是為了確保台灣的使節團能夠定期抵達。不過,這一切都取決於德川政權是否願意接受這群人是一支真正的使節團,而且認為理加確實能夠代表台灣發言。
剛開始,幕府官員的反應似乎正合乎他的期望。在這群村民從長崎前往江戶的途中,他們獲得馬匹、僕人,以及一份通行證──這是個明白的徵象,顯示他們被視為真正的使節團,有資格獲得官方的支持。不過,不論這些發展有多麼令末次平藏感到滿意,情勢卻隨即因為一場天花疫情的爆發而告翻轉,這群村民有一大半都遭到了感染。兩人立刻死亡,其他人則是接受隔離等待疾病痊癒。等到他們恢復了健康之後,這群大使才繼續上路,而在一六二七年十月抵達江戶。他們獲得的接待記述於《異國日記抄》,這部文獻也記錄了荷蘭第一支抵日的使節團:
十一月五日(一六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一個名叫理加的多加佐古〔高砂〕人前來向兩位幕府將軍請安。連同他的人員,共有超過十人來到花園。理加在小遊廊上請安,呈獻的禮物是五張虎皮、二十張毛毯以及二十根孔雀羽毛。他先在主樓(本丸)請安,接著又到西樓(西丸)請安。典禮內容相同,沒有呈獻信函。這一次,來自高砂的人全都感染了天花(疱瘡),而且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存活得下來。理加也感染了天花,他在獲得接見期間的面部顏色顯得很奇怪。
表面上看來,接待過程顯得相當有利。這群村民雖然明顯感染了天花,卻在西樓與主樓(也就是德川家光與德川秀忠的官邸)都分別獲得接待。記錄中沒有敘明幕府將軍是否在場,但看來這場接見活動至少有高階官員出席。最後,這群村民獲得服裝與六百根銀條的賞賜,伴隨這支使節團的中國通譯則是獲得二十根銀條。
不過,也有些元素看起來與末次平藏精心安排的呈現方式不太合拍。傳統的接見地點是在城堡內,但這群村民卻是在花園裡獲得接待。如果假設德川官員只是想要和天花這種危險疾病保持距離,那麼這項決定當然合理;不過,此舉卻也是第一個徵象,顯示理加沒有被視為台灣的大王。更明確的證據是用於描述理加的文字:他只單純被稱為是多加佐古〔高砂〕人。他不是國王,不是領主,甚至也不是要人,而且《異國日記抄》也沒有提及這支使節團代表一個國家或是任何種類的政治結構。因此,在德川政權的眼中,這個代表團純粹只是幾個村民,從遙遠的邊疆前來向幕府將軍呈獻貢品。幕府雖然沒有拒斥這群人,卻顯然也無意將他們視為合法的大使或者為他們授予任何政治地位。
這點本身不該令人感到意外,畢竟,憑著個人的力量要打造出一支可信的使節團,能夠合乎德川幕府的期待,本來就是一項非常困難的挑戰,就算是以末次平藏的財力與人脈而言也是如此。德川政權願意協助這支使節團前往江戶,顯示接見所謂的「台灣領主」確實深具吸引力,但一看到過於簡樸的實際狀況,原本的興趣即告破滅。末次平藏沒有製造出一支堂皇耀眼的使節團,而且終究只能夠呈現出一小群感染了天花的村民,除此之外,荷蘭人又進一步降低可信度,因為他們堅稱那群村民是藉由欺詐手段被帶來日本的偽大使。
這支使節團雖然必定消耗了可觀的開支,但乍看之下卻是一事無成。結束接見之時,這支代表團的成員看起來似乎將會直接返回他們的村莊,從此悄悄被人淡忘。然而,危機卻就此升高──而且還充滿了戲劇性。此一情形的發生不是因為末次平藏或甚至是那支新港代表團的言行,而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反應所造成的結果。歸根究底,一六二七年的這支使節團其實是個製造出來的假象,目的在於迎合德川世界秩序的邏輯。就是因為如此,理加才會扮演向德川幕府輸誠的角色,以一個野蠻國家領導者的身分抵達江戶,希望臣服於文明程度較高的中心國家。不過,荷蘭人卻以另一套不同的符號解讀這支使節團,因此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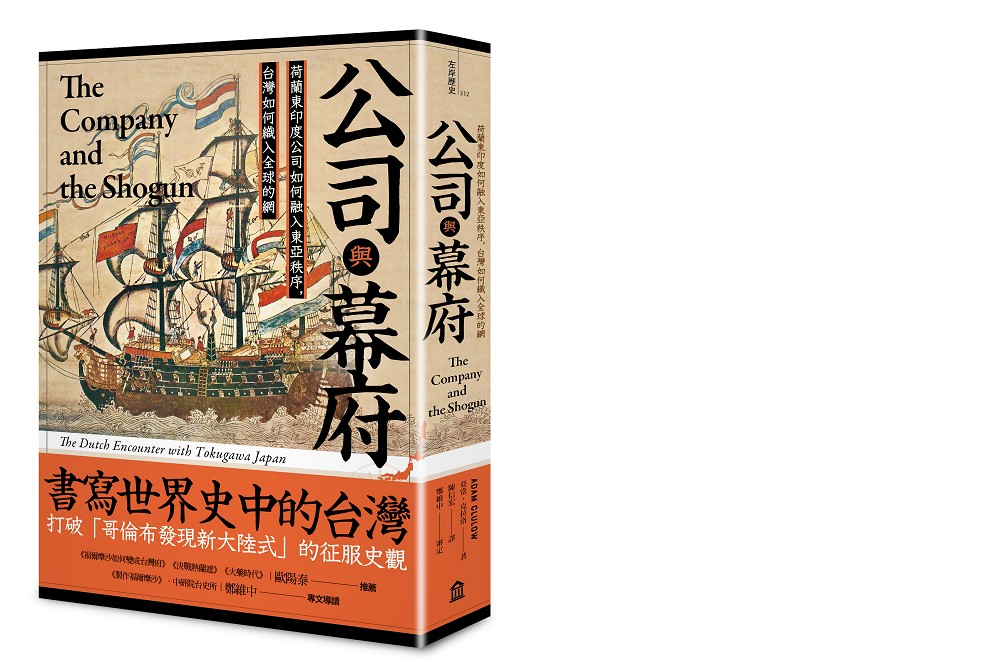
※本文摘自《公司與幕府:荷蘭東印度公司如何融入東亞秩序,台灣如何織入全球的網》(左岸文化出版)。作者 亞當.克拉洛Adam Clulow為歷史學家,目前在德州大學任教。研究範圍為近代亞洲,包括東亞和東南亞之間的跨國交易、人員流動、觀念交流等。以本書榮獲美國歷史學會頒發的Jerry Bentley Book Prize、國際亞洲學者會議的人文類獎項等等。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難哄》白敬亭直播「這段話」與宋軼撇清關係 聽到與章若楠的「藍白」關鍵詞瞬間害羞
- 《難哄》白敬亭與緋聞女友宋軼分別曬賞櫻照 他「這2舉動」卻急撇清兩人關係爆分手
- 《難哄》白敬亭潮牌2雙新鞋都與章若楠有關 緋聞女友宋軼「這舉動」遭爆與男方已分手
- 趙露思真人秀《小小的勇氣》3段話被罵「沒同理心與沒常識」 節目秒刪網友酸爆
- 陳都靈、辛雲來《雁回時》劇情慘被狂刪6集 大結局留3大謎題全網敲碗番外篇
- 【有片】中國「金屬風暴」超高速防空機槍每分鐘45萬發 火力遠超美軍方陣CIWS
- 《苦盡柑來遇見你》大結局掀淚海 劇迷怨朴寶劍戲份太少本人回應了
- 有牌快抄!《PTCG Pocket》嗨放異彩 3/31 千人大賽牌組推薦:騎拉夢、蜂貓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