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謝宜容起碼幹掉賴清德半壁江山 2024-11-22 00:02
- 最新消息 投書:立院惡鬥 只會讓更多科技人企業人不敢投身政壇 2024-11-22 00:00
- 最新消息 勞動部稱謝宜容失聯明天不出面 吳母淚控:霸凌太過分、太惡毒 2024-11-21 22:05
- 最新消息 俄烏戰況恐升級 烏克蘭是否有能力攔截ICBM 2024-11-21 21:50
- 最新消息 明後兩天各地氣溫回升 北部、東北部18到23度濕涼舒爽 2024-11-21 21:45
- 最新消息 劍橋詞典2024年度代表字出爐 「manifest」反映人們追求身心健康趨勢 2024-11-21 21:43
- 最新消息 為了9萬元勒斃馬國女大生 陳柏諺一審判賠父母逾638萬元 2024-11-21 21:32
- 最新消息 觸犯戰爭罪、違反人道法 ICC對納坦雅胡、哈瑪斯領導層發出逮捕令 2024-11-21 20:47
- 最新消息 【世棒四強賽】「CT AMAZE」自費飛東京應援 推掉台灣活動損失近10萬 2024-11-21 20:45
- 最新消息 蔡英文抵達加拿大 感謝台灣鄉親熱情接機 2024-11-21 20: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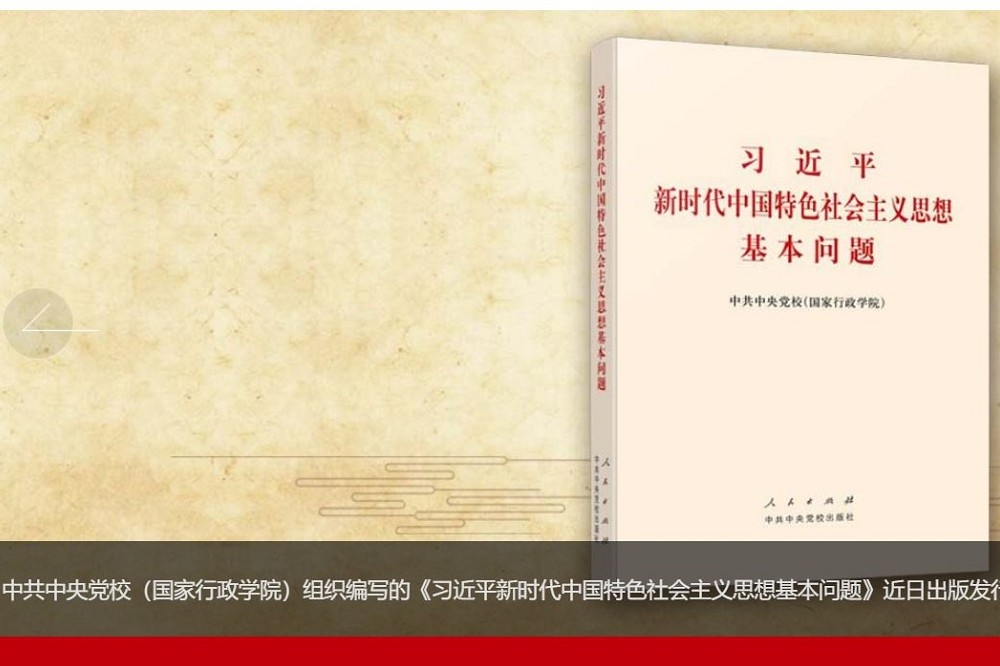
作者因為一篇點評胡溫遺產的文章,讓時任中共中央黨校的校長習近平十分「震怒」。(圖片擷取自中共中央黨校網站)
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因言論問題而被黨校問責,開除黨籍,取消退休待遇,此事近期引發海內外的軒然大波,有知道我一些情況的讀者希望我把當年被黨校「開除」的事也公開說說。一直以來也有朋友建議我把事情說出來,好讓外界看看中共的無恥。以前因為在國內,不方便披露內情,18年後來到自由世界,雖然沒有禁忌,但事情已經過去幾年了,我也不想再提舊事。
改變我想法的是前些天和國內一個朋友交流,他告訴我,黨校在傳達處置蔡老師的事情時,還提到我在紐約時報接受的採訪。紐時中國首席記者儲百亮先生問過我對蔡霞被處分一事的看法。朋友這麼一說,我能想像得到,黨校在處理蔡霞後,肯定要把國際輿論對此事的報導和反應一併關注和考慮,要它的幹部和老師警惕西方媒體拿這個做文章,攻擊中共。而我作為被它「開除」的前編制外員工,紐約時報作為一家有影響力的知名媒體,被黨校點名是不奇怪的。
既然黨校還「不忘」拿我這個前編制外員工來敲打其老師,再加上這些年來輿論把我被黨校「開除」誤當作停職,所以我決定打破沉默,也回應朋友們對我的關切。
不過我首先聲明一點,我是黨校學習時報的聘用人員,黨校對我的處理法律意義上是解聘,我尚沒資格享受它的開除待遇,這裡說的「開除」,只是通俗說法,為免有人拿這個來說事,我在標題的開除二字上特意加個引號。
外界多誤認為我是因《中國應放棄朝鮮》一文而遭黨校停職的,最早曝出該新聞的是韓國媒體,但其實這是不確切的,內情比這要複雜,涉及習近平、胡錦濤和溫家寶等中共最高領導人。

點評胡溫遺產惹習近平「震怒」
我在中共十八大前的兩月,即2012年8月底9月初,在中國「財經網」(由胡舒立的《財經》雜誌主辦)以《胡溫的政治遺產》為名,分上中下三期發表。上是談胡溫十年的成就,中說問題,下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其中引起國內外廣泛反響的是「中」部分。我在該部分談了10個問題,包括社會道德體系崩潰,意識形態破產,批評胡溫十年維穩式外交,不能利用時機推進政治改革和民主化。
或許是我在中國輿論中首次公開點評現任領導人的政治遺產,而且10大問題涉及當時中國比較敏感和尖銳的問題,加上我的身份是學習時報副編審(許多人不知道我只是個編外的副編審),而習那時是中央黨校校長,於是我被海外輿論習慣性猜測為習的智囊,習授權給我在十八大前夕有意放風批胡,試探外界反應。那段時間海外媒體蜂擁著要採訪我,包括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CNN等。國內也是爭相傳播此文。我記得報社社長在一次編輯會上談到該文的社會影響,說他去某地出差,對方一位副省級官員向他打聽這篇文章有什麼背景。當然他是從批評我的角度說的。
由於中國政治的不透明,大家習慣從權力鬥爭的角度去解讀某篇文章。特別是鑒於臨近黨代會,而中共建政後的歷次黨代會都免不了有激烈的人事權力鬥爭和路線政策分歧,習近平再過兩月要從儲君接大位,他的政治面貌還有些模糊不清,而我恰又批著黨校員工的外衣,所以外界包括中國的官員很想從我的文章裡窺探習上臺後政策的一、二點,這個我能理解。但由於拙作產生的國內和國際影響,我也就被動捲入中國高層無論是想像中的還是真實的權力鬥爭內。根據我後來的瞭解,至少有5個政治局常委批閱了拙作。據說胡很淡定,溫有些生氣,而當時主管宣傳的常委李長春,以我為黨校員工為由,將此事的處理推給習,習大概是因外界傳聞我是其智囊,為他批胡溫,怕引發後兩者對他的猜忌,為他即將的上位帶來某種變數,而對我的文章「震怒」。這兩個字是報社總編在給員工傳達黨校處理決定時(我也在場)親口講的,而他又是從黨校領導傳達習的處理指示時聽到的。
文章「中」部分發表後不到一個禮拜,我記得那天好像是週三,晚上10點,總編突然給我打電話,說我的文章惹了大麻煩,必須寫檢討第二天早上8點交來,連同報社的檢討一塊交給黨校,再由黨校轉交習辦。我想這應該是習辦的指示。報社領導從來沒有晚上給我打過電話,幸虧我有晚上不關機的習慣,否則是不是要親自派人上門?我意識到捅了大簍子,做好了被報社解聘的準備。我本來想拒絕寫檢討的,打電話徵詢朋友意見,朋友勸我還是先認個錯,說事情不一定會到開除地步。我就花了兩個小時寫好檢討,大意是文章是怎麼寫的,初衷是什麼,沒料到它會引起這麼大的反響,並裝出一副誠懇的樣子認錯,接受學校和報社對我的處理。
第二天上午我把檢討交上去,等待處分。大概過了幾天,結果下來了,按照報社領導的說法,黨校的意見要報社將我解聘,但報社考慮到如果將我「開除」,暫時沒人接我的手做版,所以想了個折中辦法,我被停職,但可以繼續做版,報紙編輯欄內不出現我的名字,而寫別人的名字,這樣就等於我這個人不存在。報社領導也警告我,如果再犯,下不為例,並給我下達一個硬規定,給外媒寫稿一律不得出現黨校的字眼,單署副編審也不行。其實黨校幾年前就這樣要求我,只是過去它可能睜隻眼閉隻眼。
我後來給聯合早報等外媒寫文章,就不再署「學習時報副編審」的身份。做了無名編輯半年後,到2013年1月,朝鮮不顧國際社會的壓力和制裁,進行了第三次核子試驗,弄得中國非常被動,社會輿論也多指責中國政府的朝鮮政策。恰在此時FT駐北京分社社長約我就此事寫篇評論,大概她之前看過我寫的朝核政策文章,文章寫好後她譯成英文在FT發表。我的中文稿作者名頭署的是中國獨立學者。她給我說FT的規矩一般是署工作單位的名頭,而不是獨立學者或評論員這類比較模糊的身份,另外我也是第一次在FT發表文章,它們的讀者遍佈全球,對我不熟,因此建議我還是署學習時報副編審,我認為她說的在理,而且我當時也不認為這篇短文能引起多大關注,就同意了。
文章2月28日在FT發表,旋即引發國際輿論的注意和重視。由於我的身份問題,外媒誤把它看作中國官方有可能要改變中國的朝核政策,而紛紛報導,那幾天外交部沒少接要採訪的電話。這事把外交部搞得很被動,朝鮮本來對中國反對其核子試驗不滿,這下更不高興,據說要中國政府說清楚是不是對朝政策有改變。外交部於是把電話打到黨校,質問怎麼回事。我知道這回肯定在劫難逃。所以,兩日後報社部門主任給我電話,告知我3月不要再來上班,我反而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事情既如此,愛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吧。

莫須有的誣構
但我沒料到報社竟然找了一個抄襲的汙名化罪名來給我戴。我不清楚這是不是報社領導不想因解雇我而要給我賠償經濟損失,因為若以在海外媒體發表不合時宜的文章為由解聘我,將面臨經濟賠償問題。我的聘用合同裡沒有因言論問題而解聘員工的規定,否則按照勞動法它要賠償我的經濟損失。我是2002年10月進入學習時報的,到2013年3月在報社服務了10年多,以當時報社的工資水準(很低),估計也要賠償幾萬給我。
大概是在3月中,部門主任再打電話給我,要我去報社。我知道這次是要正式宣佈對我的處理決定,也正好清理我的物品。來到報社後,通知我到平時很少用,報社開全體大會的會議室去。報社社長和總編以及辦公室主任三人早已坐在一排桌子後,我坐在他們對面,相隔一米,我現在還記得這個樣子有點審犯人的感覺。總編拿著一摞厚厚的像塊大磚頭一樣的4A打印紙,面無表情,說這是外面其他作者和讀者舉報你抄襲的材料,你在外媒寫什麼文章,表達什麼觀點我們不管,但抄襲影響報社聲譽,我們要對你作出處罰,解除聘用,你在這裡簽個字,然後遞給我一張列印好的紙。
說實話,我萬沒料到他們用這個理由,我已經想好,如果他們指控我違反報社要求,署了學習時報副編審的名,拒絕給我經濟賠償,我接受。我一時有些懵了,說,能不能把這些舉報材料給我看看,好讓我知道到底抄襲了誰。總編說這個不能給你看。我於是大聲抗議,你們可以說我違背報社要求,我沒意見,你們採用這手,我是不會簽字的,然後扭頭走了。
現在看來,他們要污蔑一個和他們意見不合的異議者,是沒有下限的。他們用嫖娼來指控許章潤,用經濟犯罪來指控任志強,這種骯髒無底線做法,不是今天才開始的,而是很早就這樣做。想來也真難為他們,短短幾天內,炮製這麼一大摞舉報材料,要是真有人指控我抄襲,為什麼不直接給我說?那時網路已很發達,不和我聯繫,也可以通過媒體或網路公開舉報。既然把舉報材料直接寄給黨校和報社,如果是以前寄的,黨校和報社不提醒和告知我,難道「好意」要包庇我?如果是在黨校處分我的時候寄來舉報材料,這些舉報者又如何獲知我要被處分的事?可見,分明是要誣構我。
其實他們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說,因為我的文章給報社製造了很多困難乃至影響到領導個人仕途而解雇我,我一點都不會怪罪他們,也可以放棄經濟補償,我也知道他們處在這個位置上的難處,可惜,一定要用一個莫須有的齷齪的罪名來對我汙名化,這是不能容忍的。
不知報社是不是用這個名義在員工中宣稱解雇我的,既然想到這一手,我知道他們是不可能給我賠償的,打官司也沒有用,所以最後我沒提賠償經濟損失的要求。
在等待受處分的過程中,韓國中央日報駐華記者採訪我,說不上正式採訪,只是私下朋友式電話聊天,我告訴對方我被停職了,在等待最後處理,然後他發報導我因朝鮮政策一文而遭黨校停職,這一來很多外媒又要採訪我,我都一一拒絕,我不想成為一個新聞人物。
離開報社後,我成了一個賣文為生的自由撰稿人,以為能夠不再受中共宣傳紀律的約束,可以做一個心靈自由的寫作者,殊料另一場噩夢開始,前頭一個恐懼的黑洞正等著我,要把我吸入,2018年8月我不得不冒險來到美國,恐懼才結束。這是另一個故事,以後有機會披露。
※作者是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起底謝宜容!傳身家背景雄厚「善做公關」 先生和綠營高層有交情
- 一元特典!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釋出「零星票券」,11/24 採實名制一般販售
- 【世界棒球12強賽】滿足「2條件」台灣確定晉級4強 今晚是關鍵
- 先搶先贏!Ado 五月林口體育館演唱會採實名制入場,11/19 輸入「指定代碼」可優先預購
- 【內幕】T112步槍裝彈器採購案疑專利侵權 以色列向軍備局寄存證信函
- 王一博金雞獎典禮被抓包視線離不開趙麗穎 網揭兩人4年戀情無法曝光背後真相
- 勞動部涉職場霸凌不只謝宜容? 何佩珊:與輕生者中間還有2個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