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謝宜容影片「4大疑點」曝光 拍攝時間竟比賴清德二度道歉還晚 2024-11-22 18:25
- 最新消息 勞發署輕生公務員用輪椅送醫遭質疑 新北消防局說明原因 2024-11-22 18:20
- 最新消息 網友亂槍掃射謝宜容娘家 受害業者:別成為另一個霸凌者 2024-11-22 18:00
- 最新消息 2024《讚讚盃》12月火熱開打,即日起開放全台《傳說對決》電競好手報名 2024-11-22 18:00
- 最新消息 【金馬61】《漂亮朋友》奪觀眾票選獎最佳影片 中國導演耿軍盼「入圍就能在台灣上映」 2024-11-22 17:59
- 最新消息 北市府長官斥下屬「說明個屁」挨告 法院駁回:有失莊重但不算侮辱 2024-11-22 17:47
- 最新消息 蔡英文與加拿大政商學界餐敘 盼台加合作更有韌性 2024-11-22 17:34
- 最新消息 北市社會局也有職場霸凌? 市府澄清:投訴信內並未提及 2024-11-22 17:19
- 最新消息 陸軍無人機反制系統第三次開標 仍只有兩家廠商投標 2024-11-22 17:15
- 最新消息 全民通話北京都能聽到 美參議員:「鹽颱風」電信入侵史上最嚴重 2024-11-22 17:08

電影終將迴避不了《無依之地》(Nomadland)所直面的社會問題,被鐵絲網包圍的印地安保留區,電話裡不能越境而死去的墨西哥人...(圖片取自時光網Nomadland劇照)
本屆威尼斯影展最高獎項金獅獎,被美國華裔導演趙婷奪得,已經讓人高呼意外,更意外的是,她拍攝的不是華裔導演拿手的海外華人生活糾結,而是很「窮白人」的「車居族」、「新遊牧族」(Nomadland,也是電影名稱)的人生,蒼茫率性又處處碰壁的另一種美國夢。
我尚未有機會看到這部電影《無依之地》(據說年底公映),但去年我就讀過電影原著,台灣譯作《游牧人生》,潔西卡.布魯德所採寫的紀實文學。我寫下過這樣的讀書筆記:
「這些新時代的『下流』階層最令我欽佩的是他們的自矜和樂觀。跳出他們一團糟的財務狀況,仍能發現這種生活不完全是迫於無奈,也不是自欺欺人,這群人無意之間在進行新的拓荒:在一個未知的新經濟領域裡,這個新經濟基於反對消費主義的條條框框……他們之間是相濡以沫,亦是相忘於江湖。如果說所謂的美國夢在二十一世紀還存在,這些人發明著一種從美國夢偏移而來的獨立,他們在輪子上建立了一個白宮與華爾街以外的平行美國。」
據說電影雖然走劇情片路線,但主角Fern基本忠實於小說裡的真實人物琳達,是一位雖然掙扎在貧窮線上但依然對自由、一無所有的自由抱有赤誠嚮往的初老女子。我當然非常好奇「紀實」與「虛構」之間的轉換和微妙的界線,正是後者才考驗導演功力。
未見《無依之地》,卻意外看到一部相似題材的2019年美國電影《長路簡史》(The Short History of the Long Road),導演也是女性,Ani Simon-Kennedy。必須承認,女性視角處理這種左翼題材,別有一番況味,前年意大利女導演Alice Rohrwacher《幸福的拉扎羅》和黎巴嫩女導演Nadine Labaki的《迦百農》都是能印證——膽大心細,傷口中取光是她們的強項。
《長路簡史》畫風自然細膩,講父女情克制而極其窩心,尤其想到電影在十八分鐘之後女兒真正進入「無依之地」,父親的「幽靈」其實陪伴了她接下來的每一個關鍵的抉擇——這一點讓身為有女之父的我,心有戚戚焉。老實說,這世上很多父親,活著時都不能做到這點,何況死後。
父親克林特的抉擇是什麼?就是從心所欲、不為物累,擺脫消費主義的操控順流而下。他帶著女兒過「在路上」的生活,卻有別於前述的Nomadland,也有別於遠祖Beat Generation「垮掉一代」的那些瀟灑漫遊者,他有他唯一要負責的人:女兒諾拉。諾拉直到孤身找到生母謝拉,才知道克林特在破產後毅然接手女兒的撫養,並為了這徹底戒酒。
在某次完成對法拍別墅的安那其式入侵之後,克林特對女兒說:「他們有後院有私人泳池而我們有自由。」這讓我想起美國夢的最早叛逆者之一、詩人艾茲拉.龐德的一首詩《頂樓》:
「來,讓我們可憐那些境況比我們好的人。
來吧,我的朋友,記得
那有錢人有管家卻沒有朋友,
我們有朋友卻沒有管家……」
但諾拉比她老爸現實一點,馬上接話說:「現在只有一大堆髒衣服」。髒衣服的意象後來出現了三次,第一次是克林特和諾拉把髒衣服綁在車子外面去洗車,同時就「洗乾淨」了衣服。第二次是克林特死後,諾拉把他的髒衣服都扔進舊衣回收桶,旋即後悔痛哭。第三次是諾拉短暫寄居一個善心基督徒家中,習慣性地把洗好的衣服晾在後者的吊燈上面,無意挑釁了後者的中產階級家居禮儀。
髒衣服其實是他們最後也是最好的盔甲。
最後一次衝突後,諾拉想起和父親一次星空下的對話,一隻章魚的脫逃故事,「顯然章魚不適合水族館」父親這句話像是預言,於是她就離開了寄居的中產家庭。這句話也解答了我在電影前半段的疑惑:特立獨行的父親如何處理孩子羨慕普通人的生活?我們家雖然不能做到像克林特那樣放棄居所和學校教育,但堅持不讓孩子看電視和接觸電玩,孩子最近也開始質問我們「為什麼別的同學都能看電視和玩電子遊戲?」——就像諾拉問克林特:「為什麼我們每次看電影都不看到結尾」(因為克林特認為結尾可以自己猜到,這是觀者的自由和樂趣所在)。
這個克林特差少少就是塞林格,寫《麥田捕手》的塞林格,終生以隱居來遠離美國社會,他後期作品「西摩(Seymour)系列」裡的西摩兄妹也是不適合水族館的天才章魚,最後陷於社會視為怪人的目光中,因為孤高而困頓甚至自殺。克林特是猝死的,就在前往諾拉出生地的路上,他的遺言是:注意那些火箭。他死前最後一個動作是鎖煞車,確保女兒的安全。
死於德州,到不了奧爾良。其後諾拉自己尋找生活的答案,電影沒有走向許多社會議題片或者驚悚片那樣的險象環生,是她遇見的美國人都太善良了嗎?還是因為尊敬她的勇氣?有的人試圖感化她「回歸正常」,更多的人對她惺惺相惜,像入侵法拍屋的朋克青年,像開更大露營車的老夫婦,像汽車修理廠的墨西哥移民……美國夢向來有這一面,對「法外之徒」的豔羨和寬容。
當然電影也終於迴避不了《無依之地》所直面的社會問題,被鐵絲網包圍的印地安保留區,電話裡不能越境而死去的墨西哥人,從流浪轉而駐留也難經營的母親,這些掩蓋不住的殘酷現實漸漸拌住了諾拉的車輪。電影以她加入一個曾被她父親嗤之以鼻的露營車聚會告終,不知道這是和解還是妥協,畢竟我們不能強求下一代的孤絕,如果我們想她也建立起屬於她自己一代的夢的話——諾拉長大後,注定不會成為《無依之地》的Fern的翻版,雖然她們有著一樣的勇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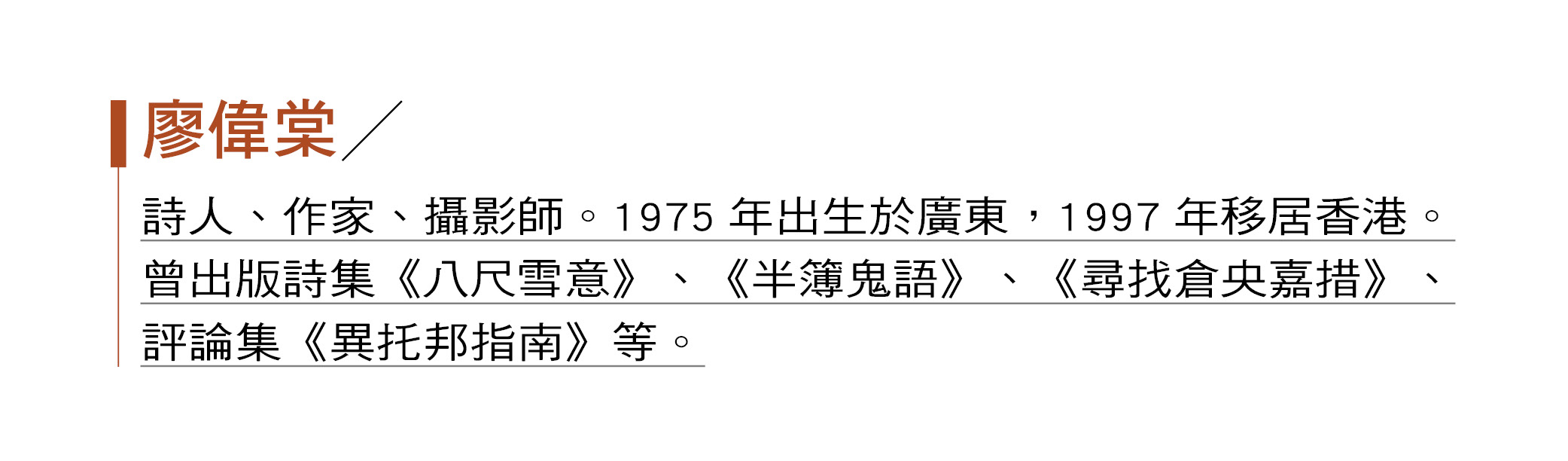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起底謝宜容!傳身家背景雄厚「善做公關」 先生和綠營高層有交情
- 一元特典!YOASOBI「超現實」小巨蛋演唱會釋出「零星票券」,11/24 採實名制一般販售
- 【世界棒球12強賽】滿足「2條件」台灣確定晉級4強 今晚是關鍵
- 先搶先贏!Ado 五月林口體育館演唱會採實名制入場,11/19 輸入「指定代碼」可優先預購
- 陳妍希與陳曉鬧婚變疑復合 她素顏與閨蜜聚餐模樣超清純全網夢回《那些年》
- 【內幕】T112步槍裝彈器採購案疑專利侵權 以色列向軍備局寄存證信函
- 楊冪人氣暴跌與《慶餘年》張若昀演新片淪鑲邊女主 造型曝光全網夢回《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